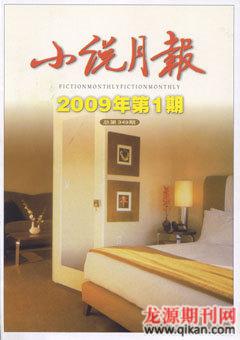人事
柳树从来不在头发上做文章,玩花样。梅志清也是。有的女同事的头发今天变钢丝,明天玩爆炸;今天焗金色,明天染红色,文章不知做了多少道,花样不知翻了多少新,已非时髦二字所能形容。梅志清呢,她的头发先是在脑后扎成两把刷子,后来把刷子散开,梳成了剪发头。她的头发不长不短,恰到好处。往后一抿,可以抿到耳后;自然流垂下来,刚刚抵达脖颈。人的头发千根万根,烫烫是弯的,拉拉是直的,变化余地很大,可塑性很强。梅志清没有求变,她的发型以剪发头的模式固定下来后,再也没有变过,多少年一贯制的样子。柳树没有烫过发,春夏秋冬,柳枝袅袅,没人说柳树的头发不好看。梅志清的头发以不变应万变,渐渐地,同事们也习惯了,没人说她的发型好看,也没有人说她的发型不好看。
一只人脚的脚指头只有五个,鞋的品种可不止五种。单拿女式的高跟鞋来说,其花样的繁多,恐怕谁都数不清。梅志清不穿那种奇高的圆锥体的高跟鞋,顶多只穿穿那种方形的半高跟。她个头不高,属于小巧型身材。如果她愿意穿高跟鞋的话,可以使她的个头显得高一些。然而梅志清不靠鞋的高跟提高自己,她觉得那样做有弄虚作假的嫌疑。这样的感觉梅志清不会说出来,报社里那么多女同事穿高跟鞋,甚至有的个子矮的男同事也穿隐蔽性的高跟鞋,一篙子打翻一船人就不好了。再者,她的工作岗位和工作性质也不允许她对一些生活小事作出简单判断。说到高跟鞋,她只说高跟鞋太拿脚,穿着不得劲。或说高跟鞋的鞋跟在楼道里敲敲打打的,太响了。
这么说,梅志清是一个古板的人吗?是一个跟不上时代潮流的人吗?也不是。流行歌曲,她也唱;健美操,她也跳;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她也看;听说哪种护肤美容霜好,她也买,她的思想一点儿都不落伍。要论思想解放的程度,梅志清当仁不让,并不比报社别的人差。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梅志清有不少创新性思维,她所领导的报社人事科,还是省内同类报社的先进单位呢!是的,梅志清是一家城市晚报社人事科的科长,科里只有她一个人,科长是她,科员也是她。人事人事,就是人的事情,不是狗的事情,也不是猫的事情。人比别的任何动物都聪明,都有灵气,做人事工作一定要慎之又慎,一点儿马虎不得。最起码,作为人事科的科长,不该说的不能说,不该做的不能做,风来了不能随风倒,水来了不能随水流,自律要严一些,应先为别人做出个样子来。报社的总编出国回来了,有年轻的女编辑在楼道里看见了总编,大老远就喊:我好想你呀!高跟鞋敲着水磨石地面,咯噔咯噔跑过去,两只胳膊一下子吊在总编的脖子上。梅志清说不出那样的话,也做不出那样与总编亲近的动作,她只对总编笑笑,问声回来了,就完了。在节日长假期间,报社的一些男女同事会应邀到某个同事家里做客,喝酒。喝了酒就玩儿派对,跳贴面舞。跳着跳着,说不定还要分头干点儿别的什么。对于这类活动,梅志清从来不参加。并不是没人邀请她,副刊部的主任黄原搞派对活动时就邀请过她,她说她跟孩子说好了,过节时要带孩子出去玩儿,就把黄原的邀请推辞了。一个女记者外出采访,乘坐的是出租车。女记者把出租车坐了一圈,连开出租车的司机姓甚名谁还不知道,就把自己的身体“出租”给了司机。天刚刚黑下来,在轿车的后排座上,女记者正举着双腿,像是作投降状,被巡逻到此的城市协管员发现了。协管员一问,女记者并不认识司机。两个人互不认识就干这种事,表明有买卖嫌疑。于是,女记者和司机都被带到派出所去了。派出所给报社打电话,报社领导派梅志清去把女记者领回来。领导还安排梅志清跟女记者谈了话。梅志清与女记者谈得很严肃。说从公共事业方面讲,作为一名新闻从业人员,要维护记者的职业形象。从个人生活方面讲,一个女性应不失生命的尊严。连一点儿尊严都不讲,捡到篮里就是菜,人和动物还有什么区别!女记者承认自己错了,说她脑子一热,就白热化了,就变成了一片空白。女记者不把梅志清叫梅科长,叫梅姐,说:梅姐,我求您一件事,这个事情请您一定替我保密。我结婚时间不长,我丈夫人不错,对我挺好的。事情要是传出去,让我丈夫知道就不好了。梅志清说:看来你的羞耻心还是有的。你这么说,我也有不明白的地方,你既然已经结了婚,夫妻关系也很好,干吗还要这样呢?女记者笑了笑,说:嗨,这个年代,大家都这样,随便找点儿刺激呗!梅志清一点儿也不笑,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这不是年代的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你还要好好认识。女记者自我解嘲似的,还在笑,以自己的手捂自己的嘴,似乎都捂不住,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又说错了。梅姐饶了我吧。今后我一定好好向梅姐学习。
梅志清的嘴很严。嘴严是做人事工作的干部必备的素质之一,不需要你开瓢的时候,你得把葫芦一直抱着,抱到发黄,发干,还是葫芦。女记者干的丑事,梅志清没有在报社传播。报社领导的意见,女记者的所作所为是激情错误,也属于个人隐私,只在内部批评教育就行了。女记者人际关系广,业务能力强,写过不少好稿子,还是用人所长吧!梅志清对报社领导的意见很不以为然。你看办城市晚报的人就是这样,他们得到社会上一些新奇新闻,不知有多兴奋呢,唯恐扩散不及,恨不能一夜之间让天下人都知道。可不管多么吸引读者眼球的事,一旦发生在报社内部人员身上,报社领导就当成了家丑,捂着盖着,不许外扬。尽管梅志清认为报社领导对女记者有些护短,她还是表示尊重领导的意见,说:好的,好吧,我明白。
有些事情不可与外人道,回到家里总可以说说。这天下班回到家,趁女儿参加学校组织的到郊区春游还没回来,梅志清把女记者的事对丈夫陈书刚讲了。她的态度与在报社不大一样,情绪有些激愤,用词也比较尖锐。她评价女记者在出租车内的勾当用了八个字,叫:禽兽不如,无耻之尤!丈夫很愿意听她讲女记者的风流韵事,但丈夫认为她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了,批评的话也有些过头。丈夫说:现在是开放的时代,是东西方文化大激荡大互补的时代,人家有张扬人性、享受生命的自由。这样的事连法律都回避了,你管那么宽干什么!两口子在客厅里的长沙发上坐着,梅志清扭过脸看着丈夫,说:纯粹胡说八道,你这是对开放的歪曲!听你的意思,你是赞成她那样做了?梅志清拿女记者的事跟丈夫当话说,是想拿这个事对丈夫进行一次测试,看看丈夫的思想走到哪一步了,还有没有是非观念。言为心声,她一试就试出来了,丈夫的思想果然到了危险的边缘。女记者是外人,无论女记者怎样堕落,她并不生气。丈夫是与自己朝夕相处的自家人,如果丈夫是非不辨,荣辱不分,和女记者的想法同流合污,她可真的要生气了。丈夫说:谁赞成她那样做了!那样做毕竟有失理智,也不雅观。我的意思主要是劝你,劝你对有些事情不要太较真,更没有必要生气。你看你的脸都气红了,何苦呢!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做人事工作一定要与人为善,宽容为怀,得饶人处且饶人,千万不要为一点儿小事钻牛角尖。牛角尖是什么?牛角尖前面是死疙瘩,钻不出去。钻来钻去,只能是自寻烦恼。梅志清说:反正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儿。什么叫张扬人性?张扬人性就是把被窝里的事拿到大街上去张扬吗?那还叫不叫人了!不管社会走到哪一步,人性应该越来越美好,而不是越来越丑恶。丈夫笑了笑,不再和梅志清争论。丈夫拿起放在茶几下面的电视遥控器,把电视机打开了。他换了几个频道,见一个频道正播放动物世界,才不换了。电视上,一只猎豹正在追捕一只邓羚,邓羚跑得快,猎豹跑得更快,不一会儿,猎豹就把邓羚扑倒了。丈夫说:我老婆的理论水平越来越高了,我看你当你们报社的书记都没问题。梅志清说:你不要讽刺我。
丈夫心里也有一件事,他弄到一张光碟,是一个生活片。利用女儿不在家的机会,他准备和妻子一起把生活片看一看。见妻子的情绪不大对劲,他暂时没把生活片拿出来。从妻子的讲述看,女记者与出租车司机的事也是一个生活片。妻子对那样的生活片如此反感,说不定对他带回的生活片也会反感。他的本意是调动妻子的情绪,讨妻子喜欢,若惹得妻子反感,岂不失了本意。干什么事都有一个时机问题。时机把握得好,就水到渠成。时机把握不好呢,就不会收到好的效果。他必须等妻子的情绪缓和下来,再伺机行事。他看着动物世界,先称赞猎豹身手矫健,快如闪电;又夸邓羚长得漂亮,吃得肥。他说他估计,邓羚的肉一定很好吃,因为什么动物跑得越快,它的肉就越好吃。妻子说:那不见得,凡是跑得快的动物肉丝子都粗。听妻子接话,丈夫往妻子身边靠近一些,伸出一只胳膊,揽住了妻子的肩膀。妻子没有拒绝。妻子的肩膀窄窄的,恐怕跟邓羚的肩膀差不多。而丈夫膀宽身长,隆鼻阔嘴,手背上还长有毛毛,与妻子相比,很像是一只猎豹。丈夫说,他带回一个生活片,问妻子愿不愿看一看。妻子问:什么生活片?丈夫说:就是关于夫妻生活的片子呗。妻子说:没看过。丈夫说:我也没看过。妻子问:不是黄色的吧?丈夫说:结过婚的人都是色盲,看什么都一样,哪里还分什么黄色绿色!
正好电视里的动物世界结束了,丈夫把生活片放进读碟机里。没有什么过渡,生活就开始了。在生活片里进行生活的是两个外国人,女人是白人,男人是黑人,形成了鲜明的黑白对比。丈夫一边看生活,不时地从眼角偷着眼观察妻子的反应。妻子满面通红,神情像是有些紧张。妻子的嘴张开了,又闭上了,像是不知张开好,还是闭上好。妻子喉咙那里一鼓一鼓的,在往下咽着什么。他及时献上殷勤,问妻子:你渴吗?要不要我去给你倒点儿水喝。妻子说:不渴。丈夫问:怎么样,好看吗?妻子说:什么呀,乱七八糟的,恶心死了!丈夫说:我看挺好看的,这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这就是生活的本质。这个黑家伙,真来劲!又看了一会儿,丈夫伸出一只手,向妻子两腿之间摸去。妻子把两腿一夹,说:干什么呀?丈夫说:我摸摸你的裤子湿了没有。妻子说:没湿。丈夫说:你说没湿,我都闻见味了。看来两口子看看生活片很有必要,对夫妻生活是很好的铺垫。妻子说:老说什么,看你的吧。丈夫说:我受不了啦,我想。妻子说:等一会儿。丈夫说:不行,我等不及了!说着,他两手一托,把妻子抱起来,往卧室抱去。生活片还没有放完,妻子说:你去把读碟机关掉。丈夫说:不用关,他们干他们的,咱们干咱们的。妻子说不行,万一小敏回来看见就不好了。小敏是他们的女儿。丈夫说:小敏不是说了今天和同学一起住农家院嘛!妻子说:万一她回来呢?丈夫只好跑回客厅,把读碟机关掉,并把生活片退出来。
丈夫兴奋着,对妻子的身体欣赏有加,把妻子叫成小鸽子、小麻雀、小花朵、小樱桃……一连叫了一大串。看了生活片,他不想按常规出牌了,提出换一种新的玩法。妻子不同意,说不行,你是流氓呀!丈夫说:让你说对了,我就是流氓。妻子说:你是流氓也不行,我必须坚持原则。丈夫说:你的原则是狗屁,今天你不放弃狗屁,我不干了!妻子说:不干拉倒!说着要起来。丈夫只得妥协,说好好好,依你,行了吧!按原则纳入轨道,丈夫对妻子有所埋怨,说:碰见这样的冷血老婆,真没办法。大概因丈夫准备得过于充分,他刚上去,就下来了。丈夫说:真没劲。
睡觉还有点儿早,梅志清穿上衣服准备回到客厅。丈夫未能尽兴,闹情绪似的赖在床上不起来。丈夫也不穿衣服,就那么光着身子在床上趴着。丈夫腿上的汗毛又黑又浓,像是外国男人的汗毛。梅志清说:陈书刚,你以后少跟我来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一套。陈书刚不答理她。梅志清又说:陈书刚,我问你,你的生活片是从哪儿来的?陈书刚还是不答理她。梅志清提高了嗓门:陈书刚,我问你话呢,你不要装哑巴。说着伸手在陈书刚看去很结实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屁股替陈书刚说话,发出一声脆响。陈书刚这才说:哪个超市里都有味精,随便就可以买一包。梅志清说:谁问你味精了,我问的是生活片。陈书刚说:生活片就是味精,夫妻生活的味精。梅志清说:胡扯!你拿回的生活片是黄色的,是淫秽录像,属于国家扫黄的范围。陈书刚翻身从床上坐起来了,说得得得,梅志清,你少拿大帽子吓唬我。谁家厨房里没有味精,谁家做饭不放味精就没有味道。我实话告诉你,你太保守了,太僵化了,在夫妻生活方面表现得相当差劲,连一点儿与时俱进的精神都没有。你如果再跟我玩儿原则,再对我这样冷淡,我就找别的女人去!梅志清说:去吧,爱找谁找谁。反了你了!
丈夫不止一次对梅志清说过,他要找别的女人,有时说要找一个情人,有时甚至说要找小姐。他的欲望比较强,要求比较多,一两天就向梅志清提一次要求。梅志清也需要那方面的生活,但她比较节制,主张少吃多香,避免大吃大喝。常常是丈夫要求两三次,她才给丈夫一次。她给丈夫的建议是,最好一星期一次。丈夫说:一星期一次我不够,你想憋死我呀!人家外国人,每天都要做。做少了女人还不干呢!梅志清说:你是外国人吗?你又不是外国人。丈夫说:外国人吃肉,我们中国人现在也有肉吃,我的能力一点儿也不比外国人差。要求得不到满足,丈夫急得狗不得过河似的,就说那些要挟性的话。那样的话说得多了,有一次梅志清突然发问:你在外边是不是已经有女人了?丈夫一愣,没有及时作出回答。梅志清说:不许编瞎话,看着我的眼睛,老实交代!丈夫把嘴撇了撇,说:我外边要是有女人,我还求你干吗!我要是真找到了女人,我就不会再提找别的女人的话了。梅志清说:那可不一定,现在的人变得很狡猾,说着花儿偷花儿的家伙多得很。过去是以假乱真,现在是以真乱真。丈夫说:看来你很有经验哟!梅志清说:你少跟我来这个,我的经验多得很。我正式警告你,你要是敢在外边给我胡作非为,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丈夫说:咱两个,要是出问题,也只能是你出问题。你长得这样可人,不知有多少男人盯着你呢!再说报社那种地方,哪个男编辑男记者不是见多识广,花花肠子!梅志清说:你不要倒打一耙!我要是出问题,除非石头也会出问题。丈夫说:我可不愿意让我的宝贝老婆变成石头。
陈书刚是市里某建材销售公司下属分公司的一个副经理,行政级别是副科级,比梅志清低一个级别。别看陈书刚管人不多,公司里女性资源还是有的。有道是兔子不吃窝边草,陈书刚才不听老传统那一套呢。窝边草干吗不能吃,哪儿的草嫩,哪儿的草好吃,就吃哪儿的草。窝边草吃起来更方便些。他利用方便条件,至少和公司里的两个女职员有了那种事。他以为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现在大家都放开了,谁还在乎那些事呢!当然保守的人也有,像自己的老婆梅志清就是一个顽固不化的落后分子。人性解放的潮流浩浩荡荡,一日千里,像梅志清那样的可怜之人才有几个呢!话说回来,老婆有那样的态度,也让他心中暗喜。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这样的老婆正好可以让他放心。不料有一天晚上,他们一家三口正一边吃晚饭,一边看电视,其中一个女职员的丈夫杀上门来。来人是个矮胖子,手提一只红色塑料袋。矮胖子认准了陈书刚,便从塑料袋里抽出一把菜刀,嚷着:陈书刚,你个狗日的,你个臭流氓,我劈了你!举刀向陈书刚劈去。陈书刚说:住手,你要干什么?你认错人了!矮胖子说:就是你,扒了你的皮,我认识你的骨头。人家是兔子不吃窝边草,你狗日的连窝边草都不放过。今天老子让你知道知道我是谁!亏得陈书刚身高力大,他抓住了矮胖子持刀的手腕子,菜刀才没有劈到他的门面上。亏得梅志清大声喊来了邻居,邻居报了警,警察赶来,才把矮胖子弄走了。矮胖子与陈书刚厮打期间,矮胖子朝陈书刚腿裆里的要害部位踢了一脚,还把他们家的电视机踹碎了。
梅志清是那么洁身自好,那么要脸面,这件事情对她的打击和伤害程度可想而知。梅志清气得脸色刷白,全身都在抖。她指着陈书刚的鼻子说:卑鄙!无耻!你滚吧!陈书刚说:我什么都没做,这家伙肯定误会了,要不然就是诬陷我。梅志清说:你说什么都没做,鬼才相信你的话。实话告诉你,我早就看透你了,只是没证据。这一次人家把证据送上门来了,看你还有什么说的。你说人家诬陷你,你就那么好诬陷。人家为啥不诬陷别人,为啥不诬陷我!梅志清还是让陈书刚滚。陈书刚塌下了眼皮,说:我往哪里滚,这是我的家。陈书刚的老家在农村,父母在农村,在城里他没地方可去。女儿说:妈,别吵了,原谅我爸这一回吧!梅志清说:不行,坚决不行!什么事情都可以原谅,就这种事情不能原谅,我不能跟不要脸的人在一起,不能跟叛徒在一起。他不走,咱们走!她带上女儿,到母亲那里去了。
梅志清的母亲是退休干部,母亲站在梅志清的立场,也认为陈书刚太不像话,应当好好教训他一下。母亲说,男女问题在以前是大问题,是大节。如果男女作风不正,就会被人看不起,就做不起人。现在改革了,开放了,虽然对男女之间的事情看得不像过去那样严重,但也不能胡乱来。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胡乱来也是丑事,乱搞男女关系的人也不能当国家元首。至于梅志清提出与陈书刚离婚,母亲的意见是等一等,看一看陈书刚的态度再说。人吃五谷杂粮,谁都有可能犯错误。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还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如果陈书刚态度好,愿意悔过,不妨给他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
梅志清住的是报社自建的居民楼,整座楼上住的都是报社的员工和家属。那天梅志清的丈夫遭人报复,一时间报社的人全知道了。公司经理与女职员有染,女职员的丈夫持刀上门复仇,用新闻的眼光看,这肯定是一条不错的新闻,而且是找上门来的新闻,不见报确实有点儿可惜。然而,梅志清毕竟是报社人事科的科长,为了照顾梅志清的面子,以免打老鼠时伤到镜子,这样能吸引读者的好新闻也只好割爱。要说每个行业都有不正之风,每个行业的人都能得到本行业的好处,那么从事新闻工作的人能得到的好处之一,就是家里出了丑事可以压下来,不会登到报上去。尽管这件事情没有传播出去,梅志清还是觉得很憋气,很没面子,甚至有些委屈。从门第、学历、级别,包括长相等各方面的条件来讲,她的条件都比陈书刚的条件优越一些,她没有任何对不起陈书刚的地方,陈书刚为什么还要与别的女人鼠窃狗偷!这是对她的背叛,也是在欺负她,实在不能让人容忍!梅志清把自己关在人事科的办公室里,上午十点报社的同事做广播体操时,她没有下楼。中午,报社食堂安排有免费午餐,她也没去吃。陈书刚打来电话,她一听是陈书刚的声音,只骂了一句无耻,就把电话挂了。
那位女记者来到人事科,问:梅姐,中午怎么没看见你去吃饭呢?梅志清说:我身体不大舒服,没觉得饿。女记者的黑头发前面挑出一缕,染成了黄色。那缕黄头发显得很跳脱,远看像是戴了一串黄刺梅。女记者指着“黄刺梅”问梅志清:梅姐,你看我的头发做得怎么样?梅志清应付似的说:挺好的。女记者说:这是我自己设计的。现代的人,就得自己设计自己。梅姐,我知道你为什么不爽,这实在没必要。有些事情发生了,也就发生了;过去了,也就过去了,千万不要放在心上,更不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梅志清笑笑说:没事儿。女记者说:你别说没事儿,我知道你的心情很不好,看你的脸色就看出来了。你比我大不了多少,可你们这一代人对传统文化接受得比较多。我不是说传统文化不好,但传统必须和现代结合起来,好比用笔写信和用手机发短信结合起来一样。现代化的力量是很强大的。梅志清说:你给我上课来了?女记者说:哪敢呢,我不过给梅姐提供一点儿信息而已。我看过一份西方关于人性需求的研究资料,说一个男人一生需要五个到六个性伙伴。女人需要性伙伴比男人少一些,一辈子至少也需要三个到四个。研究采用了大量实证材料,证明不管男人或女人,一辈子只有一个性伙伴是不够的,也是不人道的。他们认为,人类的性生活是生命之要义。有的女人找对象,对男人的性能力有数字化指标要求。能达到指标就嫁,达不到指标就不嫁。她们给男人定的指标是,一年内必须能够做爱三百六十五次。梅志清不让女记者再说了,说胡扯,纯粹是资产阶级世界观。
过了几天,一天下午快下班时,副刊部主任黄原也到梅志清办公室来了。他们一开始聊的是报社的事儿。梅志清学的是新闻,黄原学的是中文。黄原说:在报社工作,还是新闻系毕业的好一些,专业对口,说话硬气。他认为梅志清做行政工作屈才了,要是当编辑或记者,这些年下来,现在的职务至少是个副总编。梅志清说:我可不敢那么想。黄原说:反正我是这么看的。报社的不少人也是这么看的。梅志清说:真的?黄原说:当然真的,我恭维你干吗!大家不但认为你有才华,认为你人品也好,行为端正,气质高雅。梅志清笑了一下,说:你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你看,只顾说话了,忘了给你倒水喝。黄原说:不用客气,咱俩,你跟我客气什么。不过呢,也有人对你有一些看法儿。梅志清问:什么看法儿?黄原说:我说不说呢?梅志清说:你只管说吧,没关系,我能承受。黄原说: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认为你太清高了,太矜持了,感情生活也过于压抑。梅志清说:是吗?这可能与我的工作性质有关系,与我的性格也有关系。黄原说:其实咱们两个一样,我的感情生活也很压抑,我们都过得很苦。梅志清不由得说:你还压抑?她听报社的不少同事说过,黄原身边有一大帮女作者,女作者这个走,那个来,走马灯似的围着黄原转。女作者请黄原喝酒,在酒桌上,黄原就跟人家拥抱、接吻。黄原跟女作者谈稿子时常说一句话:这个稿子还需要润色一下。如果女作者心有灵犀,一定会请黄老师帮她润色一下。于是,他们就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润色”去了。不知黄原与多少个女作者“润色”过,反正女作者们都知道,黄原可是有名的“黄老师”。黄原说:我当然压抑。说不定我比你还压抑。举例说吧,我心里一直觉得你这个人很好,就是不敢对你说出来,这不是压抑是什么!今天总算壮着胆子说出来了,志清你不介意吧?梅志清说:这有什么,没什么。我有什么好,人家都说我保守。黄原说:哎,对了,我喜欢的就是保守的女性。现在有的女孩子开放过头了,一点儿情趣都没有。好比一朵花,开大了,就意味着凋谢。倒是有一些花,处在似开非开的状态,最令人神往。走,志清,今天晚上我请你喝酒。你的名字我也琢磨过,“志清”和“至清”谐音。古人云,至清则无鱼,至察则无徒啊!梅志清说:真不愧是名牌大学的高才生,真能咬文嚼字。黄原说:开玩笑开玩笑,傲霜斗雪有腊梅,志在清远品自高啊!
去不去跟黄原一块儿喝酒呢?梅志清为难了,陈书刚是喝酒的,梅志清领教过男人喝酒之后的疯狂。黄原喝了酒,是不是像陈书刚一样疯狂呢?她觉出来了,黄原有意于她。黄原像是一只精力旺盛的公兔子,把她当成公兔子窝边的草了。她想到了乘人之危这个词。黄原一定知道了陈书刚的事,并知道了她和陈书刚现在处于分居状态,就想从中插一杠子,这不太好吧。梅志清说:对不起,我不会喝酒。黄原说:你不会喝酒,咱就不喝酒。我请你喝茶,喝咖啡,总可以吧?梅志清说:我家里有事儿,必须按时回去。我们家出事后,我女儿竟然同情她爸爸,我一定要好好教训她。黄原说:看来你是不给我面子了。梅志清说:谢谢你的好意,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梅志清说过要和陈书刚离婚,但没有离。陈书刚三番五次到梅志清的母亲家,对梅志清说尽了软话,就差给梅志清跪下了。后来在梅志清母亲的监督下,陈书刚不但写了检查,还写了保证书,一并交梅志清保存,梅志清才又带着女儿回家去了。陈书刚在梅志清面前有了短处,每有夫妻生活方面的要求,更得看梅志清的脸色。他像一个乞儿,梅志清什么时候愿意给他一口,他就吃一口。梅志清不给他,他就只好饿着肚子。梅志清并不揭他的短,当他在梅志清跟前摇尾巴时,梅志清只须不声不响地瞪他一眼,他就乖乖地把尾巴夹起来了。偶尔有例外,那是陈书刚从外面喝了酒回来。陈书刚一旦喝了酒,就像另外换了一个人一样,雄赳赳,气昂昂,完全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时他根本不看梅志清的脸色,也不管梅志清瞪眼不瞪眼,挣扎不挣扎,抓住梅志清,就要做那件事。有时女儿小敏还没熄灯,正在自己房间里做作业,梅志清切着齿小声说:小敏还没睡呢,你干什么!还顾不顾一点儿影响?陈书刚说:什么影响,狗屁!我干自己的老婆,谁都无权干涉。如同一只猎豹叼一只弱小的邓羚,他很快就把梅志清“叼”到大床上去了。又好比,梅志清只是他的一顶帽子,帽子在某个地方放着或挂着,他眼到手到,轻而易举,就把帽子扣到自己头上去了。陈书刚不是把帽子扣到头上就完了,他刚扣到头上又取下来,刚扣到头上又取下来,循环往复,乐此不疲。这是陈书刚喝酒之后的又一种状态,特别能坚持,特别能战斗,持续战斗的时间格外长一些。梅志清完全处在被动的地位,为照顾影响,只得咬牙忍着。什么是野蛮?这就是野蛮。什么叫兽性大发?这就是典型的兽性大发。这与被人强奸有什么区别?没什么区别!梅志清深感屈辱,眼里噙满了泪水。她想到陈书刚和别的女人可能也是这样,觉得还是和陈书刚离婚好一些。
不管家里有什么事,梅志清从来不把不好的情绪带到办公室里去,从来不影响正常工作。把家事与公事分开,梅志清做得很好。经过体制内人事工作的长期训练,梅志清称得上是一位出色的机关工作人员。这年秋天,梅志清被评为全省人事系统的优秀工作者,省人事厅通知她,让她到省城接受表彰。梅志清很高兴。她没在新闻行业中当上状元,总算在人事工作方面当上了状元。表彰会开得相当隆重,省里的一位副省长都到会讲了话。开完表彰会,开宴会,喝酒。喝了酒,接着开联欢会,唱歌,跳舞。省人事厅部门很多,领导也很多,梅志清不认识别的人,只认识联络处的华处长。华处长到她所在的小城去过,她参加过华处长召开的人事联络工作座谈会,还与别的人事干部一起陪华处长吃过一顿饭。一回生,二回熟。再见到华处长,华处长就算是一个熟人了。在联欢会上,她跟华处长打了招呼,华处长果然认出了她,还带她跳了舞。那一曲是慢四的节拍,可以一边跳舞,一边说话。她对华处长说:华处长,谢谢您!华处长问:谢我什么?梅志清说:让我当优秀工作者,不用说是您对我的抬举。华处长说:应该的。又说:我喜欢你嘛,这没办法!华处长这样说话,是梅志清没有想到的,万万没有想到的。她本来是说句客套话,不承想这话让她说准了,她能当上优秀工作者,果真是华处长起的作用。看来客套话该说还是要说。她心跳有些加快,脸上也有些发热。她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也不敢看华处长的眼睛,只是低着头微笑一下,又微笑一下。华处长问她笑什么。她说:我觉得华处长说话挺有意思的。华处长说:我说话当然有意思,有意思的还在后头呢,你就等着吧!梅志清的勇气提高了一点儿,问:我不知道华处长喜欢我什么?华处长一点儿都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说:我喜欢你的小。小就是美嘛!我第一眼看见你,就想抱你。说着,趁舞曲结束,果然把梅志清抱了一下。
梅志清和华处长没有再跳成舞。不是华处长请别人,就是别人请华处长,华处长像是一个舞星,那些各地来的女优秀工作者都愿意和华处长跳。华处长的舞跳得自由,舒展,流畅,的确很好。不管华处长旋转到哪里,梅志清都能看到华处长。
回到房间,梅志清洗过澡,华处长打来电话,约她到自己住的房间聊聊。上级领导约她聊聊,她不好拒绝吧。于是,她到华处长的房间去了。华处长没怎么跟她聊,只说:你来了,很好!一下子就把梅志清抱住了,抱得梅志清双脚离地,像抱一个孩子一样。梅志清说:华处长,你不是说聊聊吗!华处长说:是呀,咱们躺到床上聊,可以聊得深入一些。你今晚不要走了,就睡在我这里。梅志清说:这不太好吧!华处长说:这有什么不好,我看挺好。我说过,一看见你,我就想抱你。而且,愿意把你抱到床上去。华处长说着,就把梅志清放在床上去了。华处长房间的床是双人床,床上的枕头也是两个。梅志清知道华处长要做什么,她稍稍有些紧张,双手也有些抖。她说:我刚洗过澡,头发还有些湿。华处长说:刚洗过澡正好,我也刚洗过澡。梅志清说:我心里一点儿准备都没有。华处长说:这不需要什么准备。又说:其实你一直在准备,你准备好多年了。梅志清说:你的话我不懂。你跟多少女人好过了?华处长说:只有你一个。梅志清说:我不信。华处长说:信不信由你。华处长正脱梅志清的衣服,床头柜上的电话响了。梅志清惊了一下,说:有电话。华处长一点儿都不慌张,说:可能是小姐打来的,不用管它!电话还在响,梅志清说:你还是接一下吧,万一有什么重要的电话找你呢!华处长这才把电话拿了起来:喂,哪位?噢,不需要,我们正在开会,正在研究重要的问题。
趁华处长在接电话,梅志清赶紧翻身下床,出门去了。
回到报社,心中似乎有了秘密的梅志清老是想起华处长。她想,她拒绝了华处长,一定把华处长得罪了。她有时有些恍惚,不知和华处长的关系到了哪一步。有一次做梦,竟梦见和华处长做到一处去了。华处长很会做。华处长的动作像和煦的春风一样,春风一吹,花儿不知不觉就开了,花瓣和花蕊都在微微颤动。
梅志清没有再提和丈夫离婚的事。平日里丈夫有了要求,她也不再拒绝,只是说:你要温柔一点儿。丈夫兴奋得直搓手,说:我的好老婆,你总算想开了!
原刊责编 王 童
【作者简介】刘庆邦,男,1951年生,河南沈丘人,当过农民、矿工、记者。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等六部,中短篇小说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二十余种,散文随笔集《从写恋爱信开始》等。先后获得河南省、煤炭部、北京市及各种刊物奖三十多项。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断层》获首届全国煤矿乌金奖,中篇小说《少年的月夜》、《卧底》分获本刊第十一、十二届百花奖。作品被译成英、法、日等外国文字。现为北京市作协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