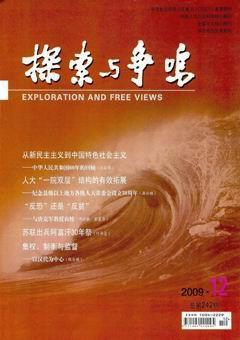“反恐”还是“反贫”
邱洪敏 郭星华
内容摘要《论道德恐怖主义》一文从一个不能成立的前提假设出发,构造了名曰“道德恐怖主义”的“假想敌”,根源在于对道德及其运行机制的认识和理解有偏差。它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界限;片面强调人性,没能认识到道德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规范系统,否定了职业道德、家庭道德等道德范畴存在的必要性,表现出一种“道德虚无主义”的倾向;且将道德运行的正常机制视为“非常态”,否认了民间自发的道德生机的正当性。道德在社会中有其特殊的、不可取代的价值,当前迫切需要的不是“反恐”,而是反对中国社会陷入到普遍的道德贫困。
关 键 词道德恐怖主义 道德虚无主义 道德运行机制 道德贫困
作者1邱洪敏,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2郭星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
近些年来,在社会转型、传统的破坏、市场经济发展等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社会道德状况持续恶化,并已然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道德滑坡”、“道德危机”、“道德沦丧”、“道德失范”、“道德真空”等概念,表达着对当前中国道德状态的感受和思考。最近,在2009年第9期的《探索与争鸣》上,唐克军教授发表了《论道德恐怖主义》一文(以下简称“唐文”),围绕一个新名词——“道德恐怖主义”,阐述了对目前中国社会道德生活的一种判断。笔者认为,唐文实际上构造了一个“假想敌”,对道德现状的判断有误读、误导之嫌。现阐发以下意见,与作者商榷,供同仁探讨。
“道德恐怖主义”的定义问题
唐文对“道德恐怖主义”的定义是:“我们把这种以道德为武器而制造公众对某些群体或个人的愤恨,从而使这些特定的群体或个人处于道德恐怖中的做法称为道德恐怖主义。”此定义其实暗含着一个前提假设,即认为目前中国社会存在一个统一的、为公众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体系。唯有如此,道德才可能成为“武器”。然则,如果这种假设是成立的,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又怎会如此堪忧?以“范跑跑”事件为例——唐文将其列为网络时代典型的“道德恐怖主义”案例。公众对于该事件的讨论,尤其是网络上的跟帖,炮轰指责的、辩护颂扬的、寻获真相的、漠然置之的,各种声音兼而有之,唐文所暗示的万众一心的道德攻击未曾真实存在。公众对“范跑跑”事件发出的不同声音,多少表明了人们对道德认识的混乱和迷茫,这恰恰说明了当前中国社会缺乏道德共识。
唐文将不存在的统一道德规范体系视为理所当然,并认为它掌握在某些个人或群体手中,被用来向另一些个人或群体实施“道德恐怖”。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那些“以道德为武器制造公众对某些个人或群体的愤恨”的人及他们针对的对象究竟是谁?这些人各自占到全国人口的多大比例?有什么样的社会特征?唐文却始终回避着上述问题,在“道德恐怖主义”的实施和承受双方的界定上含糊其辞、语焉不详。文中先后使用了“某些占据精神的官员”、“城里人”、“体制内的人”、“处于社会结构的强势地位的人或为社会强势说话的人”等内涵不一的词汇,指称制造“道德恐怖”的一方;相应地,亦使用了一些同样内涵各异的词汇来指称受到“道德恐怖”威胁的另一方,如“那些心怀蝇头小利的人”,“作为‘草民、‘刁民的人”,“体制外的人”,等等。通过回避对实施和承受“道德恐怖”双方群体的明确界定,不断偷换概念,唐文构建了这样一幅图景:在我们身处的时代,道德再度成为工具,利用它的是“某些官员”、“城里人”等“强势群体”,他们以道德高尚者自居,夸大渲染“那些只有自己利益的人”、“乡下人”等“弱势群体”的道德危险性,从而将可能的竞争对手排斥在社会之外,目的在于维护既得利益和地位。如此一来,“范跑跑”似乎摇身一变成了弱势群体的典型代表,而对“范跑跑”等利己者进行过“道德攻击”的人们则已然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
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从两点揭示上述“道德恐怖主义”图景的虚假性:其一,依据韦伯的经典定义,权力是可以不顾他人反对而贯彻自己意志的能力[1 ],权力的合法性根源于人们的普遍认同,道德权力概莫能外。无论是中国封建时期的“以礼杀人”,还是西方的社会种类区分,乃至唐文虽未提及却容易使人因其表述联想到的——“文革”时期的泛化道德主义,道德之所以能在一定的时期,成为统治者或占据社会强势地位的人利用的工具,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中,有着相应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道德伦理价值共识。反观当今中国社会,正如之前所述,并不存在为人们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体系,这大大削弱了道德权力的合法性基础,道德的力量有限,并不能或不足以成为唐文所谓的“道德恐怖主义者”的“武器”。其二,众所周知,公众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有很强的弥散性和民间自发性,集权的、官方的因素并不明显,在没有找到确凿的经验证据之前,笔者对存在任何能只手遮天的激起公众愤怒和仇恨的人、群体、阶层或利益集团,持保留、怀疑态度。在这一点上,唐文无法或不想给出“道德恐怖主义”双方群体明确界定的做法本身,就是极好的注解。
至此可见,唐文从一个不成立的前提假设出发,描述了一幅虚假的当今中国道德生活图景,将其称之为“道德恐怖主义”。且不说唐文对此概念的提出,没有与任何既有知识进行对话沟通——尽管只要抬手在网上搜索一下该词条,至少也能追溯到在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中,曾出现过“道德的恐怖主义”这一形似概念及定义①;在唐文发表四年多以前,“道德恐怖主义”一词已经出现在一篇期刊文章中②;一年多以前,在天涯论坛的一篇帖子中也显现了踪迹③——单是唐文将其对目前道德现状的判断与“恐怖主义”相提并论,就颇有忽视学术严谨规范性的意味。“恐怖主义”(Terrorism)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成为了全球范围内的热门概念之一。门德兹曾尖锐地指出,“恐怖主义确实是一个为散播某种不恰当的推论,从而促进不恰当情绪发展的被广泛采用的词汇和概念”[2 ],这提醒人们警惕误用甚至滥用此概念可能导致的不良影响。《辞海》对该词条的解释是:“主要通过对无辜平民采取暴力手段以达到一定的政治和宗教目的的犯罪行为的总称。较多采用制造爆炸事件、劫机、扣押或屠杀人质等方式造成社会恐怖,打击有关政府和组织,以满足其某些要求或扩大其影响。”[3 ]虽然目前学界尚未形成对恐怖主义的统一定义,但对恐怖主义的本质特征还是有基本共识的,即暴力性、恐怖性及政治性,而且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只是恐怖主义实施者实现其政治性目的的工具。
据此来审视唐文“道德恐怖主义”概念的定义,不难发现,这是一种对“恐怖主义”概念不恰当的误用,其致命错误在于:唐文所谓的“道德恐怖主义者”顶多也就是使用了道德言语的冷暴力,即使其对手因为网络时代放大效应下的“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而产生了生命受到威胁的恐惧心态,陷入了道德恐怖之中,这一切还是与任何攫取政治权力的图谋扯不上关系。仍以“范跑跑”事件为例,有多少网民在发帖议论范美忠的行为是否道德的时候,不是针对其人其事,而是瞄向“打击有关政府和组织,以满足其某些要求或扩大其影响”的?唐文对“恐怖主义”概念没有进行宏观把握和细致辨析就贸然使用,实在不够科学。
综上所述,无论从事实逻辑层面,还是从学术规范层面看,唐文提出的“道德恐怖主义”都只是一个“假想敌”。范跑跑等人确实因为不当的言行承受了过分的社会压力,即陷入了唐文所谓的“道德恐怖”之中,但问题绝不是出在有既定利益集团拿着道德当枪使上。在旧的道德体系瓦解,新的道德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的情况下,目前中国的道德呈碎片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德评判,主导公众达成某种道德共识的概率少之甚少。
道德及其运行机制问题
笔者认为,唐文之所以错误地制造了“假想敌”,根源在于对道德及其运行机制的认识理解有偏差。
其一,人类对道德的思考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虽则尚没有形成一个完备的、严格的逻辑定义,但还是达成了一些基础性的共识。道德是以善恶评价为中心的规范系统,从其发展的逻辑轨迹看,其范围呈现缩小的趋势:在原始社会中,道德几乎是唯一的社会规范,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一部分道德上升为了法律,一部分道德不适应社会的需要而消失,道德规范的范围不断缩小,演变成为对共同体成员行为底线的规定。由此可见,在现代社会中,道德已经不可能包揽衡量人们言行的所有准则,唐文却完全忽视了道德的作用域问题,例如文中举了评价中年妇女为儿子偷肉被抓事件陷入的困境,以说明“道德问题发生在复杂的情境中,因而不可能凭借一种道德标准衡量人”,其实唐文已经依据一定的准则对这位妇女做出了道德评价——慈母和法律评价——小偷,只是没有意识到道德和法律这两种社会规范的界限罢了。
其二,道德、法律、习俗,等等,都属于社会规范范畴,而一切社会规范都是对人性、对利己之私的约束,以此来调节和控制社会,避免人类共同体陷入霍布斯所说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之中。唐文片面强调“人的特性和具体的情境”、“人有软弱的一面”,甚至走向这一立场的极端,认为军人临阵怯弱没有违背道德,“范跑跑”没有不道德,父母因贫穷而卖儿卖女不是不道德。其论证逻辑是:因为“人非圣人”,没有人能绝对地履行道德准则,所以军人在国家需要他浴血奋战时退缩避战不是“恶”,教师在学生们需要他指引生路时只顾自己逃生不是“恶”,父母为了自己能活下去把子女当物件卖掉也不是“恶”。唐文的错误是没能认识到道德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规范系统,将过去的、现在的、不同职业的、不同社会领域的道德内容混为一谈。
道德有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之分,不同层次的道德对应不同的作用域和作用对象。在社会分工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职业道德对社会秩序的维持有着特殊意义,军人职业有着对军人行为底线的要求,教师职业有着对教师行为底线的要求,对军人、教师等言行的道德评判就必须立足于相应的职业道德要求,而不能以普通公民的道德准则去衡量。在地震来临时,人本能地选择逃生无可厚非,但范美忠作为一名教师全然不顾自己学生的安危自己逃命,这就违背了人们对教师行为的预期,突破了作为教师的道德底线,且他本人还丝毫不为之感到羞耻。对这种严重违背职业道德的行为,如果还用普通人人性的软弱、利己加以辩护,是站不住脚的。唐文如此混淆善恶、是非界限,等于否定了职业道德、家庭道德等道德范畴存在的必要性,实际上也就否认了道德评判的可能性,是“道德虚无主义”(moral nihilism)④的表现。这种混淆和否定如果成为当今中国道德评价的主流,势必导致人们道德底线的普遍失守,使社会共同体处于崩溃的危险境地。更何况,假使人人都能绝对地履行道德准则,道德反而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正是因为人性固有的利己和软弱,才需要一定的道德机制来压制人们的恶,弘扬人们的善,从而维持社会的基本秩序。在这里,有一个对道德和人性孰重孰轻的权衡问题,正如赫胥黎曾说过的,“如果没有从被宇宙过程操纵的我们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天性,我们将束手无策;一个否定这种天性的社会,必然要从外部遭到毁灭;如果这种天性过多,我们将更是束手无策:一个被这种天性统治的社会,必然要从内部遭到毁灭”[4 ]。
其三,道德发挥作用的机制与法律不同,法律依靠专门的组织、借助正式强制力实现社会控制,而道德依靠的是社会共同体的成员,借助的是人的内心信念、传统习俗、社会舆论等非正式力量。具体而言,道德规范是与某种“好”或“坏”的、“善”或“恶”的说法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不是随意的,而是在长期的社会共同体生活中形成的。当有人违反了某种道德规范时,他会经历一种内在的“社会裁定”,即那些感受到此人的行为是“对共同体自身(共同体一般)基础的一种违背”的共同体成员们,会将不道德的行为标识为坏的行为,并将此人判定为坏的,对其产生义愤的道德感受,进而指责或谴责他。与之相对应,如果这个违背道德规范的人认同所属的共同体,那么他的人格就会被义愤或指责所“击中”,产生羞愧和罪责的道德感受,而义愤趋向于导致他被道德共同体开除的结果,是他最为惧怕的,道德由此发挥了对个人人性的制约和控制;反之,由于社会化不成功等因素,这个违背道德规范的人并不认同这个共同体的道德价值,义愤无法击中他,社会裁定对他不造成影响,道德也就丧失了对人性及行为的约束力。[5 ]
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表明,在原始社会中,违反原始道德招致的社会压力非常大。而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社会流动频繁、社区解体等原因,社会成员的共同体认同感下降了,道德的作用范围在缩小,控制力也随之削弱,这才使得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等依靠正式强制力的社会规范有了用武之地。回到唐文的论述上来,它联系古今中外指出,“不论道德恐怖主义以何种形式出现,其实质是一种社会排斥”,此外,还大谈此社会排斥“破坏人的道德平等”、“阻碍制度的改进”、“损害民主的健康发展”等危害,殊不知,这种社会排斥本身就是道德发挥作用的正常机制。
唐文将道德发挥作用的正常机制视为“非常态”,却没能看到:在当今中国社会不容乐观的道德状况下,如果公众网络舆论真能形成某种排斥不道德者的合力,恰恰说明人们心中还残留着某些共同的道德标准,这种民间自发的道德生机,将是道德重建的宝贵资源。唐文将这些人标签为“道德恐怖主义者”,可曾想过在转型时期的当今中国,在传统和信仰已然缺失的情况下,假如连他们都噤若寒蝉,结果会是怎样?
唐文的可取之处在于,提醒人们注意网络时代道德舆论压力的限度问题。道德不是目前中国社会唯一的社会规范,在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需要考虑与法律等其他社会规范的协调统一。现代社会,尤其是在网络等现代媒体无孔不入,且倾向于将舆论压力无限放大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尊重和保护人的隐私权,不能因为某些人有了不当言行,就对其进行“人肉搜索”,进行肆无忌惮的人身攻击,完全不尊重这些人起码的人格和尊严,令其陷入“道德恐怖”——甚至无法正常生活下去。这一方面是因为目前种种不道德行为的出现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也是社会的问题:范美忠道德社会化的不成功,原因不可能完全归结到他自己身上,根源还在于中国目前的道德伦理“真空状态”[6 ],在普遍的道德贫困中,如何能保证人人都能自觉地遵从道德规范行事?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在对别人进行道德评判时,人们也要守住自己的行为底线,滥用“网络暴力”,侵犯人的隐私权,会突破道德的界限,甚至触犯法律,这就违背了道德舆论的初衷。
社会秩序的维持不可能完全依靠法律等正式规范,道德在社会中有其特殊的、不可取代的价值。唐文未能给出对中国道德现状的正确判断:我们今天迫切需要的不是“反恐”——掐灭道德残存的一点儿生机,而是“反贫”——反对中国社会陷入普遍的道德贫困。“反贫”的核心在于重建社会道德体系,但道德重建,既不能照搬过去的道德体系来规范现在的行为,也不能完全脱离历史和文化传统进行彻底的颠覆建设,更不能遵循唐文的思路走向混淆道德、否定道德的误区,对此我们当保持清醒的认识。
注释:
① “人类在其道德的天职上,或者是继续朝着更坏倒退,或者是不断朝着改善前进,或者是永远停顿在被创造界中自己道德价值的目前阶段(永远环绕着统一点旋转也和这是同一回事)。第一种主张我们可以称之为道德的恐怖主义;第二种为幸福主义(如果以广阔的前景来观察进步的话),也可以称之为千年幸福主义;但是第三种则可以称之为阿布德拉主义……”摘自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② 风石堰:“公共利益与道德恐怖主义”,载《开放时代》,2005年第4期。
③ 冷眼童子:“网络空间培育着道德盖世太保,不,道德恐怖主义者们”,2008年6月25日,网址: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1318258.shtml。
④ 道德虚无主义是一种根本否定道德的主张,它认为,“任何证明或批评道德判断的可能性都不存在,理由是道德不过是寻求自我利益的借口”,见刘时工:“道德虚无主义和柏拉图的对策”,《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第35卷第6期。
参考文献:
[1]贾春增. 外国社会学史(修订本).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13.
[2]P.麦斯纳德. 门德兹,于海青摘译. 甄别“恐怖主义”:语词与行动. 国外社会科学,2003(6).
[3]辞海(缩印本).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1931.
[4]张桂华. 道德对科学的误解. 博览群书,2002(12).
[5]E. 图根特哈特,辛启义译. 论道德的概念与论证.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版),2007(3).
[6]万俊人. 现代性的伦理话语.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178.
编辑李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