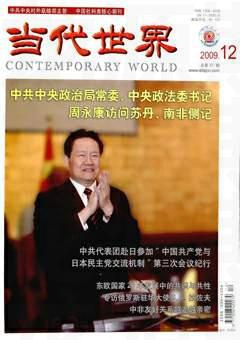也谈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机制
黄卫平 丁 凯
雷曼冲击引发次贷危机发生以来,各国联合出手,实施特殊的经济刺激措施,发达经济体运用大规模财政政策的配合,实施零利率下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取得了效果,稳定了人们的价格预期,避免了1929-1933年“大萧条”式衰退的发生。特别是2009年8月以来,随着国际金融市场逐渐趋于稳定,各国股市大幅回升,流动性奇缺、信贷紧缩现象有所缓解,大宗商品价格回暖,油价突破70美元一桶,铁矿石价格提升,海运指数向好, 市场风险偏好和信心提升。很多政府和国际组织都已作出危机最坏时期已经过去的判断,有的学者甚至判断全球经济衰退基本结束,并预测全球经济将在2010年前后开始全面复苏。在这样的环境下,雷曼冲击渐行渐远,人们探讨刺激经济措施的退出,具有政策和现实操作的重要意义。
近来,澳大利亚央行将基准利率提升25个基点至3.5%,并表示将逐渐退出刺激政策。此前,以色列、挪威、印度等国家均已跻身“加息大军”,美国政界和经济界已忙不迭地宣称自己已接近危机尾声,法德等欧盟经济大国的经济恢复也算得上是“出人意外”。中国经济更是“一片大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7.7%,其中第三季度增速达到了8.9%,最乐观的预测已将中国的GDP增长看高到9%以上,据此,中国的银行贷款不同月份变动极大,央行也在利用市场机制回笼货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退出机制。一时间,世界金融危机阴霾渐去,全球范围内的“退出机制”已悄然实施。
“退出机制”的含义
应该说,“退出机制”已成世界和中国不得不关注的问题。所谓的退出机制,就是指对由政府主导的、专门旨在挽救金融危机的特殊经济刺激政策的放弃。一般来说,各国政府宏观调控的“三大法宝”无非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道义劝说(即行之有效的行政手段,政府首腦和央行行长或劝说或威胁或暗示)。特殊的刺激政策则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大规模财政投资和借钱给银行(美国把后者称为注资)。当然,它不包括那些正常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发达经济体由于体制的分立,也由于过去反周期大量运用凯恩斯主义的措施,财政赤字堆砌形成的压力已经无法使它们再大量运用财政手段刺激经济,而更多地使用货币政策,谈到退出时,则主要是货币政策取向的变化。但就中国而言,特殊的经济刺激政策是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配合使用,未来如何动态调整、适时退出。说白了,就是在宏观调控政策下,目前实施的财政、货币政策撤不撤、往哪儿撤的问题,如何把“洗澡水”泼出去,还得确保把“孩子”留下来。
“调结构”与“保民生”的意义
金融海啸以来,中国主要实行的是积极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多次降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大部分政策都是以保增长、保速度为出发点,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结构的调整,保环境、保民生应成为下一阶段的“战略重点”。2009年全国财政预算安排中,有1300多亿投向了医疗、保障性住房、教育等社会保障方面,同比增长25.1%。但在笔者看来,媒体和大众往往只看到其拉动消费的作用,殊不知这正是中国经济改革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措施,是中国在这一具有世界意义难题面前,通过应对次贷危机形成的重大改革步骤,它将深深影响国人的消费习惯和思维方式,所以将中国实施的经济刺激措施单纯地看成是拉动内需有些偏颇。将于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把“调结构、防通胀”作为重点,财政收入的增长要同个人收入增长相协调,政府投资的限度和节奏都将做大的调整。笔者以为,调结构是一个动态过程,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如果调结构被理解为只是在老产业中进行资产重组,甚至是“国进民退”式的重组,并且符合国内需求、国外需要的新产业发展缓慢,就业也不能够较大幅度增加,那实际上就没有达到调结构的真正目的。如果符合客观需要的调结构、保民生的政策出台了,就是某种意义的目前刺激经济措施的“退出”了。
“触底反弹”与“自我修复”
是“退出”的充要条件
现在,美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出经济刺激政策开撤的信号。中国该不该响应?这需要探讨宏调政策“退出”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
中国央行认为(中国人民银行5日发布的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一是要从理论上判断,退出应以危机的影响基本消除、经济恢复增长为前提。但实践中,需要对退出时机和力度作出准确的判断,否则,政策退出过快,可能给复苏带来压力;退出过慢,则可能引发新一轮资产价格泡沫和恶性通胀。二是关于退出工具的选择。除逐步缩小应对危机的数量型工具规模、适时运用常规工具外,也可以考虑创新其他工具,以保证在经济复苏时既可以较快地回收大量流动性资金,又不会使信贷市场发生较大波动。三是关于货币政策与财政等其他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以及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应避免政策效应的漏损,或以邻为壑政策对其他经济体的损害。笔者则以为,刺激政策“退出”的必要条件是经济触底并持续反弹,充分条件是经济已经出现自我修复机制。复苏会是什么方式?V形(快速回升到正增长)、U形(缓慢的复苏)、W形(双底形)或是L形(长期衰退)?所谓触底反弹和自我修复,在美国是一回事,在中国是另一回事,到了印度可能又是其他一回事了。在美国,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银行开始向政府还钱,破产保护的通用公司也开始还钱了,宣布了债务偿还计划。据称要分期偿还欠美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的67亿美元和14亿美元债务。企业的高管认为已经不需要政府这根“拐棍”了。中国的情况则比较复杂,主要可以看“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指标的情况。2009年上半年,尽管中国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了88%,是过去10年平均值的两倍,但消费的增长却并不同步。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消费需求占GDP比例较低的时候,内需可以绝对支撑发展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其实,只要“三驾马车”比例不失调,内需、外需都在提升,就可以考虑放弃刺激政策。
如果把美国挽救金融危机的政策比作是给经济“排毒”,那中国就是在给经济“大补”。4万亿当中,有1.8万亿即使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也要投入,这属于前面所说的正常财政投资。非正常的是另外的2.2万亿,是特殊政策。政府充当了市场流动性的“主治医”,银行信贷变成了项目投资,经济是政府投资拉动型增长,而非自然“康复”、可持续增长,因此应逐步撤出。当然,刺激也不能一下子全断掉,要考虑到乘数效应(支出的变化导致经济总需求与其不成比例的变化,一般是后者大于前者)和加速数效应(收入或消费的变动所引起的投资变动,后者的增长一定要快于前者),因此,“退出”不可能是一个立竿见影的“令行禁止”过程。
利率与资产泡沫是“退出”的着力点
经济的刺激政策,如果行之有效,可以增强市场和投资者的信心,使得人们感觉到有政府的依靠,对未来“托底”。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同样重要。退出时机的把握,力度的调控,明确未来政策退出的机制,可以改变投资者对未来经济走势的预期,而这种预期会对未来经济走势形成实质的影响。笔者认为,退出机制的最明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利率上。为了削减赤字,各国央行通过将利率减到接近零的水平(瑞典的利率甚至在零以下),再辅以发放超常的信贷来缓解市场的不足,以增加货币供应。美国的货币基数在一年内翻了一倍。若中国不考虑跟进他国的退出机制,就有可能出现利率息差,资金流量就会发生变化,通货膨胀等压力就会出现。现在,发达国家去杠杆化已撤销,而中国还在堆钱,难免会出问题。现在澳大利亚、以色列等已退出,美国实际上也已退出,北欧各国正在退出,他们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提升利率,减少货币的供应量。发达国家这次的经济刺激政策,在执行中资金供给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实施,例如拍卖等,形成大量的流动性,表现为存款和现金,因此,它们可以相对容易地收回市场中的流动性资金。中国的刺激政策却不是这样,政府充当了市场流动性的主要提供者,银行信贷是大量项目投资的配套资金的主要来源,一旦财政、货币政策退出过快,资金跟不上,那就意味着“半拉子工程”激增和银行不良贷款的上升。因而,建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协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退出机制是不容易的。中国事实上也在逐渐相机撤出,央行公开市场回笼货币,逐月变化信贷投放的举措都体现了这点。有媒体预测,中国2010年上半年至少会有两次加息。流动性减少,股市不会有太多收缩迹象,但房地产市场会由于贷款政策的日趋谨慎而放慢增长,股市会持稳或往下行通道波动,房价会得到一定的抑制。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资产价格的膨胀。2009年1—10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8.9%。中国宏调刺激措施迟迟不退出,过度信贷将使资产泡沫继续放大,但国内一般产品的生产能力的事实全面过剩,又使得一般产品的物价难以高企,通货膨胀和缓,这反而会对形势判断形成困惑,退出机制迟迟难以出手,给实体经济发展造成不利,甚至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退出机制越有效,市场对未来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预期就会越平和,投资者对资产价格的追逐也会越理性。当然,中国经济结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要协调发展,投资结构是关键,判断也需要正确,事实上,人们的许多判断是似是而非的。例如,人们在谈及中国内需增长缓慢时,大多会将原因归结为社会保障的缺失和不到位。研究表明,社保投入提高了,消费却未必上得去,因为养老的钱和看病的钱省下了,却可能存入银行或全扔进股市里了,边际消费倾向反而可能会因此递减。
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应协调发展
自2008年底开始,中国新一轮刺激措施安排了数额高达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以政府投资为主,同时超配银行信贷,政府预算与银行贷款一起,演变成了中长期的项目投资。2009年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55057亿元,同比增长33.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6.4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连续两个季度超过30%,处于历史高位。这些钱主要投向了地方基础建设。此中,国有企业占有绝对垄断地位,导致国有企业成为推动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增长的主体,政府投资增速比民间投资增速要快得多。
随着“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实施,相当部分贷款的项目围绕着铁路、公路和机场展开,投向了政府主导的大型建筑公司或城市投资公司等平台,私人部门投资的“阵地”被大量占领。应该说,当经济增长出现困难时,国有经济因其特点,被更多地赋予责任是应该的,事实证明也是有效的。因此,在经济困难时,一定程度的更多地依赖于国有经济的运作,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如果经济状况好转之后,民间投资不能跟进的话,将会严重影响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只有双方共同的配合和努力,宏调退出后的局面才会稳定。
一个良好的退出机制和有效的操作,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不仅反映了中国经济的状况,也将体现出在经济竞争领域“民进国退”的既有常态,对中国经济结构的良性变化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会具有更好的促进作用。
(本文第一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第二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肖雪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