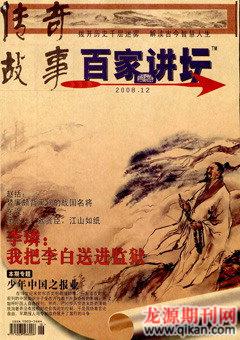秦穆公:跑龙套的春秋霸主
黄朴民
春秋五霸,名头响亮,可究竟是哪五位霸主?历来人言言殊,说法各异。其中比较通行的名单有两份:一是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另一说是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而在这两说之中,似乎又以第一种说法为更多的人所认可。
虽说都是霸主,但这五人的分量,也就是说,其霸业成就以及影响却不可同日而语。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可以算是一个档次,他们号称霸主,当属名副其实,而宋襄公被列为五霸之一却颇有些不伦不类。他的高雅贵族风度,固然让人肃然起敬,可他的那份儿霸业,则难免让人啼笑皆非,世俗是势利的,只以成败论英雄,泓水一仗,他大败亏输,出尽洋相,以至于成为千百载来够“厚黑”或不够“厚黑”的芸芸众生挖苦嘲讽的对象。如果靠这种表演居然能跻身于五霸的行列,那么,多少有些滑稽,有些荒诞,宋襄公九泉有知,恐怕也会受宠若惊。
至于秦穆公,则是一个异类,换句话说,他属于不尴不尬的角色。说他不济吧,可他在当时的“国际”大舞台上活跃得很,又是“勤王”,又是“盟会”,知名度、出镜率一点儿也不逊色于其他人,更何况他也曾“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为秦国在春秋战国期间的雄起,作了非常扎实的铺垫,多少混出个“霸主”的模样,可如果真的把他算成是霸主,却似乎又不是这么一回事,毕竟他没有像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那样,一本正经地充当过中原的霸主,他的事业也仅局促于西北一隅,从来不曾达到过光辉的顶点,而且总是笼罩在晋国霸业的巨大阴影之下,只好在当时上演的争霸大战中,敲敲边鼓,跑跑龙套,总而言之,秦穆公在当时更像是搅局的角色,把他列为春秋五霸之一,或许比较勉强。
秦穆公之所以没能成太大的气候,显然有种种客观因素的制约,在他出道的时候,齐、晋、楚已俨然蔚为大国,中原这块大蛋糕基本已被它们抢先分割完毕。秦国长期僻处西北一隅,中原诸侯“戎翟遇之”,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想要入局并充当龙头老大,困难之大,可想而知。然而,这并不等于说,秦穆公一点机会也没有。如果战略高明,战术对头,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秦穆公还是可以有一番大的作为的。问题的症结,看来还是出在秦穆公自己身上,是他战略眼光的短浅、战略举措的失当,直接导致了其雄心勃勃的争霸企图成了“水中之月,镜中之花”。
秦穆公在位近40年,平心而论,他本人为秦国的崛起与发展,还是做了不少力所能及的工作的,他四处延揽人才,打破常规,任用百里奚、蹇叔、由余、邳豹等一群贤能。扎扎实实发展经济,大刀阔斧扩充军备,今日东征,明天西讨,使得秦国的势力迅速扩展到渭水流域的大部分地区。总之,秦国在他的领导下,虽然不能跻身为“国际”大国,但终究算得上地区强国。
“人心不足蛇吞象”,秦穆公也不例外。拥有了比较雄厚的资本,他自然要企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去成就更大的功业。这功业就是带领秦国走出狭窄的关中地区,东进中原,称霸诸侯,尽管秦穆公也知道要做到这一点绝非一件容易的事,但他却不甘心就此淡泊寂寞,偏居西隅,日趋被边缘化。他相信事在人为,决心尽最大的努力,来使自己的夙愿变成现实。
可惜的是,人算不如天算,秦穆公的战略措施跟他的战略目标是完全南辕北辙的。照着秦穆公自己的如意算盘,秦国东进战略步骤应该是:先想方设法同晋国搞好关系,对晋国的政局施加影响,通过缔结婚姻、提供援助等手段,逐漸控制晋国。一旦在这方面得手之后,再大兵出崤、函,从容图霸业,指点江山,号令天下。
于是乎,秦穆公便趁着晋国内部发生骊姬之乱政局动荡的机会,加大力度干预晋国内部的事务,操纵晋国国君的废立。他先是派军队保驾护航,把晋惠公扶持上台,尔后又默许晋怀公即位,可是这两位受保护者都不尽人意,位子刚刚坐稳,羽翼稍稍丰满,便神气活现起来,将秦穆公晾在一边。晋惠公更是忘恩负义,撕破脸皮与秦穆公作对,出动军队在韩原(今山西河津东)与秦国干上一架,两国之间的关系完全恶化,秦穆公原先的计划统统泡汤。
与其将错就错,不如改弦更张,于是秦穆公决心中途换马,重新物色代理人。具体的做法,便是提供军事援助,进行武装干涉,帮助长期流亡在外的公子重耳返回晋国,从晋怀公的手中抢过政权,成为晋国民众的新主子,也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晋文公;同时,秦穆公好人做到底,送佛上西天,又把自己的女儿文赢下嫁给晋文公,延续所谓的“秦晋之好”,希望借助政治联姻的途径,笼络住晋文公,让他成为秦国争霸中原事业中的一颗过河卒子。秦穆公的想法很单纯,也很天真:“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打从这儿过,留下买路财。”你晋文公既然受了我的大恩大惠,加上大家又有这么一层翁婿关系,难道可以知恩不图报?常言道,“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你晋文公总得多多少少买我的面子,替我办点实事吧?
遗憾的是,秦穆公过于乐观了,简直是白日做梦,异想天开。他忘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既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永远不变的利益。他自以为对晋文公有过恩惠,人家就得图报,对不起,只要牵涉到利益,世上恩将仇报、以怨报德的事情可多了去了;他自以为自己是晋女公的岳父大人,人家会顾及温情脉脉的面子。对不起,为了利益,父子反目、手足相残尚且司空见惯,更何况是没有血缘的翁婿关系!眼下秦国想要染指中原,争夺霸权,势必要越渡黄河,锐意东进,而晋国要独霸中原,号令诸侯,也势必要紧紧关上秦国东出的门户,将秦国的活动范围死死地框定在西北一隅。这方面两国之间的利害冲突是根本性的,是绝对无法调和的。用今天的话说,便是所谓的“结构性的深层次矛盾”。在这个时候,什么恩德,什么姻亲,一概无效,全都给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而且秦弱而晋强,秦小而晋大,一旦双方真的撕破脸皮,闹将起来,处下风的肯定是秦国。秦穆公啊秦穆公,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也太天真、太一厢情愿了,居然会设这样的死局,会出这样的臭牌,真让人怀疑你的智商存在问题。
事实也正是这样,晋文公爬上宝座后,一门心思追求“取威定霸”,丝毫没有被秦穆公昔日的恩情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当然,他也不主动和秦穆公公开叫板,撕破脸面,在不触及晋国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有时也不忘拉上秦穆公一把,让秦穆公跟着自己露露脸儿,抖抖威风。但在晋文公心中,双方的定位是明确无误的,即我晋国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你秦国只能当插科打诨的配角,彼此之间是老大与伙计的关系,绝对不容颠倒,就如同当今世上美国与英国的关系一样。
这时候,秦穆公才发现,自己以前的筹码都下错了,所花费的心血都被风吹了。他三助晋君的努力,结果只是加速了晋文公成为诸侯霸主的进程;他多次参与盟会,多次投入军事行动(包括城濮之战中派兵增援晋国,一起教训楚
国),也往往是名惠而实不至,全是在那儿傻乎乎替晋国的霸业添砖加瓦哪!
“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假如秦穆公的战略失误只是走到这一步,还不算是输得精光,血本无归,至少可以同晋国维系表面上的一团和气,弄好了或许还能从晋国那里分得一杯羹。可是,事实是秦穆公接下来的做法更加令人匪夷所思,更加错得离谱,他居然利令智昏,孤注一掷,想用武力来达到外交、政治所没有实现的目的,日暮而途穷,倒行而逆施,决心“霸王硬上弓”了,真是:软的不成便来硬的,“巧取”不成改用“豪夺”。
晋文公在世时,秦穆公深知对手的厉害,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即所谓“有贼心,无贼胆”。谁知天遂人愿,机缘凑巧,阎王爷让晋文公死在了秦穆公的前头。这一下,秦穆公便浑身上下来了精神,觉得可以玩一把世纪战略“大豪赌了。于是,他蛮横决断地拒绝了大臣蹇叔的劝诫,决定趁着晋文公易箦之际,大起三军,越过晋国境上,去袭击郑国,企图占领地处天下之中的战略要地,以作为自己称霸中原的前进基地,他一厢情愿地认为,晋襄公(在名义上算是他的外孙)刚刚登基,正忙于稳定内部,无暇顾及秦国方面的军事行动,所以,他在没有向晋国借道的情况下,派遣孟明视等三位大将,统率300辆战车的兵力去偷袭郑国,以圆自己的霸主之梦。
劳师袭远,兵家大忌,弃信背盟,庸人短视。结果可想而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但没有把郑国给打下来,反而偷鸡不着蚀把米,秦军在崤山一带让晋国的伏兵杀得大败,300辆战车全部报销,“匹马只轮不返”,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这三位统帅一个不曾走掉,悉数做了晋军的俘虏。而秦晋两国之间保持多年的传统友谊,也随着崤函山谷中刀戟喊杀声的响起而烟消云散了。这真可谓是“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
更为糟糕的是,秦穆公似乎有心理障碍,脾气古怪而又偏激固执,见了黄河仍不死心,撞了南墙仍愣不回头。在他看来,姥爷让外孙这么给“修理”,实在太窝囊,太没面子,非得翻过盘来不可。于是为报崤山惨败之仇,他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动用军队去找晋国的晦气,结果是越输越惨,在彭衙(今陕西白水东北)之战中又让晋军杀得一败涂地,惨不忍睹,使秦军成了名副其实的“报赐”之师,距离当中原霸主的目标乃是越来越远,遥不可及了。尽管他后来转而同楚国结盟,企图通过南北夹击,将晋国从中原霸主的宝座上掀翻下来,来一个“新桃换旧符”,但是他这么做,除了让楚国渔翁得利之外,对自己实现光荣的霸主梦想,可是半点儿帮助也没有,干的还是替别人火中取栗的傻事,到头来,依旧是个跑龙套的角儿,一点儿长进都见不着。秦穆公战略眼光之差劲,实在是让人难以恭维。
编辑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