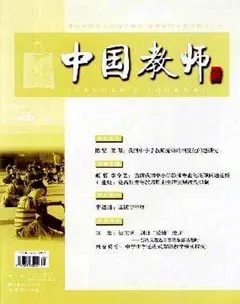孔子如何对学生进行知耻教育
中华传统耻感文化源远流长。孔子的思想和学说,沿承夏商周的文化大流,继往开来,成为耻感文化的源头活水。
在较早的经典古籍《诗》《书》《易》的一些文字中,已经体现出耻感意识。《书·说命下》把人内心对羞耻的体会与感觉形象地表达出来:“其心愧耻,若挞于市。”意思是内心惭愧和羞耻,就像在街市上当众挨鞭子一样。《诗·蓼莪》以酒器中没有酒为酒器之耻,比喻不能奉养父母的羞愧:“瓶之罄矣,维罍之耻。”《书·说命中》把过失当作耻辱:“无耻过作非。”意思是不要觉得有错可耻而文过饰非。而在《易·恒卦》中,已将蒙受羞耻同不能很好地保持美德联系起来:“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尽管在这些经典古籍中已经反映出了耻感意识,但直到孔子,对耻的认识和理解才更加自觉,使耻感文化初步形成体系。孔子特别重视对学生进行知耻教育。他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礼记·中庸》)孔子把知耻和好学、力行并列在一起,体现出知耻在修身中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论语》中多次出现孔子对知耻重要性的强调以及师生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和应答,这么薄薄的一本小书,“耻”字竟然出现了十六次。这足以让我们从中领略孔子知耻教育的内容、重点和教育方法。
一、要求学生从知耻开始确立人的尊严和价值
孔子教育学生把知耻看成修身的起点。因为儒家认为,人类文明皆从知耻开始。人如果不知道什么叫羞耻,与禽兽有何区别?《礼记·曲礼》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正如孟子解释的,人无“羞恶之心”,就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人。知耻是人性的标志,因此,可以说知耻是一种底线伦理。不知耻就是不要脸,不要脸的人什么坏事、丑事、见不得人的事都干得出来,所以知耻十分重要。与别人相比,如能醒悟自身修养的差距,道德的缺失,并引以为耻,于是便会奋起、励志、进取;人若丧失羞耻之心,则会陷于麻木、堕落、苟且、萎靡。既然知耻对人生十分重要,确立人的尊严与价值,必须从知耻开始,进而提升精神境界,追求理想人格。
为了保持人格尊严,孔子要求竭力避免耻辱。如何避免耻辱呢?他教给学生的办法是:“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论语·学而》)恭敬待人,可以远离耻辱。遭遇耻辱,损害人格尊严,可谓人生之不幸,特别是奇耻大辱更令人难以忍受。孔子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是:“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礼记·儒行》)宁可被杀头,也不蒙受耻辱,实现这种道德践履,需要极大的勇气,所以知耻为勇。孔子树立的这种道德人格,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学生们完成学业后都是要做事的,孔子又教育学生,无论做什么事,特别是那些需要承担重任的,要时刻对自己的不当行为保持羞耻之心。子贡问老师:“怎样做才可以称得上士?”因为子贡口才好,能言善辩,长于辞令,是搞外交的好材料,老师就以出使外国为喻来回答这个问题:“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意思是维护国家尊严,光靠能说会道不行,首先要有廉耻之心,用坚定的操守约束自己的行为,才有可能不使君命受辱。士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其角色是大道的承担者。孔子是这一传统认识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他在这里强调的是,承担天下重任的人,必须做到“行己有耻”。
二、教化民众知耻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的思想
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以仁为实质内容、以礼为制约形式的德治社会。这种理想社会的建立和维持,主要依靠的是贤德之人和道德榜样,而不是靠刑律和严苛的处罚进行统治。所以,孔子向学生灌输这样的思想:“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意思是用行政命令来统治民众,用刑法约束他们,这样民众虽然能暂时避免犯罪,但并不知道犯罪是可耻的;如果用德引领民众,用礼来约束他们,这样,民众就会知道羞耻,心悦诚服,并进一步革除自身可耻可羞的行为。
孔子理想中的社会是一种和谐社会。建设这样的社会,依靠政令和刑律虽然有成效,但其作用是有局限的,因为这种治理方法不过是用外在的强制力量,起到震慑作用,老百姓害怕了,收敛一下,暂时不去犯罪罢了。社会的这种和谐是表面的、不稳固的,建设和谐和稳固的社会单靠强制是难以实现的。只有对民众进行教化,使他们知道什么叫羞耻,一心想着趋荣避耻,去恶为善,从而自觉地遵从道德原则和社会规范,才能使社会实现稳固的和谐。
孔子向学生灌输这种思想,目的是为他们日后出仕从政,建设儒家理想的社会,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子游在武城做官,就是按老师的教诲,着重对民众进行礼乐教化。有一次孔子来到武城,听见弦歌之声,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莞尔笑曰:“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孔子诙谐幽默,和学生开了一个玩笑,这正是对学生学以致用而发自内心的表扬和肯定。
三、对学生强调知耻才能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孔子对“义”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义者,宜也。”(《礼记·中庸》)“宜”即应该做的、符合道义的事。通过“行义以达其道”(《论语·季氏》),而“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孔子要求士人勇于承担起社会责任。那么,见义勇为的初始动力由何而来?孟子的解释是:“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人之所以勇于行义,由羞恶之心而来。
孔子要求学生勤奋好学,坚定信念,矢志于道:“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在国家和社会迫切需要有为之士施展才能,做出贡献的时候,却以种种借口放弃这种责任,见义不为,就是莫大的耻辱。孔子要求学生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是否知耻不仅关系到个人品行和人格,而且关系到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兴衰。龚自珍说过一句很有影响的话,那就是:“士皆知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明良论》)
另一方面,政治黑暗,难以施展抱负的时候,孔子教育学生应做出不与世沉浮、同流合污的选择,避免蒙受耻辱。学生原宪向老师请教关于耻辱的问题,孔子回答:“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孔子的意思是:“国家政治清明,可以做官拿俸禄;相反,国家政治黑暗,俸禄照拿不误,这就是耻辱。”孔子的话对原宪形成了烙印性的影响,原宪对于孔子的教诲终生恪守。孔子去世以后,他感到天下无道,便隐退山野,过着清贫的日子,坚守节操,不与当政者为伍。孟子继承和发挥了孔子这一道德思想,概括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这一仕进原则,一直被后世知识分子奉为圭臬。
四、在知耻教育中对学生进行的具体行为指导
孔子对学生的知耻教育,不停留在空洞的说教上,而是辅以具体的行为指导。他首先要求学生善于区分什么耻、什么不耻。人都是要脸面的,但看你要什么样的脸面。比如向地位比自己低的人求教不算耻,像孔文子那样“不耻下问”反倒值得赞扬。孔子认为,不同的人,耻感的境界也有高下之分。平常人更多地在细节上考虑荣耻,而对志士仁人的要求则不然,不诚实守信才是士的最大耻辱。在《论语》中,孔子多次强调了这个问题。如:“君子耻其言过其行。”(《论语·宪问》)“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意思是古人不轻易把话说出口,因为他们以说到做不到为可耻。又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这说的是:“花言巧语,伪装和颜悦色,低三下四过分谦恭的人以及表面上装出友好的样子,却把怨恨藏在心里的人,左丘明以为可耻,我孔丘也以为可耻。”
孔子又对学生强调对耻的自我体验,从而发挥道德主体的能动作用。学生中有人因贫穷而自卑,以穿粗衣、吃糙食为耻,于是孔子提醒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孔子特别观察了子路的行为,表扬他说:“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论语·子罕》)意思是“穿着破旧的棉袍和穿着华贵皮袍的人站在一起高谈阔论,并不觉得羞耻,大概只有子路吧?这就是《诗经》上说的‘不嫉妒不贪求,有什么不好呢?’”子路受到表扬,有些得意,时不时地把这两句诗挂在嘴上,念诵个没完。孔子听说了,又批评说:“是道也,何足以臧?”意思是仅仅是这样,怎么能算最好呢!可以看出,在伦理教育中,师生展现了思想认识上的真情互动,细致入微。孔子对子路的表扬和批评,抓住了青年人的心理特点,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人生际遇不同,贫贱困厄不足为耻,人与人相比较的应是道德境界的高低。道德自信,不随流俗,不慕虚荣,也是一种勇气。孔子对学生知耻教育的细节,弟子们日久回忆起来,仍然历历在目,可见影响之深。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