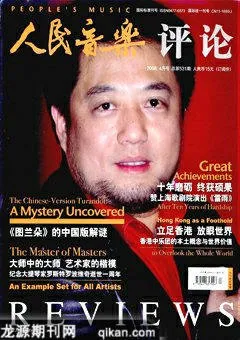通俗音乐与高雅音乐的对话
有关通俗音乐与高雅音乐的比较研究已经有很多,这些研究为我们认识并理解通俗音乐与高雅音乐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不得不说的是,我们的研究思维依然存在着一定的缺憾。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研究视角的单一。这使我们要么用高雅音乐的标准来规定通俗音乐,对通俗音乐横加指责;要么以通俗音乐的追求来衡量高雅音乐,对高雅音乐指手画脚,以致无法正视各自的特点。另一方面则是价值评判多于客观学理分析。这导致我们把注意力更多集中在价值的大小优劣的争论上,而没有意识到两者具有各自无法取代的价值。正如有人所言:“‘高雅’艺术的难度和复杂性首先被用来建立它相对于‘低俗’或浅白艺术的美学优越性。”①这里的“美学优越性”就是一副有色眼镜,它让人无法看清事物的真实面目。鉴于此,本文引入了对话的思维,通过流行音乐与高雅音乐的对话来彰显彼此的特质。
一
从时间上看,通俗音乐追求的是艺术的现时性和时尚性,高雅音乐则主要着眼于艺术的永恒性和发展性。
人们常说的“喜欢流行音乐是一时的事,喜欢古典音乐是一世的事”正印证了这一点。前者即代表通俗音乐,后者则是指高雅音乐。之所以说通俗音乐是“一时的事”,是因为它追求的“永远是现在”,表达的是一时的风尚,所谓“活着就是现在”(那英),“不想从前不谈未来”(王杰)。此外,时尚就像不定的风,具有多变的特点,当时尚改变了,人们就会去追求另一种符合当下时尚的通俗音乐,而不会长久喜爱某一种通俗音乐。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西北风”热浪到90年代“四大天王”的崛起,从校园民谣的风靡到“超级女声”的狂热,从刀郎的瞬间走红到周杰伦的独领风骚,通俗音乐的风格变了又变,原因正在于此。当然,高雅音乐也不可能脱离具体时代而存在,但高雅音乐除了带有时代特点之外,它还具有超越于这个时代的永恒的东西,比如对最高的人性、信仰、人的灵魂等的诉求。这些诉求不会因时代的改变而消失,而具有永久性。李斯特的话就说明了这一点,他认为:“真正的艺术作品,它们将永远保持着生命力,世世代代地流传下去。由于这些艺术作品里贯注着人类心灵的重要本质,它们将能经受住一切革命的考验。”②这里的“真正的艺术作品”就是指高雅音乐,而“人类心灵的重要本质”就是指作品中永恒性的东西。由于高雅音乐中含有超越于时代之上的永恒因素,所以说欣赏它是“一世的事”,甚至可以说它是几世的事。我们可以以巴洛克时期的两位作曲家J.S.巴赫与泰勒曼的作品为例加以说明。那个时代,泰勒曼的名气要在巴赫之上,其作品比巴赫的作品更受时人的欢迎,因为泰勒曼作品富于装饰的罗可可风格更符合那个时代人们讲究精巧、细腻的时尚追求,正如有人所说:“在一生中,泰勒曼都醉心于法国式的舞曲和个别乐段的奇特法国标题。……这些都是法国时尚的表面现象”。③巴赫则坚守自己的创作原则,没有应时而动,音乐丰富而内在,表现了一种永恒的东西:超越时代的不变的信仰。有人认为“巴赫一生创作了极多数量的音乐作品,有教堂内用的音乐,也有一般演奏厅中演奏用的音乐。但他从来不认为他的任何一件作品是与实现他的信仰无关的,无论从他的《b小调弥撒曲》、《马太受难曲》中,或从他《十二平均律的钢琴曲》或《勃兰登堡协奏曲》中,都能体会出他对自己信仰的表白。在他所写的《管风琴手册》一书封面上,他就写到‘仅为崇奉至高的上帝——并使主的信徒们受到教益’”。④确实,信仰就是超越于具体时代的终极实在,虽然巴赫的作品被时人称为“老套的”、“过时的”,但在其后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甚至现当代均被奉为圭臬,其中的原因正是巴赫音乐中表现出的永恒性诉求。德彪西的评价同样十分中肯:“在巴赫的作品里,音乐保持着它的全部尊严,从不降低身份去投合那些被称之为‘爱音乐爱得发狂’的人的虚伪的感情的需要;而是以一种比较傲然的态度,迫使这些人,即使不崇拜音乐,也要尊重音乐。”⑤如果说泰勒曼的音乐代表的是通俗音乐,那么巴赫的音乐则代表的是高雅音乐,前者更多地受到当时人们的欢迎,而后者则更长时间受到人们的推崇。综上所述,通俗音乐追求的主要是人当下即时的体验,因而是多变而短暂的。而高雅音乐则更多地表现了人永恒的诉求,因此历经时代的检验而艺术魅力依然。
二
从空间上看,通俗音乐主要体现的是广度和零距离,而高雅音乐则更多体现出深度和距离。
由于商业利益的驱动,通俗音乐需要得到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年龄阶段的尽可能多的人的喜爱。而要得到尽可能多的人的喜爱,它就要尽量平面化,力求与听众零距离,所谓“平面的游戏”。因为具有深度模式和距离感的音乐是很多人接受不了的,它需要人生境界的提升和文化的积淀。此外,通俗音乐还要与生活零距离,或者说“音乐就是生活”,它亲身参与日常生活之中,传达人们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让听众感觉到音乐中所表现的自己也亲身经历过,与自己很接近,这样听众就会沉浸其中。比如李春波的《小芳》之所以那么流行,就是因为它让人回想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段生活。《一封家书》由于反映了客居他乡的游子写给爸爸妈妈的书信这样一个生活细节,同样引起了无数人的共鸣,歌曲结尾甚至出现了“此致,敬礼”这样的写实歌词。我们甚至可以找到通俗音乐与生活零距离的极端例子,比如《豆浆和油条》、《蛋炒饭》等歌曲。由于通俗音乐与听众和生活之间没有距离感,听众就不会跳出来加以反思,而是不加思考地一味接受并喜爱,所谓“跟着感觉走”。相对于通俗音乐,高雅音乐则体现出深度和距离感。我们经常所说的“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距离产生美”,指的就是高雅音乐的深度和距离感。由于高雅音乐不是平面化地展示现实生活,而是带有反思地看待现实生活,甚或批判现实生活、给出理想生活,于是深度和距离感就产生了。正如有人所说“如果说‘完好无损’的牛仔裤所包含的是当代美国共享的意义,那么,将之损坏变形,便成为使自身与那些价值观念保持距离的一种方式”。⑥审美距离的产生相应带动审美姿态的换位,这时如果听众用欣赏通俗音乐的直观的、不假思索的方式来欣赏高雅音乐,就很难理解高雅音乐。由于很多能欣赏通俗音乐的听众无法欣赏高雅音乐,高雅音乐的听众就自然比通俗音乐的听众少,所谓“曲高和寡”。而听众要想听懂具有深度的高雅音乐,自己也必须要有深度,这就要求他的人生境界、文化水平必须要提高。下面这段话很好地阐释了通俗音乐与高雅音乐的差别:“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趣味的主要差异是‘距离’和‘参与’的差异,中产阶级的‘距离’是一个双重概念,因为它一方面指读者与艺术作品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指作品与日常生活琐事之间的距离。相反,工人阶级的趣味倾向于参与,也就是说,读者参与艺术作品的体验,而艺术作品参与日常生活文化。中产阶级的美学要求艺术的评判标准依照人性与美学的普遍性,而不是此时此地的特殊性。”⑦这里的中产阶级显然代表高雅趣味,而工人则代表通俗趣味。“人性与美学的普遍性”即指带有深度和距离的高雅音乐的审美方式,而“此时此地的特殊性”则指零距离、平面化的通俗音乐审美方式。
当然,通俗音乐与高雅音乐的界限并非是绝对的,有时也会相互渗透,出现高雅音乐通俗化或通俗音乐高雅化现象。如理查德·克莱德曼用钢琴演奏的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陈美用小提琴演奏巴赫的《托卡塔与赋格》,以及现今的“新民乐”风潮等就是高雅音乐通俗化的例证。通过电声化的配器、速度均匀的节拍律动、华美的舞台布景以及非常规的演奏方式,这些过去的高雅音乐的深度已经被拉平,已经被演绎成了通俗音乐。此时此刻,判断力被愉悦所取代,永恒被瞬间所取代,有机被无机所取代,净化被过瘾所取代,韵味被震惊所取代,高雅音乐的深度模式已经被“此时此地的特殊性”所消解。反之亦然。
三
从所起的作用来看,通俗音乐主要给人以娱乐和消遣,满足的是人自然性的需要;而高雅音乐则可以提升人的人生境界和审美品位,满足的是人超越性的需要。
人们称通俗音乐这一行业为娱乐圈,可谓名副其实。娱乐和消遣是人的一种自然需要,有人认为“人类对于娱乐的需求如同对于衣食住行与传宗接代一样自然。”⑧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因为一个人为了缓解精神的压力和紧张,自然而然需要娱乐和放松。通俗音乐正是应人们的娱乐需要而诞生的。通过听通俗音乐,人们可以暂时摆脱紧张和烦恼,使身心得到调节和休整。可以说,现今娱乐圈、娱乐业之所以如此火热,正反映了人们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对娱乐和消遣的强烈需求。而为了达到娱乐和消遣的目的,听众就不想投入太多精力去听音乐。因此,这就要求通俗音乐必须在表现内容和手段上都做到简单、易懂,比如在内容上尽量贴近生活,拉近与大众的距离,在表现手段上则以人们比较容易感受到的旋律、节奏为主,而人们不易感受到的音色、和声、调性、织体等表现手段则放在次要地位。只有如此,听众才能得到真正的娱乐。高雅音乐与通俗音乐相比则起着不同的作用,平面的游戏和娱乐是人的一种自然需要,但不是人的唯一需要,提升自身人生境界和审美品位也是人的一种需要。一个人如果长久处于平面化的生活中,就会感到空虚、无聊、迷茫,于是便会产生一种更高的需要,或曰超越性的需要。高雅音乐满足的就是人的这一需要。听高雅音乐的过程就是不断更新、修改、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过程。对于生活阅历较浅的听者而言,他一开始很难把握一部艺术价值较高的音乐作品,但当他后来把这部作品听懂的时候,他的人生境界和审美品位就提高了一个档次。比如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对于一般听众而言就是很难把握的,因为贝多芬经过一生的思考后在这部作品中义无反顾地否定了他的过去,选择了信仰。对于很多人而言,以恨对恨、以黑暗对黑暗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贝多芬在这部作品里却告诉我们:无论世界如何充满黑暗、仇恨和痛苦,我都无条件地回报以光明、爱和欢乐。这,就是信仰的高度,惟其如此,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加温馨和美丽。显然,如果欣赏者理解了贝多芬这部作品的美学内涵,他们的人生境界和审美品位无疑也就得到了提高。由此可见,通俗音乐与高雅音乐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但它们都是人们所需要的,它们之间是相互补充的。
结语
通过对话,通俗音乐与高雅音乐的的内涵得到了更为合理的阐释。客观来说,短暂、时尚、简单、浅显、直白是通俗音乐的特点,而并非其缺点,因为这正是通俗音乐的追求;永恒、超越、复杂、高深、隐晦是高雅音乐的特点,而并非其缺点,因为这正是高雅音乐的诉求。只有如此理解,我们才能正视通俗音乐与高雅音乐,才能摆正两者的位置。从长远看,两种音乐对于我们都不可或缺,都是我们生命的内在需要,两者体现的是差异而非差距,只有特点不同,而没有优劣之分。因此在我们欣赏它们的时候,不是判断哪一种音乐好或哪一种音乐坏,而是看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样的音乐。比如一个人经历过一天紧张的脑力劳动后,去听贝多芬、巴托克的音乐显然不合适,他可以选择通俗音乐来放松一下自己的神经,而如果一个人很长时间处于空虚、无聊、迷茫的状态中,听一听贝多芬、巴托克的音乐可能让他受益匪浅。因此,过分强调通俗音乐或过分强调高雅音乐对人的发展都是不利的,会造成人的片面发展,只有通俗音乐和高雅音乐的共同作用,才能使人的生命得到健康、协调、全面的发展。
①[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杨竹山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页。
②[匈]李斯特.《论柏辽兹与舒曼》,张洪岛译,音乐出版社1962年版,第43页。
③[美]杰拉尔德•亚伯拉罕.《简明牛津音乐史》,顾奔译,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年版,第490页。
④杨周怀.《基督教音乐》,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112页。
⑤[法]德彪西.《克罗士先生——一个反对“音乐行家的人”》,张裕和译,音乐出版社1963年版,第34页。
⑥[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⑦同⑥,第163页。
⑧董天策.《传播学导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陈新坤 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金兆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