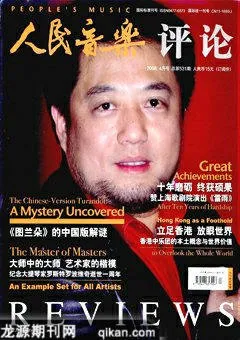民乐翘楚——香港中乐团
2008年1月28日下午,香港中乐团于国家大剧院的两场演出结束后,由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及《人民音乐》主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支持的“香港中乐团大型民族音乐会访演北京座谈会”于北京市前门建国饭店举行,两地的民乐知音尽情交流。会前一连两天,香港中乐团在国家大剧院献上了两套完全不同的曲目。1月26日的首场音乐会题为“从古曲经典到现代情怀”,上演五首于过往三十年由香港中乐团委约的经典作品,包括《十面埋伏》刘文金、赵咏山编曲,《忆》赵季平曲,《滇西土风:阿佤山》郭文景曲,《缘》吴大江曲及《乐队协奏曲》程大兆曲。次晚的演出题为“与你共乐”,通过台上台下互动,体现“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以人为本的精神,四首乐曲包括山西民间吹打乐《大得胜》张式业编曲,《昆虫世界》林乐培曲,《庆节令》王宁曲,幻想曲《秦·兵马俑》(彭修文曲)。
音纯曲精 专家齐呼震惊
围绕香港中乐团的演出水平、乐器改革、委约创作制度、乐团政策及行政管理、观众拓展和教育普及,以至于乐团的服装形象,在座的专家都发表了独到的见解,而就香港中乐团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阎惠昌的领导,众人也给予高度的赞赏。
“吃惊”几乎是当天的热门词汇,中乐团于两晚演出所表现的艺术水平,深受各方专家的击节赞赏,如指挥家卞祖善称赞:“如果说香港是东方明珠,香港中乐团就是香港的东方明珠。”《音乐周报》陈志音说:“香港中乐团的音色确实让我非常吃惊,我认为是独一无二的。”另外,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刘键巧妙地用电影剪接技术来比喻香港中乐团对演奏要求的严谨、专业,“几乎所有的细节,香港中乐团都能符合指挥心理的要求,这是令我震撼的,这在我们国内哪怕西洋乐器都做不到的事情,香港中乐团做到了。”“一句话:舒服、好听,是一种享受”是资深打击乐专家,原济南前卫文工团副团长刘汉林简单的总结。指挥家卞祖善的见解是:“国际一流的交响乐团最大的特征就是室内乐化,是那样的和谐那样的融合,我觉得香港中乐团已经达到了这个境界,他们的演奏已经室内乐化了。”作曲家郭文景则惊讶道:“我从来没有听见过一个中乐团、一个民乐团的声音是这么的纯净、融合,从来没听见中乐和民乐音质这样的好,演奏的力度、幅度如此的大。我就觉得乐团的合作水平已达到了民乐的顶峰。指挥对音乐的细腻、研究把握,都让我感到非常震惊,也非常高兴。听了这样的演奏你作为一个作曲家会产生强烈的为民乐写作的欲望。”作曲家刘文金有这样的总结:“我为他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而感到骄傲。从古曲经典到现代情怀,体现了这两场音乐会作品的广阔含量,也浓缩了香港中乐团三十年来在艺术实践和艺术积累方面的深度、厚度、广度和高度,这是海内外许多相同的乐团所难以模拟的。”
与会者对香港中乐团的音色无不称善,这得力于他们的乐器改革和对音乐至高境界的追求。中乐团设有研究及发展部,由阮仕春先生担任研究及发展部研究员、乐器研究改革室主任。香港中乐团此行所用的乐器,大部分都是经过改良的,其中最触目的要算拉弦乐器,他们用环保化工产品代替蟒皮,制成环保胡琴,又用以板膜共振系统发声的革胡和低音革胡,取代板震系统的大提琴及低音大提琴,支持以皮膜振动为主的拉弦组低音区域。由于中乐团所用的乐器与其它民族乐团有明显的区别,因而形成独树一帜的音响效果。阎惠昌总监于音乐会上讲解了乐团所用的改革乐器,在座谈会上引来不少正面的响应。首先,赵季平称赞:“中乐团的乐器改革蓬勃发展,而且把科研和艺术创作能够紧密结合起来,这次在国家大剧院用音乐的形式向大家宣传,而且让普通的观众了解到他们乐器改革的成果。非常可喜的这些成果具有环保的意识,对当前来说这是对改善人类居住环境非常有意义的尝试。”另外,中国音乐学院作曲家高为杰教授则十分欣赏弦乐器的改革,他说:“香港中乐团在这方面的实践,在目前来看是最成功的,保持了统一的中国弦乐的音色。我觉得香港中乐团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绩。”中国民族管乐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作曲家张殿英特别就革胡做出点评:“尽管他们改良的革胡还有不足之处,有待改进之处,但是我认为路子是对的,应该继续改进下去,能够真正改良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民族乐队的低音乐器。”就中乐团的乐改工作,很多专家都给予了正面的评价,国家歌舞团一级指挥杨春林说:“在乐器改革方面,我觉得阎惠昌先生的观念非常好。”而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副团长张高翔则表示:“民族管弦乐发展到今天,乐器改革已经阻碍了我们的发展,香港中乐团在这方面走在前头,而且非常系统全面,我们听到了现场音响的平衡,各个方面,我觉得是非常有成效的。”总括而言,中乐团这次演出已经成功以音响证明民族乐器改革完善了音色,同时也顾及了环保。
另一备受推崇的,就是香港中乐团的委约创作制度。香港中乐团对作曲家的尊重,对作品的开放态度、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获得众人的肯定。卞祖善认为:“作品绝对是音乐发展的核心要素,没有这些作曲家的作品,我们要建立自己的表演体系,理论体系,哪里来?都谈不上。所以我们应该向作曲家脱帽致敬,香港中乐团在这方面也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庆节令》的曲作者王宁于会上现身说法:“哪个地方想有什么样的要求,经作曲家指出后,马上乐队再奏一遍,再请你来指点。这样对作曲家、对作品严肃认真的态度,我在别的乐队里面好像没有接触过,作曲家在香港中乐团面前找到了上帝的感觉。”另外,赵季平说:“中乐团对作品的要求也非常高,有一种精品意识,不断的创新,积累精品。”由此可见,委约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广受肯定,如中国广播艺术团副团长艾立群说:“我感受最深的一点是,他们所有的作品都是本团委约曲目,但是我们在这方面相差很远。”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教授梁茂春指出:“这些作品甚至流传海外,今天走到哪里,只要有民族管弦乐队,都在演奏这些委约中的作品。林乐培的《昆虫世界》,吴大江的《缘》都是委约作品,都是精品,是香港音乐的里程碑,一直到现在听起来还能打动我们。”高为杰说:“花了这么大的财力、精力去委约作品,演出新作品,这个实践是了不起的。”在委约作品中,梁茂春则点评了《忆》:“这几场音乐会最感动我的是赵季平的《忆》,它是这场演出中间比较特殊的作品,很纯净,很深沉,很真挚,真正打动人的心灵。”此外,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系主任唐建平则特别点评了程大兆的近作《乐队协奏曲》“充分展示了民乐器各种各样的手段。”面对中乐团的作品宝库,他说“香港中乐团在这一点上,对中国音乐发展做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会被载入史册。”简而言之,不论从数字还是从质量上说,中乐团委约作品制度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这次香港中乐团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不止音乐受到注意,连服装形象也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的冲击。中乐团的乐师,不分男女,均穿上一式一样的蓝色大褂,白色的袖口。对于此种服装的意见各有不同。有些与会者认为这套服装不适合女性乐师。刘汉林说“女乐手,应该是穿旗袍。女士穿大褂,底下穿一个后跟很尖的高跟鞋,怎么看怎么不舒服。”《人民音乐》编辑部于庆新的比喻更具体:“中乐团最令我感到遗憾的就是这套服装,给人陈旧之感。女士与男士穿一样的长袍大褂,像尼姑一样,把我们漂亮的女孩子都弄丑了。既然是舞台艺术,就要考虑视觉艺术形象,应当为中乐团设计一款既有民族特色,又有时代感,富有朝气和美感的服装。”陈志音的见解却刚好相反“我认为香港中乐团首先给人的就是一种‘大和之美’,我还没有看到过一个中乐团或者叫华乐团用这样的服装。香港中乐团穿的长袍是很传统的,淡化了性别色彩,我认为找到了音乐家的尊严。”音乐毕竟是表演艺术,民族乐团应当在舞台上,甚或是国际舞台上展现一种怎样的形象,怎样的风采,这是摆在香港中乐团面前的一个课题。
秉善励行 管理备受推崇
从舞台出发,与会的专家还深入到幕后的管理及观众群的拓展方面继续探讨。首先,与会者都谈到了香港政府的角色,并且十分欣赏香港政府在财政及体制上对香港中乐团坚定不移的支持。财政上,如中央民族乐团团长席强所言:“香港中乐团在香港特区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下,是有资金雄厚的实力。”香港政府提供可靠的财政支持,确实免却其艺术发展不少后顾之忧。同时,体制上的明确和稳定性也是备受赞扬的。杨春林说:“香港政府对于文化事业的发展的政策是非常清楚的,其重要的目的就是提升居民的文化素质,在这样的政策基础上,香港整个文化事业发展是非常有序的。香港中乐团行政总监和艺术总监并行的这样一个机制,然后有理事会和政府的支持,这样三足鼎立的管理模式,积极促进了香港中乐团持续不断的发展。”卞祖善进一步认为:“香港中乐团应该给我们介绍一些管理方面的经验,体制方面的经验。”而且,他也很赞同阎惠昌对中乐团发展的愿望,就是“香港中乐团有一个音乐厅,具有中国文化音乐象征的编钟永久置于该音乐厅,成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象征,这个愿望太好了,在香港没有实现。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东方民族的音乐厅,把这个编钟永久性地像管风琴那样构置在音乐厅。”总括而言,与会者都认为香港政府的支持对香港中乐团的持续发展有积极意义。
另一方面,乐团的方针及管理也获得了与会者的认同。艾立群说:“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会特别关注香港中乐团的管理经验,有好的管理才会有好的乐团。”赵季平说:“香港中乐团的行动不是盲目的,它是在非常明确的理论指导下,因为它们有一批国内非常著名的音乐理/eczENc6A4xxrnVaYwVntA==论家在做他们的顾问,而且他们非常谦虚地吸取国内外各大乐团同行们的意见,甚至包括普通观众的意见。”同时,杨春林也十分支持中乐团的目标:“香港中乐团的业务发展很清晰的一个概念,就是利用本身业务的发展,为香港市民提供优良的文化大餐,用最美的音乐去熏陶和陶冶他们的情操,来提升整个香港市民的素质。”至于方针的落实,用王宁的话说:“钱总监的行政管理,极为有效。”有效的管理,往往守在幕后默默无声,然而从会上可见,中乐团即使是最静默一环,依然相当触目。简单概括中乐团在管理方面的成就,就如刘键所言:“香港中乐团就是我们的品牌,中国的品牌。”
有关乐团的营运,最后不得不提中乐团的观众拓展与教育普及工作。于庆新说:“香港中乐团在社会服务功能上,走的是一条多元化的道路。他们做了许多在我们内地是文化部、音协、教育部等部门应该做的工作。在香港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国际大都市里,香港中乐团在普及民族音乐文化方面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努力,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在演出过程中,指挥通过讲解和其它生动活泼的方式,与观众形成交流和互动,让音乐走进观众的心灵。”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杨青教授谈到,中乐团“有一个抱负,他更重要的是把自己扮成是所有香港人乃至中国人喜欢民乐的一个团体。我觉得他们做这些推广工作的时候非常辛苦,要演出,要到基层去,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喜欢中国的音乐,喜欢中国的民乐”。这一点上,前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朱卓建跟杨青有一致的想法,他说:“香港中乐团已经不是一个我们国内意义上乐团的功能,他已经成为香港民族音乐的核心力量,他组织了那么多活动,他成为了一个香港的种子,民族音乐的种子,他既培养出了高水平的乐队,又做了大量的普及工作。”对于香港中乐团的普及工作,赵季平的概括是:“他们把市场的营销和为社会服务紧密结合起来,把优秀的中华文化传播世界。尤其近十年来香港中乐团对香港中乐文化的普及和提高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敬业亲民 指挥别树一格
香港中乐团各方面的发展和成就获得认同,其成功必然得力于一位出众的灵魂人物——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阎惠昌。对阎惠昌指挥的细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刘键有这样的评价:“当他徒手的时候他的手是有魔力的,有非常多的语言,即便很小的一个动作,只带一点点预示的收,乐器收得非常干净。”他的风格,被认为有很强的亲和力。赵季平说:“阎惠昌的指挥非常有特色。他的特色区别于其它指挥的是他的视角是平民视角,有亲民的意识,和观众互动,与观众交流,不是仰视的,而是非常亲切的、朋友式的。”而人民音乐出版社副总编辑杜晓十教授更生动地说:“这次听音乐会感觉周围好多听众都不是专业的,但是他们都非常投入和激动,我觉得这就是他的平民化。”平民化的同时,质素是没有降低的,席强说:“从我看完音乐会后我的体会就是阎惠昌老师确实把香港中乐团带入了新的起点,新的高度,尤其乐队排练的严谨和方方面面的要求,确实是树立了一面旗帜。”作为乐团的掌舵人,阎惠昌所执的何止是小小的指挥棒?刘汉林对此的看法和赞赏特别深刻,他说:“我觉得要给阎惠昌总监立一等功,我觉得他的很多时间都在为中乐团操劳。这么大的事情,这么多的事情,他设计得多么好,从头到尾没有一点造作的感觉。这个成绩确实是惊人的,为什么?感觉就是阎惠昌热爱祖国,热爱香港,更热爱我们民族音乐,为弘扬民族音乐贡献出了全部的心血,是一位观众爱戴,同行尊重的国宝人物。”卞祖善认为:“香港中乐团今天达到的这种和谐、融合、连贯,整体水平是经过三十年磨合的。近十年我觉得阎惠昌总监的劳苦功高是功不可没的。”
三十载耕耘 成就有目共睹
国家大剧院的落成开幕令表演艺术工作者们好不雀跃。隆冬的北京,即使晴天朗日下气温仍是零下十多度,但我们内心的兴奋与好奇却十分热切。香港中乐团的精彩演出令我们为民乐发展到如此高的水平而骄傲。现在国内的民乐发展荆棘满途,有很多问题尚待解决。高为杰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一句老话。但是我觉得香港中乐团为我们做出了实践的典范。关于中乐、民乐、华乐这样一个乐团的讨论,学术研究,理论探讨已经有几十年了,我觉得香港中乐团用实践来回答了理论探讨当中遇到的很多问题,做出了非常好的回答。”香港中乐团这次在北京登台献艺,给民乐团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冲击。
正如于庆新所说:“作为一流乐团必备的四个条件,即指挥、演奏、创作和管理四个方面,香港中乐团是当今屈指可数的一流民族乐团,这是当之无愧、有目共睹的。”一个乐团的成功不单是个别的荣幸,更光耀整个民族。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朴东生最后总结:“香港中乐团三十年,尤其是后十年,获得了惊人的令人震撼的飞跃式发展,他们的成就不仅仅是属于香港中乐团,他们应当属于中国当代民族音乐界,他们辉煌的成就应该属于海内外的音乐人。他们展示的是中国民族音乐的魅力,他们展示的是中国民族管弦乐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