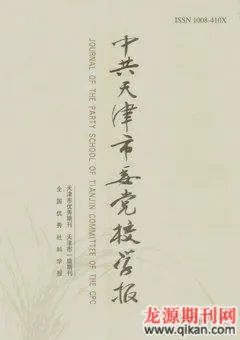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
摘 要:通过批判黑格尔肯定性的普遍等级概念,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是一个否定性的、革命性的等级。从实际历史的角度与实际变革的可能性来看,无产阶级的形成关键在于自身阶级意识的成熟。这涉及到无产阶级对现代社会经济规律的把握,以及由此而达到的对现代社会本质的把握、无产阶级的情感、对意识形态的反思以及相应的政治态度的产生等方面。只有通过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对于自身之存在以及社会之实际本质才会有真实、明确的把握。
关键词:马克思;黑格尔;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08)06003808
一、无产阶级的存在命题
自近代以来,社会主义运动的“幽灵”从西欧走向世界,无疑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对至今影响深远的社会主义思潮作出了重大贡献。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许多人错误地将马克思所谓的无产阶级等同于穷人,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无产阶级概念只是一种哲学虚构,无法从经验中找到合适的对应。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认为,马克思创造了一个“无产阶级的神话”。这至少说明了无产阶级理论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的主导性地位。那么,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这个问题首先不是一个经验的问题,它所指涉的主要是无产阶级的存在(being)问题,即首先并不是如何从经验上指认出谁是无产阶级,而是就其实际所是(what it is)或存在(being)来说,如何领会无产阶级之为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
实际上,关于无产阶级的存在命题是马克思首先提出来的。在《神圣家族》中,他指出:“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1](P45)这里,无论是黑格尔将历史看作是绝对精神实现自身的过程,还是基督教将历史看作是人类堕落沉沦、上帝介入人世、最终拯救人类的“救赎的历史”,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看来都是一种虚幻的“彼岸的真理”。马克思是用实践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考察历史的,从而建构了一种宏大历史观。正是通过回到历史活动本身的方法论,马克思揭示出历史发展具有某种必然性,而且这种必然性并非来自于远离人世的天国彼岸,而是内在于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中。历史是被实践着的物质的历史,而非纯粹精神的历史。所以,当“彼岸的真理”被揭穿之后,关键在于“确立此岸的真理”。无产阶级就是承担着这种确立此岸真理的历史使命、并为着这此岸真理奋斗不息的人,甚至可以说,无产阶级就是被世界历史选中的天命在身者。
二、无产阶级概念的缘起
(一)从等级到阶级
在1844年之前,马克思很少使用阶级(class)一词,而是使用等级(德文为“stand”,英文为“estate”)一词。关于等级的涵义,马克思认为:“差别、分裂是个人生存的基础,这就是等级所具有的意义。”[2](P346)在马克思看来,无论现代还是古代社会,人的生存基础就其现实性而言都是由等级奠定的。或者说,人们总是生活在等级之中,并通过等级获得自身之真实本质。从马克思的批判哲学来看,不存在抽象的人,只有被等级所规定的具体真实的人。后来在1843年晚期,马克思开始倾向于用来自法语的阶级(class)一词代替原来来自德语的等级(estate)一词。这一用词上的转换,主要是为了区别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不同特征,以及资本条件下新的等级制(hierarchy)与PuKxufD/9jkeHH5DD2b+jQ==古代等级制的根本不同。
在马克思看来,阶级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代现象,而等级则属于前现代现象。对于这种差别是否给予政治上的承认,是区别等级与阶级的关键因素。古代的等级同时也意味着相应的政治地位,而现代的阶级则保持着形式上的政治平等,虽然实质上可能是不平等的。进一步来说,等级与阶级的差异主要在于对人的身份认同(selfidentity)的意味迥异。在古代社会,等级的意义在于规定着个人的身份认同,正是通过自身所处的等级,人们获得自身实际的本质。在不同等级之间的矛盾尚未激化时,社会还可能是一个真实的共同体,等级之间各安其位,共同维系一种牧歌般的田园生活。而资本主义则将这种“田园诗般”的生活方式完全打破,使得过去的一切等级解体。马克思观察现代社会的深刻之处在于,封建等级的解体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平等,而是通过资本的力量,再次建构了新的等级制,而且这种现代等级制更严重的问题是,现代人不再能够从自身所处的等级中获得身份认同,对人来说现代意义上的等级完全是外在的。“现代的社会等级(指“阶级”——引者注)不像过去那样作为一种社会纽带、作为一种共同体来把个人包括在内,这就显出了它同先前的市民社会等级的区别。个人是否仍旧属于自己的等级,这一部分取决于机缘,一部分取决于本人所从事的劳动等等;这里所说的等级只是个人的外在规定,因为它不是从个人劳动的本质产生的,而且对个人来说也不是建立在硬性规定的法律之上并对个人保持稳固关系的客观共同体。相反地,现代等级对个人的实体性活动、对个人的实际地位毫无实际关系。”究其原因,“在市民社会中的其他一切规定,对于人,对于个人,都表现为非本质的外在的规定,尽管这些规定的确是个人生存于整体中所必需的,也就是说,它们是把个人同整体连接起来的必要的纽带,不过这是可以被个人重新抛弃掉的纽带”[2](P345)。
由此,在现代社会,资本摇身一变成了新的上帝,由资本规划出来的新的等级制却将人异化为金钱的奴隶,并在人的本质丧失之后还给出了一个新的填充物,进一步将人变成失去尊严的动物:“等级(这里指现代意义上的等级,即阶级——引者注)不仅建立在社会内部的分裂这一当代的主导规律上,而且还使人脱离自己的普遍本质,把人变成直接受本身的规定性所摆布的动物。”[2](P346)所以,马克思关于等级与阶级的区分主要在于将等级看作是前现代社会存在的现象,是古代意义上的阶级;而阶级则是一个现代现象,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是现代意义上的等级。这直接导致了马克思不再使用等级(estate)一词,而是将“阶级”(class)一词泛化,指称一切社会中的等级制。也就是说,在马克思后来的著作中,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阶级”一词:一是将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二是将阶级看作是适用于共产主义实现以前一切社会的一个分析范式或“理想型”。就后者而言,阶级分析法最终成为马克思解释共产主义前一切社会的基本方法。
(二)普遍等级:从肯定性的到否定性的
马克思对等级或阶级的关注,首先不是对市民社会中某些个别的、特殊的阶级的关注,而是着意于现代意义上的、整体的政治国家实际存在的问题。用等级或阶级的范式来分析现代国家,是马克思批判地继承黑格尔法哲学的一项理论成果。
在黑格尔看来,对于单个的私人来说,作为一个理念的人只具有抽象的本质,而人的本质抽象的形式要获得现实性,就必须成为等级的成员,也就是说,“人必须成为某种人物,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应隶属于某一特定阶级,因为这里所说的某种人物,就是某种实体性的东西。不属于任何等级的人是一个单纯的私人,他不处于现实的普遍性中。”[3](P216)等级是人的本质的现实性。由于需要的多样性而要求劳动与分工的不同,因而等级的差别产生于市民社会中。“无限多样化的手段及其在相互生产和交换上同样无限地交叉起来的运动,由于其内容中固有的普遍性而集合起来,并区分为各种普遍的集团;全部的集合就这样形成在需要、有关需要的手段和劳动、满足的方式和方法、以及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等各方面的特殊体系,——个别的人则分属于这些体系——,也就是说,形成等级的差别。”[3](P211)
就个别的私人来说,等级是一个“普遍的集团”,是由于其“内容中固有的普遍性”而形成的;而对于国家这种真正的普遍物来说,等级则是一种“特殊体系”,表达出特殊人群的特殊利益关切。在黑格尔看来,“从概念上说,等级得被规定为实体性的或直接的等级,反思的或形式的等级,以及普遍的等级”[3](P212)。一个合理的国家应当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国家,而国家的普遍性是通过一个所谓“普遍等级”得以体现的。由于等级是基于需要的多样性而出现劳动分工的不同,所以,等级首先是市民社会内部的概念;就市民社会内部而言,等级总是特殊的,标志着特殊群体的特殊利益。能够体现国家之普遍性的普遍等级,一方面必须具有某种普遍性从而才能真正体现国家之普遍性,另一方面只能从市民社会内部而来。他认为,“普遍等级(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政府中供职的等级)直接由于它自己的规定,以普遍物为其本质活动的目的。”[3](P322)虽然这个普遍等级的成员仍旧来自于市民社会,仍旧裹挟着个人对于私人利益的追逐,但“直接具有政治因素”普遍意义的公共事务,决定了只有这个等级才符合普遍等级的概念。于是,普遍等级首先是政治国家意义上的等级,超出了市民社会意义上的一般的私人等级,是“以社会的普遍利益为其职业”的等级,因而是体现国家之为国家的等级。由此,普遍等级的意义在从市民社会到政治国家的辩证否定运动过程中就具有双重含义:就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而言,普遍等级具有否定性;就其与政治国家的关系而言,普遍等级又具有肯定性。由于在黑格尔那里,普遍等级主要是用来体现政治国家之普遍性的,所以,黑格尔的普遍等级概念主要是一个肯定性的概念。若从实践的角度看,普遍等级的否定性就表现为一种否定的力量,也就是一种革命的力量;普遍等级的肯定性就表现为一种持存的力量,也就是一种保守的力量。
然而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政治国家概念只是一种抽象的建构,在这种抽象建构的背后,政治国家的普遍性维护的是市民社会的特殊利益,市民社会中存在的异化现象在政治国家中并未消除,而是以一种隐秘的方式被确定下来了。“政治国家即国家制度的形成……它是作为普遍理性、作为彼岸之物而发展起来的。所以,历史的任务就是要使政治国家返回实在世界,但是各个特殊领域并不因此就意识到:它们自己的本质将随着国家制度或政治国家的彼岸本质的消除而消除,政治国家的彼岸存在无非就是要确定它们这些特殊领域的异化”[2](P283)。市民社会没有扬弃为政治国家,而是上升为政治国家,所谓政治国家的普遍性乃是一种虚伪的、甚至是居心叵测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谓现代意义上的政治解放并不能使人获得真正的解放,而是导致一种真实而隐秘的奴役,只有实现人的解放超越政治解放,才能真正将政治国家的特殊性连同市民社会的特殊性一并扬弃,才能使人获得真正的解放。
虽然马克思尖锐地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理论,但在政治理论上仍然受到黑格尔的巨大影响。在将人的解放规定为“历史的任务”进而寻找人的解放使命的承担者时,马克思也在运思寻找一个具有否定性的普遍等级,即能体现出政治国家的特殊性、真正完成对政治国家的扬弃的否定性的普遍等级[2](P374375;63;95)。对于现代资本社会而言,这个否定性的普遍等级就成为一种否定的力量、革命的力量,这种等级的否定性与革命性是如此彻底,以至于它能促成一切等级的消亡,最终促成国家的消亡。因此,这个可以扬弃政治国家的否定性的普遍等级也是摧毁一切(包括自身)等级的最后等级。在马克思看来,这个肩负“最后的、否定性的、自我摧毁的”普遍等级就是无产阶级。
(三)无产阶级概念的提出
“无产阶级”(proletariat)一词,本是公元前6世纪罗马时期的用语。当时社会中最底层的第六阶级被称为“proletarii”[4]。在命名者看来,这个阶级对国家的唯一贡献就是生养了子孙后代(proles)从而为国家提供了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大生产背景下,“无产阶级”的使用与对新兴的产业工人阶级的分析有关。作为“工业革命的产儿”,新兴的“无产阶级”主要是指努力工作、辛苦劳动的作为生产者、劳动者的穷人,而有别于游手好闲的穷人。这一至关重要的区别背后隐含着一种道德控诉:当无产者通过努力工作和辛勤劳动仍不能获得相对体面的生活时,那么,他们不幸的原因就不在于懒惰或游手好闲,而只能到整个社会的制度和结构中去寻找了。
对此,马克思将无产阶级对社会和政府的道德义愤看作是一种客观意识。“这个阶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在被唾弃的状况下对这种状况的愤慨,这个阶级之所以必然产生这种愤慨,是由于它的人类本性和它那种公开地、断然地、全面地否定这种本性的生活状况相矛盾。”[1](P44)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就提出:“被剥夺了一切财产的人们和直接劳动即具体劳动的等级,与其说是市民社会中的一个等级,还不如说是市民社会各集团赖以安身和活动的基础。”[2](P345)这是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概念的最初端倪。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所谓的政治国家尽管表面上维护所有人的权利和利益,但实际上是以牺牲一个阶级的利益为基础的。这个阶级甚至被逼到了市民社会的边缘而不成其为市民社会中的一部分。当然,这个阶级就是由“被剥夺了一切财产的人们”所组成的那个直接从事具体劳动的阶级,也就是后来马克思所谓的无产阶级。
马克思首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概念,是在被称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宣言”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马克思从“德国解放”的主题出发,指出了“部分纯政治的革命”与“彻底的革命”的区别,也就是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已经提出的“政治解放”与“全人类的解放”的区别。他认为,在德国,“彻底的革命”或者说“全人类的解放”恰恰不是“乌托邦的空想”,解放的实际的可能性正在于在德国形成了一个有能力从事“彻底的革命”或者说“全人类的解放”的无产阶级,而不是一个可以从事“部分纯政治的革命”的资产阶级:“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答:就在于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形成一个非市民社会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一个由于自己受的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并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种特殊权利,因为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无权,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权……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2](P466)
那么,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概念其内涵到底是什么呢?与政治解放不同的全人类的解放又是如何规定无产阶级之为无产阶级呢?
首先,无产阶级是一个“把自己标志为社会消极代表”的阶级,它意味着人的全面丧失。这种丧失与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方式有关。在资本成为上帝的现代社会中,金钱主宰着一切,人的劳动发生异化,对只有劳动力的无产阶级来说,劳动就不再是一种体现人的本质的活动。而且在劳动的异化中,人与劳动产品、与自身、与他人、与自身的类本质都发生了异化。异化劳动正是人的类本质丧失的真正根源。这种丧失也与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理念有关,因为从抽象的角度看,无产阶级拥有政治上应有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但实际上无产阶级丧失了一切权利和自由。同时,这种丧失也从经济生活与政治领域上升到道德人格的丧失。劳动的异化与权利的虚设,使无产阶级丧失了自己的全部精神,他的人格、家园、本质、共同体以及他的人性。因而无产阶级实际上就什么也不是,或者说无产阶级就是虚无。无产阶级之所以是反社会的,就是因为社会本身不给他提供归宿,而是将他排斥在外;工人之所以没有祖国,就是因为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共同体,而是游离于共同体之外:“工人自己的劳动迫使他离开的那个共同体就是生活本身,也就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人的道德、人的活动、人的快乐、人的实质。”[2](P487)
其次,无产阶级所遭受的苦难具有普遍性,是个因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的阶级。无产阶级受到物的力量的奴役,是一个被彻底的锁链锁住的阶级。无产阶级的苦难源于资本的运行规律以及与之相共谋的现代社会本质上的不正义。因此,无产阶级所遭受的苦难是普遍的,表达出现代社会的一个本质特征。另外,无产阶级由于没有私有财产,也就没有特殊的利益从而也就不会成为一个特殊阶级。因此,无产阶级的利益也是普遍的,无产阶级利益的普遍性内在于其概念本身。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是一个普遍阶级。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无产阶级就是一个具有双重否定性的普遍阶级,它不仅是政治经济学内在矛盾的表现和对现存市民社会的否定,同时也是走向彻底革命和全人类解放的否定性力量。
正是通过打造黑格尔肯定性的普遍等级概念,马克思提炼出了一个否定性的普遍等级,是一个体现国家之是其所非、非其所是的等级,或者说是一个普遍体现现代国家本质上不合理性的等级,因而也是一个否定性的、革命性的等级。实际上,黑格尔在法哲学领域中运用的辩证否定逻辑也被马克思运用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从而提出每一种社会形态的变革都在于在其内部形成了这样一个否定性的普遍阶级:“封建主义也有过自己的无产阶级,即包含着资产阶级的一切萌芽的农奴等级。”[5](P154)“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正如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消灭一切等级一样。”[5](P197)把农奴阶级称之为“封建主义的无产阶级”,表明马克思把一切否定性的普遍阶级都称为无产阶级,或者说,无产阶级的概念在这里是被隐喻地使用,其含义就是“否定性的普遍阶级”。而把工人阶级的解放与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的解放相类比,表明马克思认为两种解放的逻辑基本上是一致的。
三、无产阶级概念与存在论问题
通过逻辑学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原理,黑格尔提出了普遍等级的概念。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也是在这样的逻辑框架中提出来的。因此说,无产阶级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穷人,也不是经验中的工人,而首先是一个对应于逻辑范畴的哲学概念。
在黑格尔看来,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客观精神的自我实现,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东西,所以,在客观精神的发展中,扬弃的历程将止于国家。作为客观精神之实现的理性的国家(rational state)自然就是一个普遍性的国家,是一个关乎普遍利益、代表普遍精神的伦理共同体。而普遍等级正是体现国家之普遍性的等级。而马克思则认为黑格尔意义上的政治国家实际上并没有到达真正的普遍性,所以,扬弃的历程仍将继续。无产阶级就是马克思为了扬弃政治国家之特殊性而提出的一个否定性的普遍等级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说,正是在哲学-逻辑学的意义上,无产阶级才是代表着普遍利益的,才不是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而成为一种否定性的或者说革命性的力量的。同样,当马克思说无产阶级的特殊利益就是全人类的普遍利益时,就既不是随意附会,也不是强词夺理,而是内在于辩证否定的逻辑框架中的。
黑格尔的逻辑学与普通的形式逻辑不同,关注的是存在论(ontology)问题。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也应当在存在论的论域中加以理解才是恰当的。所以,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实际上也关乎存在论问题。甚至可以说,只有在存在论的高度上去理解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才能真正把握到这一概念的真正内涵。
马克思曾说,无产阶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虚无”[1](P52)。这里的“虚无”也只有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才能被真正理解。无产阶级首先是被剥夺为虚无的,马克思曾将这种消极意义上的虚无称为“最令人绝望的唯灵论”[1](P52)。所以,马克思意义上的普遍等级是通过具体的无(被市民社会剥夺得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体现普遍的无(政治国家之普遍性的阙如)。当然,马克思并不将无产阶级看作是纯粹消极的虚无[1](P119),而是将无产阶级看作是一种积极的虚无,一种从根本上归属于存在的虚无,她聆听着存在的召唤,承担着变革的使命。或者说,作为普遍的无的体现,无产阶级的志向正是普遍的有(一个代表普遍利益的人类共同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才是一种否定的力量、革命的力量。或者说,无产阶级就其本性而言就是一种革命的力量。无产阶级就是高贵的、积极的虚无,这就是马克思通过存在论所给出的无产阶级概念的真正内涵。
既然无产阶级概念在哲学上有其根源,那么,从实际历史的角度与实际变革的可能性来看,无产阶级的形成实际上就是指无产阶级在实际历史中的出现以及她对自身之曾是、正是与能是的领悟。所以,从实际历史的角度看,在无产阶级由于现代社会本身的逻辑被必然地产生出来以后,最紧要的问题就在于无产阶级如何领悟到自身的真实处境、自身的过去与将来以及现代社会的真相与历史的真理,也就是,如何形成自身的阶级意识。
四、阶级意识的形成
从无产阶级概念的存在论内涵来看,什么是无产阶级的“正是”,即她的真实的处境呢?绝对的贫困,或者说人的本质的全部丧失。无产阶级不仅在物质上被剥夺得一无所有,而且在精神上也是赤贫者,她的本质,她的人性,她的家园,她的祖国,所有人之为人的东西,除了可以苟活的生命,全部被剥夺了。正是这种绝对的贫困,贫困的贫困,使无产阶级被迫陷入绝望的唯灵论,被迫陷入虚无主义。而在无产阶级身上失去了的那个“自己”,也就是“人的本质”或者说“人性”,即是无产阶级的“曾是”。无产阶级是人,但人的本质在他身上又被全部剥夺,这就是无产阶级的过去与现状,也是现代社会的实际状况。无产阶级唯一未被剥夺的,就是她的生命,被迫苟活的生命。“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这就是无产阶级的“能是”。本质是人,现在却被剥夺殆尽,但必将复归于人,这就是无产阶级对自身之存在(being)的领会。无产阶级就是要求自己解放自己、复归自身之本真曾是的生命。
然而,在实践的领域内,阶级意识的形成涉及到无产阶级对现代社会经济规律的把握,以及由此而达到的对现代社会本质的把握、无产阶级的情感、对意识形态的反思以及相应的政治态度的产生等方面。
马克思秉承黑格尔,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而由于在现代社会货币成为主导一切的力量,所以,人的劳动异化了。劳动者在劳动中与自己生产的产品、与劳动者自己、与人的类本质都发生了疏离。随着劳动的异化,人丧失了自己的全部本质:“人作为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因而这种劳动人每天都可能由他的充实的无沦为绝对的无,沦为他的社会的因而也是现实的非存在。”[6](P106)所以,对自身之为“充实的无”和沦为“绝对的无”的领会,就是作为劳动者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成的内容。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异化劳动是现代社会的必然现象,所以其后果并不是局部的或片面的。货币作为一种非人的力量是要“统治一切”的,表现为“对社会的、人的本质的普遍剥削”[6](P133)。质言之,在资本的左右下,不仅没有财产的、从事具体劳动的无产者被异化,而且拥有财产的资本家也被异化。正是在社会普遍异化、人的本质被全部剥夺的意义上,马克思才将共产主义标识为“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是人的本质对人来说的真正的实现,是人的本质作为某种现实的东西的实现”,并非着意于无产阶级单个阶级的利益,而是以全人类的普遍利益为其根本志向。那么,既然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样都是人的自我异化,为什么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觉悟者与革命者呢?
这里的关键在于,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作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1](P44)。有产阶级在异化中感到的是一种心满意足,所以他们不可能产生革命的意识。这就是说,当社会陷入普遍异化的泥淖,变革社会的关键因素主要就在于对社会现状的真实领会和把握,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种变革意识的形成。谁能够觉悟到现代社会异化的真相,历史的天命就会向谁呈现。但无产阶级对人的异化和非人的社会现状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情感上的愤怒和对社会的怨恨态度。这种道德上的义愤和怨恨心态一方面是与无产阶级对自身处境的强烈不满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也标志着在无产阶级身上所残存的最后一点人性,最后一点希望之火。“只要他们还对统治阶级感到愤怒,他们就仍然是人;但如果他们乖乖地让人把挽轭套在脖子上,只想把挽轭下的生活弄得比较过得去一些,而不想摆脱这个挽轭,那他们就真的变成牲口了。”[1](P400)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敌对不是一种私人性的敌对,无产阶级所追求的也不是某个特殊阶级的利益:“在原则上,共产主义是超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的……无产阶级对他们的奴役者的愤怒是必然的……但是共产主义比这种愤怒更进了一步,因为它并不仅仅是工人的事业,而是全人类的事业。”[1](P586)
这是因为,无产者最初与有产者一样,不仅在实际经济关系中处于货币的奴役之中,而且在心态结构也处于货币的奴役之中,同样是自甘为金钱拜物教的信徒。这种心态结构上的奴性意识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虚假意识”。但资本的异化力量却使有产者感到满足,使无产者感到痛苦,感到被毁灭,在这种被迫丧失的过程中,无产者逐渐明白强加于他们之上所有外在于他们的本质的规定性的真相,于是,资本的形而上意义和相应的伦理意义以及原来由资本所规划的社会等级秩序就会在无产者心中彻底破产。也就是说,由于资本的奴役,无产者在丧失一切的过程中也会丧失原本充满奴性的虚假意识。实际上,资本的奴役力量越强大,无产者失去的越多,他们就越有希望在意识上从他们原来认同的经济关系中摆脱出来,即彻底的丧失反而会带来彻底的希望:从阶级意识形成的角度看,我们可以说,无产阶级诞生于心灵从钱的毒化中被迫解毒,并回复到生命原本之为高贵的、积极的虚无的活力状态。在某种意义上,也正因为无产阶级能够在意识上从金钱的奴役中摆脱出来,无产者才是最解放、最革命的力量。“因此,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人的本质必须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这样它才能够从自身产生出它的内部的丰富性。因此,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6](P124)由此,无产阶级只有意识到自身就是虚无,而且是高贵的、积极意义上的虚无,是从根本上归属于存在之天命的历史性此在,她才能领悟到自身作为人的本质所是,才能从绝对贫困的绝境中看到一条希望之路:复归人之为人的本质。所以,这希望之路首先并不是无产阶级的一种幻想,而是从人自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内部的丰富性”。
阶级意识的形成也包括无产阶级的政治态度的形成。马克思甚至认为,无产阶级之形成为阶级,某种意义上就在于其政治因素的产生。他曾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来说明“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5](P157)。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无产阶级的成熟”、“潜在的无产阶级”等提法意味着阶级意识对于无产阶级形成为一个阶级的重要性。马克思想要强调的是,作为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阶级,无产阶级是在实际的政治斗争中形成的,也只有在革命实践中才能真正成长起来,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阶级意识的形成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觉悟。或者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无产阶级如何从一个自在的阶级转变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指出了无产阶级如何在资本的统治下从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中,这批人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5](P196)显然,自为的阶级就在于政治意识的觉悟。或者说,自在的阶级受外在的必然性左右,自为的阶级则受人类真实的必然性所指导。自在的阶级已然获得了该阶级之为该阶级的存在,但尚未获得对于自身存在的意识。自为的阶级则获悉了自身存在的秘密,对真实的命运与历史天命有明确的意识。对自身之存在与现代社会之本质的领悟,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形成的关键。阶级意识的形成首先并不是某个无关全局的特殊阶级内部的、只关乎特殊利益的一桩私人性的事件,而是关乎整个社会、关乎普遍利益、关乎人的本质的实现、关乎历史发展的一件公共事务。所以,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甚至认为无产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也能产生无产阶级的意识,也就是根本革命的意识:“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由于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必然与其余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这个阶级是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根本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当然也可能在其他阶级中形成,只要他们认识到这个阶级的状况。”[7]
这里就引出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即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的关系问题。尽管无产阶级所受的苦难是普遍的,但无产阶级的感觉却是私人性的、属己的。由于无产阶级的受教育程度往往很低,所以,要洞察苦难背后的真正根源,要理解无产阶级自身之所是以及社会之真实本质,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不可低估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马克思曾谈及无产阶级与批判哲学的“伙伴关系”,认为无产阶级与批判哲学的关系也就是人类解放的心与脑的关系[2](P467)。这就指明了只有通过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对于自身之存在以及社会之实际本质才会有真实、明确的把握。之所以知识分子能够成为无产阶级的启蒙者,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能够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而真诚合作,根本的原因在于,追求人的解放、人的本质的实现是人之为人的当然要求,从而一个关照普遍利益的共同体就是人类生存的共同渴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才成为一个革命性的普遍阶级,也正是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才与无产阶级形成“头脑”与“心脏”的“伙伴关系”。这就是说,在阶级与阶级意识之间,可能存在着许多不一致。一个特殊阶级可能对于自身的存在一无所知,但任何一个阶级都有可能从社会整体之普遍利益的角度领悟到另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阶级的实际状况,从而也领悟到这个社会的普遍本质。
从以上的梳理与分析可以看出,作为同时背负着苦难和自由的阶级,作为新文明的承担者,作为世界历史的选民,无产阶级形成的关键就在于阶级意识。无产阶级必须领悟到自身之所是,必须领悟到自身所属阶级的实际状况、地位和历史使命,必须领悟到自身就是高贵的虚无,自身就是历史性的此在,才能真正成为无产阶级。而任何一个阶级,尤其是知识分子,只要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存在论内涵,就会明确自身也可以成为积极的、推动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力量,也可以成为民族之天命的历史性此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4]DAVID W.LOVELL.Marx’s Proletariat:The Making of a Myth[M].Routledge,1988:72.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7778.
责任编辑:李 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