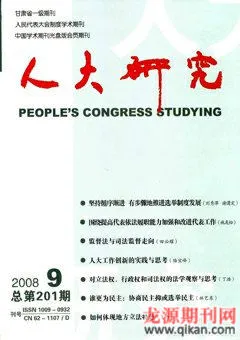内地与香港管辖权冲突协议应经过人大表决程序
内地和香港虽然属于同一主权国家,但却分属于不同的法域。随着两地民商事交往日渐增多,民事诉讼管辖权的冲突及其解决问题开始引起法学界的广泛关注。由于两地在民商事法领域没有共同的立法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所以无法直接通过统一冲突法或统一实体法的方式解决管辖权冲突[1]。内地和香港相继签署的《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的安排》(1998年12月)、《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1999年6月)和《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2006年7月)三项司法协助安排的有效实施充分说明,运用区际协议的方法解决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管辖权冲突应该是在现行宪法和基本法框架下一种可行又可取的方法。上述三项司法协助安排都是由最高人民法院代表内地与港方进行协商,并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发布后在内地实施的。今后在签订和实施区际管辖权冲突协议是否也可以采取这一方式?是否需要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的介入?如果需要,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应该如何分工?本文就从法律依据、效力等级和实施方式三个方面对区际管辖权冲突协议签订和实施中的这几个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一、区际管辖权冲突协议的法律依据
与现行的三项司法协助安排的法律依据相同,内地与香港为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签订区际协议也应该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九十五条“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通过协商依法进行司法方面的联系和相互提供协助”这一规定作为法律依据。该法律条文中的内地“其他地区”应指内地省级地区,但是如果由省级地区的高级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分别进行协商和签署协议,一方面会使协商较为繁琐,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出现内地各省级地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协商的结果不一致,仍然难有统一的效果[2]。所以应该采取签署三项司法协助安排时的做法,仍由最高人民法院担任内地的代表,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代表协商并签订协议。
二、区际管辖权冲突协议的效力等级
在内地,国际条约和国际协定在国内适用时是有效力等级的。凡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的,均具有与“法律”同等的效力——低于宪法和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凡由国务院缔结的,而不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的,均具有行政法规的效力——低于宪法、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3]。但迄今为止,我国法律尚没有明文规定区际协议在国内的适用问题,亦未作出参照国际条约适用的准用性规定。从法律渊源来看,在目前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法律体系中,区际协议还没有其应有的位置,本质上还不是任何形式的法律,因而在这两个法域的内部没有直接适用的效力,无法对抗内地法与香港法规定[4]。
三、区际管辖权冲突协议的实施方式
区际协议只有在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方式分别被内地和香港的法律接受后才能在各法域产生对内效力。那么,未来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签署了解决管辖权冲突的区际协议后,应该以怎样的程序和方式在内地实施?
1. 能否由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予以公布?
有学者认为,跟现行三项司法协助安排一样,民事管辖权冲突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代表内地与特别行政区政府进行协商,达成一致后,由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发布,在内地实施;香港特区由立法机关修改或制定相关的法例的方式得以实施[5]。笔者不赞同这种观点。未来两地关于管辖权冲突的区际协议在内地的实施方式不可以套用现行三项司法协助安排的做法,因为两者的性质明显不同。司法协助,除去国家主权因素之外,主要是法院之间代对方为一定的行为,只涉及法院自身的活动,对当事人并无不利影响,因而最高法院将这种司法协助安排作为对《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并无太大问题。但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如果就民事管辖权问题达成协议,必将与内地现行法律的规定有很大不同,以至于超出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所能涵盖的范围,所以不宜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予以公布。而且区际民事管辖权冲突协议属于对民事主体权利义务关系有很大影响的事项,同时也属于我国《立法法》第八条所明确规定的只能制定法律的有关诉讼和仲裁制度的事项,所以理所当然应该经过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的表决程序。
2. 是作为法律而通过,还是作为准条约来批准?
国际条约在国内的适用,我国倾向于直接纳入的做法[6],在国内直接适用,无需再通过国内立法使之转变为国内法。但区际管辖权冲突协议与国际条约不同,必须经过立法程序转化为内地的法律才能在内地法域范围内发生效力。也就是说为了使区际管辖权冲突协议得以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委会应该通过立法程序将其作为法律通过,而不是作为准条约来批准。如果只是以批准条约的方式批准了区际管辖权冲突协议,它的性质仍然是未经转化的区际协议,仍然无法对抗内地的各种位阶的法律。区际管辖权冲突协议在适用上必须经过立法程序的转化,这并不是出于垄断立法权的需要,而是由区际协议本身固有的缺陷所决定的。
注释:
[1][2][5] 胡宜奎:《内地与香港民事诉讼管辖权的冲突及解决方法》,载《江淮论坛》2004 年第1期。
[3] 张乃根:《重视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研究》,载《政治与法律》1999年第3期。
[4] 慕亚平、林昊:《防范“溢出效应”——探析CEPA中“香港公司”定义难题》,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11期。
[6] 王铁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426页。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法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