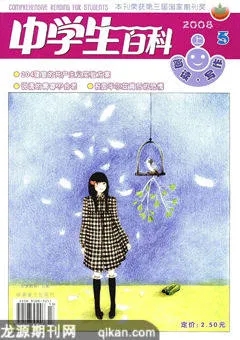我是一朵南瓜花
我是一朵南瓜花,可惜不是开在野地里的,而是开在一个农妇家的墙外,换言之,我是她种下的种子开出的花,所以我可能会失去寻找自己爱情的机会。
从我还是蓓蕾的时候起,就有两个异性在关注我,追寻我。一个是风雅,一个是蓝秋,是的,我们都有自己的名字,我叫蕊黄。他们两个拖着自己的瓜藤,拼命地向我靠拢。终于,我们的距离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而这一夜我们将同时绽放。
我更喜欢蓝秋,他对我的爱真诚,但也是含蓄的。而风雅,他的表达是直接的,他的爱来得汹涌,如正午的阳光。所有的南瓜花都知道他在追求我,他的这些做法跟他的名字很不相称。他和蓝秋在暗地里较着劲,我心里明白,自己将属于蓝秋。
清晨,我们都在朝阳下,绿叶间是一只只金黄色的喇叭,冲天空吹奏着。花瓣上是细细的绒毛,那上面托着一颗颗摇摇欲坠的露珠。对于我们,这是一个收获爱情的早晨,我期待着。
农妇带着她四岁的儿子来了,小家伙在瓜藤间蹒跚,那条叫黑子的狗跟在小主人的左右,撒着欢。我的心跳加快,因为农妇、儿子和狗在接近我们。我看到蓝秋又使劲挺了一下身子,他更醒目了,我盼着即将到来的幸福时刻。
黑子先窜了过来,它的头就在我的上方,舌头伸出嘴外,热气都哈到我脸上了。突然他抬起一条后腿,撒了一泡尿,那尿就撒在了蓝秋的身上。蓝秋趁着风势晃动着,但是没有用了。我一下子懵了,满眼都是蓝秋的绝望。农妇看到了黑子的所为,她大声呵斥着,黑子跑了,儿子去追。农妇毫不犹豫地掐下风雅,撸去他柔软的花瓣,拿着他套在了我的花蕊上。我看到了胜利者的微笑,但这不是我想要的爱情。我用力甩动自己的身躯,风雅差点掉下来。农妇回头发现了风雅的不牢靠,她弯腰扯了根细长的草叶,把风雅往里推了推,用细草叶把我柔软的花瓣合拢,捆扎。就这样,我接受了人类给我安排的婚姻,我恨那只破坏了我爱情的狗——黑子。
农妇走了,她把过剩的雄花都拿走了,当然蓝秋除外。这让我更痛苦,我能想象他看着我跟别人成亲,是怎样的难过。但是他什么也没说,正午的时候,他无奈地耷拉下头。第二天就奇迹般地脱落了,他提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却留给我一个信念:好好活下去,快快长大。
不管我愿不愿意,我成了一个大肚子南瓜,南瓜叶已经掩盖不住我的身躯。农妇每个早晨还来,还在按自己的意愿帮我的同类设计爱情和婚姻。黑子再没有把尿撒到其他的花上,渐渐地我觉得这都是命运的安排,便不再为曾刻骨铭心的爱感伤,别奇怪,在这一点上我们比人类潇洒多了。农妇怕我太招摇,扯了几把青草盖在我的身上,显然她对我是很重视的。
我开始编织另一个梦,那就是离开这里,到大城市去。我的妈妈是一颗从城里被带回来的种子,是见过大世面的。我记下了她描述的所有的都市生活,所以我向往着,希望有一天农妇把我摘下,卖到城里去,享受大都市的文明。
然而命运又一次捉弄了我,我还没有完全成熟,农妇就摘下了我。我想她是明白的,我虽然个子够大,但是并没有成功孕育后代。果然她的刀在切开我的时候,我的宝宝们还是瘪瘪的,她看都不看就把他们扔了,可怜我就没有了传人。她把我切成片,我知道做南瓜少不了挨刀的,因此我不怕疼,但是我心痛的是自己失去了进大都市的机会。
农妇把我分割完了,放到草木灰里拌了拌,然后把我放在一块大青石上晒。几天后,我的瓜片片们都干干的,卷卷的了。被集中在一个白布袋子里。我为自己这样的命运叹息,挂在屋檐下,我看到了季节的转变。当所有的南瓜都被收获时,我还在屋檐下看风景。
冬天到了,我被装在一个纸盒子里,送到了邮局,之后我坐上了火车,又换了汽车。尽管盒子里黑洞洞的,但是外面的喧闹是挡不住的,我知道我来到了都市。
从都市的邮局把我领走的是个女人,都市女人。她拿起盒子,轻甩到汽车的后备箱里。即使这样,那里面躺着的高尔夫球杆还是踢了盒子一脚,我在盒子里感到了鄙夷。
我从盒子里被倒出来的时候头晕目眩,因为这里太明亮,太干净,太幽雅,太豪华了。我定了定神,知道这是高尚住宅里的奢华家庭的整体厨房。虽然听妈妈描述过,我还是惊呆了。我想起农妇做饭的地方:狭小,简陋,儿子和黑子在灶台和腿边打转。
都市女人年轻,漂亮。她用白嫩细腻的手把我洗得干干净净,和肉一起炖,肉的鲜美弄得我身上也香喷喷的。被端上餐桌的时候,我才看到男主人,他有点胖,保养得很好,吃起东西来和身边的女人一样优雅。他看到干南瓜片炖肉时激动了,还让女人开了瓶红酒。
我和红酒一起到了他的胃里,他不断地吃,不停地喝酒,后来女人恼怒地说什么前妻的时候,男人疾走。接着,我从他的嘴里喷出来,进了一个白色的陶瓷容器,即使那东西是镶金的,我也知道它的名字:马桶。
其他的事情我就不再知道了,最终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田野中,土地里。
只是,这次,这里的土地上伫立的是一群群大白菜。一个来采风的年轻诗人对着雪地里的大白菜说了一句话:挺住便意味着一切。
我在土里扑哧就乐了。
编辑/姚晟
- 中学生百科·小文艺的其它文章
- 成长的烦恼
- 我相信你的爱
- 如何与孔雀型朋友相处
- 校园华尔兹背后的恐慌
- 金牛座的星语
- 心动DE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