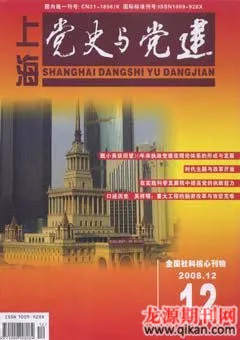麦卡锡主义时期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
当以极端“恐共”、“反共”为特征的麦卡锡主义在美国肆虐时,与共产党中国有牵连的机构、组织、学者备受打击和迫害。由此,现当代中国研究成了学术雷区。富布赖特(J.William?摇Fulbright)指出:“无论是在政府部门还是在政府部门以外的其他地方,撰述‘真实中国’情况被认为是一件非常不明智和不安全的事情。”①费正清(John?摇K.Fairbank)亦认为,“20世纪50年代有关中国的问题被弄得像令人恶心的食物一样无人问津,连狗见了恐怕也要掉头作呕。”②虽然如此,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却是在这一时期兴起的。
一、中共党史研究兴起之原因
二战后,随着美苏冷战加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及社会主义国家增多,麦卡锡主义思潮开始风行于美国。在麦卡锡主义思潮的推动下,美国习惯于用“是否是苏联阴谋”这种简单化、概念化的思维模式来看待错综复杂的国际问题。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共产主义新政权的建立以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美国政治精英几乎一致认定“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由莫斯科一手设计策划,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傀儡,完全听命于莫斯科”。1950年8月4日,国务卿助理杜勒斯在给艾奇逊的备忘录中言道,“很显然,现在中国的政府实际上是莫斯科的傀儡,接受其指导和帮助——事实上是受控于苏联的军事、技术和政治的顾问”;③1951年5月18日,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一次宴会演说中指出,“北平政府可能是俄国人的殖民政府……它不是中国的政府……它不是中国人的。”④国务卿艾奇逊在与英国首相艾德礼交谈时坚称,“中国共产党……是屈从于莫斯科共产主义的意见。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根据莫斯科的旨意。他们是比东欧卫星国更为理想的傀儡。”⑤杜鲁门总统在1951年的《国情咨文》中亦指出,“苏联帝国主义者……使用颠覆行动和内部发生革命的方法……煽动革命。这正是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国所干的事情。”⑥
美国各社会阶层也都普遍认同这一观点。罗伯特·诺斯(Robert?摇C.North)认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美国人都抱有这种幻想:中国共产党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共产党人,他们只是采取激进措施解决中国问题的土地改革者。然而,最近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已经粉碎了这种神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这场冷战中已坚定地站到了苏联这一边。现在,我们强烈地倾向于认为整个中国革命是由苏联人策划的。”⑦当时学术界还有其他很多人都持有这种看法。费正清曾提到,“我的许多同事和其他人多年来一直反复强调这是由莫斯科所指导的一次国际阴谋。”⑧学术界外,其他社会阶层亦如此。1949年,《纽约时报》刊发了一篇社论,认为“毛及其追随者们是一股由莫斯科委任的统治严密的寡头政治小集团。”⑨1950年12月的民意测验表明,“80%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受苏联之命参加朝鲜战争的,只有5%的人认为这是中国自己决定的。”⑩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已有所显露,美国多数民众仍认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由莫斯科策划的一次阴谋。1954年8月,盖洛普进行的民意测验显示,选择将共产党统治中国的主要原因归于俄国的压力和宣传的人数最多,超过三分之一。{11}
麦卡锡主义的这种社会氛围,激发了学者探寻苏联人如何操纵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趣。罗伯特·诺斯曾言及他开展中国共党史研究的缘由:“西方人更为关注的是新成立的共产党中国将不可避免发展为中苏集团。如果毛泽东宣称与苏联建立稳固的关系,西方世界将不得不考虑令人恐怖的共产主义帝国版图……所有这一切是如何形成?这当然涉及到许多因素,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复杂而又相互关联的。但是,在他们中间有一点尤为重要,因为非共产党人发现它是非常难以分析和理解。这就是由早期布尔什维克创造并专门设计用以指导在其它政府和民族行动的策略密码……如果能将苏俄操纵共产主义运动的策略、方式及其指导思想勾勒出来并加以消化吸收,那么西方世界不仅可以更好地判断共产主义者所想,而且还可能准确了解他们准备如何实现其想法。许多在西方流行的错误观念将被粉碎,西方政府和民众将能更好地预防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阴谋。”{12}
与此同时,一部分学者基于对传统中国的深刻认识,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不可否认与苏联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作为拥有深厚文化传统和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国,不会甘于受外来势力所操控,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绝不是像主流论调所想像的那样是完全受苏联操纵,这种论调忽略了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现实国情。事实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土生土长的,由中国人自己根据历史环境和现实情势为解决其自身问题而发起的一场运动,并不是莫斯科预先计划好的。费正清就认为:“中国的共产党是真正的共产党,并且他们以此自傲。他们与苏联的联系是文字上的、理论上的联系,并不一定是实际上的,手续上的,足以具体地证明他们与苏联维持密切关系的证据并不多,甚至稀少得使人感到惊讶……中国共产党政权非常明显的并不是莫斯科的傀儡,那是全部中国人组成的政权。”{13}为论证其观点,这些学者也对中共党史展开研究。
二、中共党史研究之概况
深信“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由莫斯科一手设计策划”的学者,他们在从事中共党史研究时,讨论和关注的主要是两个问题:其一,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和操纵;其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对苏俄的模仿。诺斯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即是如此。他的《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一书共15章,其中有相当篇幅是梳理苏俄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国共联盟的形成、国共分裂后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江西苏维埃政府的建立等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目的及结果。在围绕苏联通过什么方式或策略与中国建立联系展开论述时,他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在苏联领导的第三国际筹划之下成立的”;在北伐、国共合作中,苏联因素起着关键作用,目的在于“使得共产党得以与工农阶层建立联系并影响他们,从而为控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或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作好准备”;毛泽东的崛起、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江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同样与苏联相关,“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的决议,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第六届大会所通过的土地革命和农民武装起义决议经常被引用作为后来毛主义发展的证据,然而事实上它是由莫斯科事先设计好的。”在诺斯看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共产主义的一部分,它的最终目标是——一个苏联世界。”{14}
韦慕庭(Clarence?摇M·Wilbur),自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转向从事中共党史研究。他的中共党史研究同样试图从学术上佐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苏联人操纵的。由韦慕庭编撰的于1956年出版的《1918-1927年共产主义、民族主义以及苏联在华顾问的文献》即是例证。该著是一部文献资料集,包含两部分内容:50份有关1918至1927年期间中国革命的档案文献以及这些文献资料的历史背景。韦慕庭选择从事此项研究工作,主要是基于1918年至1927年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段至关重要的历史时期”,这段时期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对于理解最近的中国历史极其重要”。韦慕庭根据历史进程将这50份文献分成: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政策、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革命阵营的分裂与重新巩固、中国共产党关于群众运动的方针、冯玉祥与国民党和苏联的关系、北伐期间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等七个部分。从其分类来看,韦慕庭没有像之前其他文献资料的编译者那样,“只注重苏联代表在华的活动,而不管这些活动与中国政治的发展是否相关”,他强调“革命的中国部分”。韦慕庭之所以关注中国革命本身,其目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在研究中国共产主义之时,存在一种过于强调那些用于指导革命者行动的理论学说的倾向;另一种倾向即将主要注意力放在共产国际的领导层面。然而,这部文献所关注的是中国实际所发生的事件、政策理论制定的场景以及直接涉及的个人。这些虽然仅仅部分涉及到莫斯科制定政策方针的信息,但却提供了大量关于莫斯科所制定的政策是如何被忠实执行方面的识见。{15}
不满“共产国际阴谋论”的学者,他们埋首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的整理和分析。1948-1952年间,费正清同3个研究生发起翻译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文献资料的课题。之所以发起这项翻译计划,其原因在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是否是莫斯科的傀儡、如同东欧一样的卫星国,或是莫斯科-北京轴心的次要目标?毛泽东主席是否是潜在的中国铁托?近代中国真正的民族主义抱负能否与苏联轨道相吻合?莫斯科对于中国新统治者的影响力如何?对于美国政策而言,这些问题急待关注。这些问题一直以来是在缺乏坚实历史材料的情况之下加以回答的。”基于这种认识,费正清等人从大量中文、日文和俄文原始文献资料中挑选出40份代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意识形态发展重要阶段的关键性文献。根据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战略和学说的变迁,他们将这些文献划分为六个阶段:萌芽时期(1921-1923)、早期国共合作时期(1923-1927)、再定位时期(1927-1931)、江西苏维埃时期(1931-1934)、延安时期(1935-1945)、战后时期(1945-1950)。通过梳理,费正清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是根植于中国肥沃的土壤。传统秩序的破产和当代问题的迫切需要都呼唤激进的措施,马列主义恰好正符合这种需要”;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大致上取决于它适合中国舞台的程度、它适应中国需要和中国国情的程度,以及它利用中国特有机遇的程度。”费正清指出:“中国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一方面,近代中国的生活境遇是另外一方面,但是这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很明显,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如果离开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就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它能够建立就在于其为近代中国的现实问题提供了一种理智而富有情感的答案。”在费正清看来,“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只有根据中国的环境才能够被理解。因此,如果本书的读者不了解中国的情景和特有的环境,他几乎不能奢望能够理解毛泽东的思想或毛泽东的成功。”{16}
作为费正清的学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文献资料翻译计划参与者的史华慈(Benjamin?摇I.Schwartz),1951年出版了其成名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毛泽东的崛起》。该著在坚实的原始文献资料基础之上,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苏联之间的关系作出了完全不同于主流观点的分析和论断。史华慈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相关学说框架及其内部政治关系入手,着重考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兴起的原因、1923至1931年期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情况、毛主义战略学说形成过程及原因、毛主义战略学说的内涵及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信条的关系等四个方面的问题。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考察,史华慈认为,“毛泽东的政治战略不是莫斯科预先设计好的,甚至在这个战略最初明确时莫斯科仍然认为是与神圣不可侵犯的正统信条相违背的,只是形势的压力才最终导致莫斯科对这个新经验给予了合理解释的外表。”在他看来,“正统的斯大林历史学正在极力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描述成是斯大林的自我预设和巧妙计划的结果”,“奇怪的是,这个虚构信念已经被许多认为自己是克里姆林宫最仇恨的敌人的人所接受,甚至强调。然而,我们坚信,中国共产党的失败与成功一样,常常是未曾预先计划的。”{17}
三、中共党史研究之评价
麦卡锡主义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力求通过对原始文献的梳理和缜密分析,使其论述更具说服力。韦慕庭在整理1918-1927年期间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苏联代表在华活动的文献资料时,特别强调:“我们试图通过下面两种方法,考辨所收集证据的真实性:其一,外证法。即检查所有能够利用的外部证据,包括搜查的信息、文献出版的环境、就文献真实性发表过看法的个人证言;其二,内证法。这些文献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经受住历史性的详细审查?他们是否暴露出使他们受到怀疑的错误、矛盾和时代错误。”{18}史华慈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意识形态学说史的探寻,完全建立在对中国共产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文献解读基础之上。该著引用了中共一大至六大的决议宣言、八七会议决议、共产国际致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李立三的报告、周恩来的报告、苏维埃宪法等原始文献。
二战期间,美国新闻记者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共产党及解放区的著作。这些著述大多是描述性,且缺乏对历史文献资料的考证以及在此基础之上深入透彻的分析。罗伯特·诺斯批评道:“许多具有在共产主义地区亲身经历的作者都将其看到或听到的事件作了真实记录。但是,这些著述并未将中国共产党内部状况及其思想理论展现出来。”{19}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美国学术界有关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仍然是乏善可陈。《远东观察》于1949年7月在刊发两篇中共党史的文章时,特意添加一段按语:“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世界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一种中国人所独有的现象……但很少有美国人对此进行过严谨的研究”。{20}麦卡锡主义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由于研究者注重对中共党史原始文献的解读,从而使得这一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不同于新闻记者所写的新闻传记,成为中共党史研究从“新闻传记”走向“学术论证”的界标。
但这一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具有鲜明的麦卡锡主义烙印。罗伯特·诺斯、韦慕庭等人的中共党史研究,是一种“反共情绪的反映”,表明其像美国主流社会一样,“对于莫斯科-北京结盟这一对世界产生极大影响的令人生畏的十字军讨伐运动的恐惧心态。”正如马克·赛尔登(Mark?摇Selden)所说:他们的著作大都着眼于共产国际的阴谋,而置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根源于不顾。与美国政府对铁板一块的,由莫斯科操纵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谴责相呼应。{21}费正清、史华慈等人的中共党史研究,在于解答中国共产主义同苏俄的关系,驳斥共产国际阴谋论。基于此,史华慈在研究过程中既不是着眼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客观社会和政治环境,也不考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对群众的影响或中国传统文化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而是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具体细节。他关注理论细枝末节的原因在于:“当时,人们不得不对付约瑟夫·斯大林,他被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永远正确的全面解释者和‘运用者’。这包括这样一个意思:中国革命的胜利全靠斯大林同志在理论上的亲切指导。现在,我(史华慈)坦白承认,我曾对斯大林作为永远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运用者抱有怀疑,而且这种怀疑也许引导我对这种永远正确的指导总的感到怀疑。”{22}
总而言之,诺斯、韦慕庭等人的研究,力图证明“毛是国际共产主义的驯服工具,中国革命是莫斯科操纵的国际阴谋的结果”{23};费正清、史华慈等人的中共党史研究,则试图驳斥这种“共产国际阴谋论”的观点。原本是像一幅多维画卷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在这一时期却成为现实论争的直接反映。
注释:
①⑧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and Yesterday?摇: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