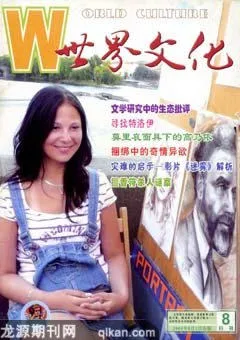柴科夫斯基死因揭秘
1893年10月28日,柴科夫斯基创作的《第六交响曲》由他本人亲自指挥,在圣彼得堡贵族会议大厅首演。由于乐团的乐手们不理解为什么这部作品的终曲写成了慢乐章,而不是像所有的古典交响曲那样是快速度,首演未取得预期的成功。11月6日,由经常指挥柴科夫斯基作品的捷克指挥家纳普拉甫尼克指挥第二次演出,人们才感受到这部作品的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可惜的是,柴科夫斯基永远也不可能看到这巨大的成功了,他已于当日凌晨3时离开人世。
柴科夫斯基之死令人们十分震惊。公开的说法是几天前他喝了一杯未烧开的水,得了霍乱,导致死亡。但也流传另一种说法,说他是自杀而亡。多年来,一直没有定论。
真 相
1920年,当年柴科夫斯基病重时的主诊医生、沙皇御医列夫·伯廷逊透露:柴科夫斯基是自杀的。他之所以要透露这个秘密是因为柴科夫斯基已去世27年,他认为柴的死因已无严守秘密的必要;并且他已年迈,这个秘密如再不揭示就将永远无人知晓了。
几乎与此同时,当年柴科夫斯基病重时日夜守护在他病床前的医生亚历山大·赞德尔也把柴科夫斯基死于自杀这一秘密透露出来。
1913年曾担任元老院上诉庭检察长的雅科比(死于1902年)的太太,向外界吐露了柴科夫斯基自杀的真相。她觉得自己年事已高,无权把这样一个重大而可怕的秘密带进坟墓里去。雅科比太太的讲述如下:
“1893年秋天,斯滕博克·费尔莫尔伯爵托我丈夫转交给沙皇一封信。信的内容是控告有同性恋癖好的柴科夫斯基对他年轻的侄子发生兴趣。在当时的俄国,法律明令禁止同性恋。伯爵控告的事如果被曝光,不但柴科夫斯基的名誉将遭受严重损害,也会使柴科夫斯基年轻时曾就读的圣彼得堡法律学校和柴科夫斯基所有的同班同学遭受名誉损害。为了维护法律学校和所有这个学校毕业生的荣誉,雅科比采取一个行动来阻止事件的公开曝光,他把柴科夫斯基和他以前在法律学校毕业的当时在圣彼得堡供职的8位同班同学召集到家里,举行了一个名誉审判会。当时我在客厅做针线活,听到书房不时传来时大时小的说话声,有时情绪很激动。这样的谈话持续了大约有五个小时,忽然看见柴科夫斯基愤怒地冲出书房,面色惨白、神情狼狈地向屋外走去,走了几步又站住脚,转过身来,向书房的人们鞠了一躬,然后一言不发地走了。其余的人在书房又交谈了很长时间才离去。雅科比要我发誓严守秘密,然后才告诉我,他们8个同学一致对柴科夫斯基说,如果他同意自杀,他们就可以不把致沙皇的控告信交给沙皇,否则的话,他将名誉扫地,难以像以前那样生活下去,还要受到法律的惩罚。一两天后,柴科夫斯基患病而亡的消息就传遍了圣彼得堡。
柴科夫斯基的自杀属被迫之说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1960年在列宁格勒第一医学院有关法医学的一个讲座上,柴科夫斯基之死就是作为被迫自杀的案例被引证的。这说明,柴科夫斯基被迫自杀的事实在某个相关机构是存有文字材料的。
内 因
柴科夫斯基的确有同性恋倾向。不过,他对异性仍有强烈的渴望。他曾在给弟弟安纳托里的信中这样说:“有时我会发疯般地渴望被女性的手爱抚。有时看见可爱的女性的脸庞,多么想把头伏在她们的膝上,吻她们的手啊。”可是,他有同性恋倾向确也是不争的事实。
虽然当时俄国法律规定:同性恋者被剥夺公民权并流放西伯利亚,但通常并不执行。许多皇亲国戚、高官显贵也都是同性恋者。既使是某位高级官吏的丑闻被众人知晓,不得不加以处置,也不会送交法庭审判,或流放到西伯利亚,通常只是将其放逐到偏远省份去。
何况沙皇对柴科夫斯基也并无恶感。1885年,沙皇家族观看了柴科夫斯基的歌剧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沙皇接见了柴科夫斯基,和他友好地交谈了很长时间,详细地询问了他的生活和创作情况,然后带他去见皇后。皇后也对他表示了令他感动的关心。
那么,他为什么要选择自杀呢?如果他足够坚强的话,他难道不可以选择另一条道路吗?
问题就在于他敏感、脆弱的性格,在于他一生中多次发作的抑郁症,包括1890年秋梅克夫人断绝了和他的友谊给他带来了精神的痛苦和抑郁,并因而损害了他的精神健康。他之所以要选择自杀,而不是选择另一条艰难地抗争之路,不能不说和他这种性格有关。在这之前,这种性格曾经导致过他的一次自杀。
1877年7月,柴科夫斯基和曾在音乐学院学习的安托尼娜匆匆地结了婚,婚后第一天甚至第一个小时,他就后悔他的轻率选择和不理智,因而陷入了极度的失望、厌恶和痛苦之中。两个多月后的一天夜里,他走进冰冷的莫斯科河,企图自杀,幸而未遂。
柴科夫斯基的敏感而忧郁的性格赋于他的某些音乐作品有震憾人心的悲剧力量,也给他的生活带来了灾难与毁灭。
外 因
根据柴科夫斯基的弟弟莫杰斯特对柴科夫斯基病症的描述,柴科夫斯基服用了砒霜。
他的同学们,那些法律界的高官和精英们,残忍地假借他自己的手,不露形迹地杀害了他,然后,他们害怕被人知道他们曾经逼迫过他,所以他们把真相隐瞒起来,公开宣称,他感染了霍乱。
为什么要把他们自己的老同学、举世闻名的伟大的音乐家置于死地呢?
《俄罗斯音乐之魂——柴科夫斯基》一书就此说:“柴科夫斯基是社会成见的牺牲品,是贵族阶层伪善、残忍、专横的牺牲品;而预谋杀人、私刑定罪的却正是一批专修法律,甚至是任职沙俄政府执法高官的人!”这种看法当然不错。可是笔者认为,既然法律并不过多深究,这些法律界的高官同学如对柴科夫斯基怀有好感,或仅仅是同情心,凭他们的智慧、能力和地位,完全可以使柴科夫斯基躲过这一劫。他们之所以要残忍地迫害柴科夫斯基,恐怕还有其他的原因。
1862年,柴科夫斯基厌烦了轻浮的社交生活和平庸的官员工作,辞去任职三年的司法部的工作,到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学习。涉足音乐界后,他更是与社会格格不入,罕与人来往,一副清高避世的姿态,这一切和他取得的举世闻名的成就,很可能引起了这些昔日同学的嫉妒心,当有一个机会可以让他们把他置于死地,以发泄他们对他的嫉恨心理时,他们就不肯轻易放过他了。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还需要用史实来证实它。■
注:文章参考毛宇宽著《俄罗斯音乐之魂——柴科夫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