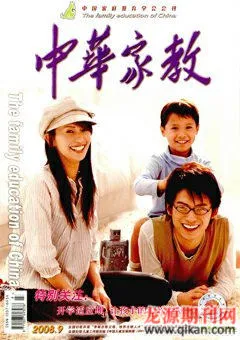孩子,那里有你的父亲
每当在街头看到蜷缩在路口、眼里充满期待的民工,酸涩会立刻充斥着我的心肺;每当走过尘土飞扬的工地,看到在烈日下或寒风中挥汗如雨的打工者,涌上心头的,便是他们在陌生的城市如何艰辛和卑微。因为,他们之中,有我的父亲……
曾经,我对父亲一无所知。他长年在外到底是怎样生活的?他一年比一年消瘦和苍老到底是为什么?他脊背上、手臂上的伤疤是哪儿来的?还有,他过得真的像信上写的那样“很好”吗?我一直以为,我没有必要为这些问题伤脑筋。我更热衷的是整日盘算着怎么说服母亲让我多看会儿电视,用什么办法来隐藏自己日益可怜的考试成绩,甚至买来假奖状寄给父亲,让他相信他的女儿依旧像以前一样优秀。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两年,直到我上初中三年级那年的冬天……
和往常一样,作业做了一半,我就坐到了电视机前。正在看电视的母亲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正当我庆幸又躲过了一次母亲的数落时,眼睛却被电视上的一幕深深地刺了一下。那是一排排水泥板搭建的简易民房,四面透风的小屋里挤满了端着水煮白菜狼吞虎咽的民工,我看得有些心酸。
母亲起身关了电视,注视着我的眼睛问:“很可怜,对吗?”
“他们真的不容易。”我应声说。
“那里有你的父亲!”母亲一字一顿地说。
正准备大谈一番感想的我,在那一刻脑海里一片空白。母亲不知何时走了出去,偌大的屋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霎时空落得让人心里难受。想起父亲,想起在被我可怜的那群人里居然有我的父亲,懊悔、愧疚、悲哀一起涌上心头。
我曾为小说中主人公的悲惨命运而慷慨洒泪,也不止一次对流浪在外、无家可归的孩童生出同情,唯独对我的父亲——这个世界上最疼我、爱我的人,冷酷得近乎残忍。他的关爱和付出被我视为理所应当,我肆无忌惮地向他索取了十几年。从可口的零食到漂亮的衣服,从小时候被我视为炫耀资本的零花钱到中学时几千元的学习和生活费用,从无微不至的关爱到今天所谓的自由空间……我的胃口越来越大,大到父亲日渐力不从心,大到他不得不离开家,到不属于他的城市挥洒汗水,像一只城市里的乡下鸟,不停地奔波,不停地找寻,找寻的,是女儿的未来。
他也许从来不曾想过,他“懂事”的女儿,竟会一面看不起他的同伴,一面心安理得地“骗取”着他的爱。他从不曾有过半句怨言,只因为我喊他“父亲”。也许他觉得,父亲的爱就该博大深沉,始终无言,却掷地有声。我一时无语凝噎,泪如雨下。
“那里有你的父亲!”就是这句话,让我两天后在志愿书上填上了重点中学的名字——重庆市一中。四面八方怀疑的目光让我清醒地认识到:3个月的时间补齐荒废两年的功课几乎是个梦想。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梦想,3个月中,我没有一天的睡眠超过4小时;就是这个梦想,让我一夜之间和过去被我视为知己的同学形同陌路;正是因为这个梦想,我手臂上为了防止犯困而用圆规扎的小孔不下100个。
终于,中考过去了,父亲也因工期结束回到家。见到我,他的第一句话不是问我的成绩,而是心疼地问:“丫头,怎么瘦成这样?”触摸着手臂上还隐隐作痛的千疮百孔,我告诉父亲,离重点线还差21分。父亲故作轻松地说,考不上,他就掏高价,反正他已经挣够了我的学费。望着父亲日渐苍老的面庞,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转过身,泪如雨下。
高中开学的日子到了,而我却又一次走进了初中校园。因为我要让父亲收到女儿的大红喜报,而不是拿出比别人多几倍的血汗钱。一年的时间转瞬即逝,我付出了所有的努力,而父亲,一直混迹于千千万万的民工中。酷暑难当的7月来了,父亲也从遥远的深圳赶回了家,当他得知我以超出重点线28分的成绩被重庆市一中录取时,又黑又瘦的父亲笑了,我却哭了。我仿佛看到在归家的民工队伍里,父亲的脸上写满了急切和期待。站在一旁的母亲用手指向人群,充满安慰地说:“孩子,那里有你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