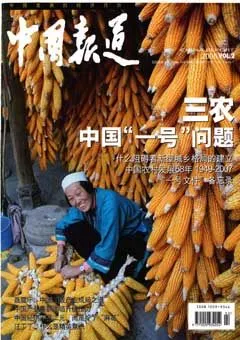“多分一些‘南水北调,长江水 ”
丁亥年的岁尾,温暖的阳光倾洒在河南安阳宝莲寺镇南田村宽阔整齐的水泥路上,不时有汽车和电动摩托车来来往往。路旁,有粉刷整洁、修葺一新的南田中学,有新建的排排两层小楼、百货商店,有设施齐全的新衣合医疗卫生室。再往前,京广铁路、107国道穿行而过。村西不远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在有序地施工建设。
在这个中国的传统新年里,村民们在前所未有地感受着改革开放三十年给农村带来的深刻变化,同时对新的一年也有了更多的期待,只是年的味道对大多数人而言,不再像过去那样浓烈。
小磨坊的大变迁
“现如今,城里人过年好吃这个粗粮,管这叫忆苦思甜!不少农村人也赶这个时髦!”
58岁的南田村村民郑金章对于农历新年的期待远不如二十多年前那么强烈而实在了。这种期待消退的直接原因,源于跟老郑有着二十多年特殊感情的小磨坊。“如今村里人是越来越好过了。到面粉厂和超市买白面的人多了,小磨坊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老郑说。
两鬓有些花白的老郑,精神很好,说话幽默诙谐,用村子人的话说,“他是个不安分的人”。
对于上世纪70年代末春节的理解,老郑认为是“能吃上白面馍馍,过年时再也不用赶着驴子围着磨道转了”。
老郑回忆说,在自己小的时候,磨面是件大事,一般要全家出动。每逢春节,父亲扛着一布袋麦子和玉米,母亲拿着磨面需要的家什跟在后面,到村南一家石磨坊去磨。四五十斤的麦子或玉米,要十遍才能磨完。老郑仍清楚地记得1 977年过年时家里困难的情景。年夜饭依旧是窝窝头、玉米面粥,仅有的一点白面要蒸成白馍留下来招待过节期间来走动的亲戚。“过年吃上白面馍馍算是好的了。”老郑说。对生活充满期待也善于发掘生活乐趣的农村主妇们,往往还会在馒头皮儿的正中间点上个鲜艳的红点儿,这化了妆的馒头一上桌,年味就来了,来年的“年”也更有盼头了。
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在衣村“吹”出了许多致富能人。往日的“大寨工,慢慢弄”,“大锅饭,慢慢干”没有了,村民们种粮的积极性高涨了,秋天收获的麦子和玉米,在场院里晒干了,该卖的卖掉。老郑是个会过日子的人,“过年的时候,照例两种面都得磨一些。过日子么,也不能顿顿吃白面吧!”
看着周围乡亲们的日子一天天变化、一天天红火,心眼活泛的老郑思想也起了变化。经过一番考虑,老郑用东拼西凑借来的一千多块钱添置了第一台面粉机,就这样开始了他白手起家的“创业”史。小磨坊就开在家里,坐北朝南三间草房,东面两司是小磨坊,西面一司是过屋,供前来磨面的人进进出出。
由于电磨磨出的面又白又好,老郑做活又细致,小磨坊很快在村里红火起来。每逢春节将近的时候,村里甚至临村的乡亲们都来老郑的小磨坊磨面。机器的轰鸣声和乡亲们边等磨面边聊着家长里短、年货置备的谈笑嬉骂声夹杂在一起,小磨坊里分外热闹,电磨的飞转中就转出了新年里的喜庆和老郑一家的喜笑颜开。
开办小磨坊后的春节对老郑而言,更多地就是跟机器一样白天黑夜轮轴转。外屋里总有那么多人在等着他磨面, “没有闲的时候,连饭也吃不得消停。”那时候的他,常常叼着别人递过来的烟卷,时而得意地抽上两口,也顾不得眉毛胡子都沾上的雪白的面屑。忙归忙,但心里的那个甜味可是啥都比不了。
90年代的春节,基本上没人磨玉米面做窝窝头了,1995年的时候,老郑又花了3000多块钱添置了一台二手的全自动碾米磨面机,再也不用“白天黑夜轮轴转”了。磨一斤面七分钱,碾米涨到角钱,年景好的时候,老郑靠着这一项一年就能挣到一万多。家底殷实起来了的老郑搬出了土坯房,盖起了崭新的砖瓦楼房,还添置了农用车。
小磨坊转了1 0多年,到了2000年,生意开始逐年下降了,即使在春节也是门庭冷落,就这样部分机器和房屋也闲置了。很多时候,村里人在春节前打个电话或发个短信,就能提前预订上老郑的小磨坊,再也没有人为磨个面亲自登门了,这让老郑心理或多或少有些落差。
意识到了危机的老郑,2005年又在村子里开了一家邮政连锁配送店,直接销售化肥和副食品,一年下来也有不少的进项。令老郑意外的是,前些年走下坡路的小磨坊,这几年倒是有不少村民专程来这给亲戚朋友弄点杂粮面, 到春节,磨玉米面的特别多,后来甚至一些城里人开车过来买玉米面。
“现如今,城里人过年好吃这个粗粮,管这叫,忆苦思甜!不少农村人也赶这个时髦!”老郑说,白面如今很少有人磨了,超市里随时都能买到成袋的面粉,春节里倒是玉米面这样的粗粮格外紧俏。“现在农村里过年的吃喝也越来越讲究了,锅里肉少了,绿菜和杂粮多了。”
翻开老郑的年终账簿,内容与以前相比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种粮农民补贴、良种补贴、建沼气补贴等新类别不断涌现,家庭的收入也日益多元化:孩子外出打工和在村办工厂做工成了两项最大的收入。小磨坊收入所占比重越来越少,配送店的收入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支出方面,不单单是购买生活用品,还有汽油费、电话费、手机费、合作医疗参保费等,而农业税、特产税、“三提五统”等则先后从账本上消失。
一年一事一连串
在如今的南田村,村民们用顺口溜传唱着国家多项惠农政策带给他们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日历翻开又一年,新年喜事一连串,种地不缴农业税,孩子上学不拿钱,水泥路修家门口,自来水通锅灶前,出门跟着轮子转,电话装在兜里边。合作医疗更喜人,今后看病不再难……”
2006年的除夕之夜,老郑的妻子郑大婶通过网络视频,接受远在广东东莞打工的大儿子和儿媳的拜年。
这位普通的中国农民,通过现代化的网络,和近2000公里外的儿子儿媳在传统新年里见面团聚。
和其他急着回家过年的衣民工不同,老郑的大儿子郑红章和儿媳妇春节时继续在东莞一家工厂干活。郑红章已经是连续两年不回家过年了。他说,每逢年前,不少同乡思乡心切,陆续买火车票回家了,这样一来,到了春节前,不但空出来很多工作机会,工资也相应涨了,干一天比平常多挣三四十元。
“他的娃儿要考大学了,想趁城里人过年的时候多挣点钱,给娃准备学费。”郑大婶对于儿子儿媳在外过年表现出格外的理解和宽容。以前,像郑大婶这样的农村家庭主妇在过年时可是最忙碌的人。
20年多前,村民置办年货至少得一个月,许多年货在外面买不到,只能在家里自己做。如今,那种“养鸡为换盐,养猪为过年,供个学生上学或害场大病就能把家变穷”的时代在南田村已找不到踪迹。去年置办年货,在家门口的便民超市,郑大婶只花了一天时间。“现在过年越来越便利,过年就是让咱也能像城里人一样好好享受一下。”郑大婶说,“以前是10元一张的票子,攥在手里,即便过年也不舍得换开,现在100元的票子一到节,就像泼到地上的水,一会就没了。”
在南田村的一家便民超市,店主的儿子告诉记者,这几年进入腊月就再没闲的时候了,每天从早8点忙到晚8点,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年前人们大都是购买鸡、鱼、肉、蛋、糖果、水果等年货,年后则是购买走亲戚的礼品,店里每天的毛收入就在2万元以上,家里能来帮忙的都来了,还是忙不过来。他还告诉记者,像他家这样的超市南田一个村就有3家。
肩膀上的担子减轻了,村里人的钱包鼓了起来,现代化的过年方式村民们也是样样都会。打个电话问声好,发条短信拜个年,“磕头”礼早已经被这些现代化的方式所代替。
“年轻人的思想在变,老人们的观念也在变。”村民们都说,过去过年不给长辈磕头被看成是大逆不道的事,现在老人们通过电视、报纸也了解了外面的世界,思想也开通了,对于电话、短信或者网络之类现代化的拜年方式渐渐也接受了。
作为惠民工程重头戏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程,也是村民们年越来越好过的重要原因。原来的村卫生所升级改造成新农合定点医疗卫生室,自2006年4月实行新农合制度以来,南田村参合率达到85%。
提起合作医疗,老郑隔壁的赵大婶插话时显得异常激动,原来,2006年年前她得了一场病,花了5000多元钱,因参加了合作医疗救助,全家一年每人交10元钱,她就能报销掉3000多块。这让赵大婶切身感受到了国家的好政策。“吃药看病能报销,做梦都没想到的好事,如今轮到俺们身上,让人不乐都不行!”
“现在我们种地不但不交公粮,还有补贴,国家又给咱衣村孩子‘两免一补’,孙子上学也不再作难了。衣村现如今是一年比一年有盼头了!”老郑说,老百姓就相信实实在在的变化,国家政策好,农民喜事就多,过年才安心。 “搁以前,过年时 小黑白电视,挤了屋子的人,如果哪家过年办喜事放个电影,四里八乡的人都要赶过来。现在谁家没有彩电和影碟机啊!”
指着门口宽阔的水泥马路,老郑又说,过去这是土路,一到下雨也成了“水泥路”,拜个年或串个门难走得很。三贵线公路开通后,如今公交车就从村子旁经过,再也不用为春节时“晴天一身土,雨天身泥”的出行难发愁了。
随着交通条件的日益改善,南田村和很多农都引进了工业项目,这些项目在促进村集体收入的增加的同时,也带动了村民的增收和村子的现代化。
和老大不一样的是,老郑的二儿子郑红军就一直没出远门,农忙时在地里忙活,其他时间靠着培训学到的技术在村里一家冶金工厂上班。除去地里的收成,仅工厂的工资也能每年收入个1万元,小日子过得舒舒坦坦。3年前的春节前夕,郑红军就一口气买回了一辆摩托车、一台34英寸彩电、一个DVD机和两个音箱。在这片曾经是贫困地区之一的土地上,农民正月里骑着摩托车串门、节日里在自家唱卡拉OK已经是很平常的事儿了。“就连过年的鞭炮也不一样了,哪家都是几万响的,一到年关,耳朵都快震聋了!”老郑说。
在如今的南田村,村民们用顺口溜传唱着国家多项惠农政策带给他们的买实在在的好处:“日历翻开又一年,新年喜事一连串,种地不缴农业税,孩子上学不拿钱,水泥路修家门口,自来水通锅灶前,出门跟着轮子转,电话装在兜里边,合作医疗更喜人,今后看病不再难……”
“南水北调”带来新愿景
站在南水北调新修的干渠上,老郑说,“早就听说了‘南水北调’工程要从村子过,这对村子是件大好事。俺只希望流过来的长江水,能多分给俺村子一些”。
像老郑一样,南田村2000多名农民对邓小平讲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句话感觉尤为深刻。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新经济体制的实行和政策的不断开放,使得理解“致富光荣”的南田村成为当地的富裕村。科技和资讯在农村的普及,村民生活节奏也不断加快。没有时间再去仔细梳理和琢磨那过年的红火与热闹,年味在除夕夜的辞岁声后便也逐渐淡了。
然而,富起来的村民对于提升生活质量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渴望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老郑说,平时吃的穿的用的和过年没啥不一样,现在过年聚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关注更多的是自己和后代的生存环境,如何能在村子里过上更好的生活。
这种渴望在2006年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阳段的启动中达到了极致。在南田,像老郑这样的农民清楚地知道:水对于他们来讲意味着更多发展权。他们把这个工程看成是他们未来更加全面小康生活的台阶,寄托着他们在新的一年的期望。
从地图上不难发现:作为我国目前最大的一项跨流域调水工程,南水北调工程施工线路和京广铁路的走向比较吻合。安阳段也不例外,总干渠位居京广铁路的西侧,全长65公里,总投资约35亿元。南田村恰好是南水北调安阳段期工程的最南端。
“南水北调要是全部建成,我们也就成北方的‘小水乡’了,也得想法子实现更科学地发展了。”一些南田村民这样表达自己对于未来生活的希望。
般人也许很难理解对于这里的农村的实际意义。
在离南田村不到30公里的牛屯镇前马头固村,大部分耕地都是盐碱地,地下水比海水还咸,多少年来,全村1500余名村民无奈地饮用着难以下咽的成水,直到2002年,村里建成了150多米深的眼机井,埋设地下管道1 500米后,家家户户才安上了自来水,吃上了甜水。
即便在离南田村不远的东街村,由于地处安阳县西部丘陵山区,全村1 500多亩耕地全部为“望天收”田。为改变这一状况,村民们不得不集资1 55万元修建了长达2500米的引水渠。该村农民陈向奎说:“有了灌渠,我们村所有的山坡田全都变成了水浇地,全村仅小麦一年就可增产15万公斤。”
解决饮水和灌溉困难、改善农村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曾是摆在这些普通中国农村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太行山脚下是个出典型的地方:杨贵、郑永和、吴金印……而这些典型无一例外的都是为老百姓修渠引水、改造良田的。离南田村不到50公里的地方,便是被林州人称为“生命渠”的红旗渠,在安阳县北部,还有一条主要的灌溉渠道名叫“幸福渠”,修渠灌溉对于当地农民的意义,由这两个名字便可见一斑。
如今,饮水困难在改革开放近30年的快速发展进程中早已不是难题。只是离“彻底改变干旱缺水的面貌,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的目标,一些农村还有不少差距。
在老郑种的6亩小麦地里,由于缺水,多年来一直不敢种植蔬菜,尽管现在种菜是种粮收入的多。南田村也很缺水,打井需要打上七八十米才有水,南水北调工程开工,将来能引水的话,对村里种地的农民而言无疑是一个福音。不仅如此,在受水区范围内,南水北调水占受水区城市供水的一半以上,水资源条件也将发生质的变化。
在南田村新规划的小区不远处,南水北调修渠工程日益推进。站在南水北调新修的干渠上,老郑说, “早就听说了‘南水北调’工程要从村子过,这对村子是件大好事。俺只希望流过来的长江水,能多分给俺村子一些。”说着他又深吸了几口烟,双眼在缕缕香烟中眯成了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