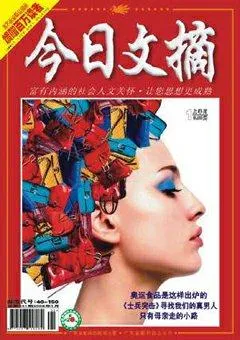有多少草可以在城里扎根
草是城市的匆匆过客,只有一小部分被城市留下来,大部分被拒之城外。
草坪是草在城里可以名正言顺扎根的地方。能够生长在草坪里的草都是草中的贵族,渴了有水喝,饿了有饭吃,头发长了有人梳理,身上脏了有人打理。但贵族也有贵族的规矩,自然不能像长在乡村的草那样争喷竞涌放任自如,它们经常会被这条条那框框束缚着,不能越雷池,也不敢越雷池。
旁逸斜出、鹤立鸡群是不可能的事。它们必须按照城里人的意愿去生存,一个个整整齐齐地站成一片,像一大群被封了口的小学生。值得称道的是,得地利享人和的它们姿态优雅,色彩华丽,铺排出一面遮天盖地的绿绸,说不出有多么诗情画意。
狗改不了吃屎,牛改不了吃草。在乡村与草厮混了十几年的我,每望见这样一片碧绿的草坪,虽不能像一头牛一样猛扑过去,大块朵颐,但我可以在绿草中徜徉一阵,也是一种满足。你经常会看到一个人背着双手围着草坪转圈,像一个老农心满意足地看护自己的粮囤,那个人往往就是我。
草在乡下用途广泛。一是喂牲口。我小时候干得最好也是最多的活儿就是割草,喂牛喂猪,沟旁渠畔蔓延的野草丰收着我的另一块庄稼地。二是作柴草。秋末,把它们连根拔起,塞进灶堂,就是一把好火。三是代替粮食救急。青黄不接或灾荒之年,茂茂密密长得兴旺的野草就是救命粮。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有谁没吃过野草呢?
而草在城里主要是为了养育城里人的闲情逸致,因此更多的草被驱逐在城市外,它们的叶子不好看,也开不出好看的花朵,对城市来说就不是点缀,而成了丑化和负担。
马马菜、乞乞牙、灰灰菜们偶尔也会进入城里人的菜篮子,那是城里人吃腻了鱼肉,想换换口味。热潮一过,很快无人问津。
但再恶劣的环境也不能阻挡一株草的生长。
高高的墙根,不被人注意的角落,必生长着一丛丛野草,只要能得到一点儿湿润和泥土,就在这里安家落户。叶嫩嫩的,茎细细的。在低谷中求生存的它们,更有一种攀登峭壁的勇气。夏天到了,它们羞羞涩涩地绽放出一朵朵茸茸的小花,悄悄扮亮了一方天空。
城市的人行道喜欢铺着彩色的地砖,夏天的雨后,常会从缝隙间伸出一两株细细的草来,处在地砖夹缝中的它们,一方面要摆脱砖的压迫,一方面要承受高温的炙烤。恶劣的环境使得这些草一律是细细的茎软软的身躯,因为长得太瘦弱,我常常不能准确地叫出它们的名字,也许是灰灰菜,也许是狗尾巴草,只是没等它们长粗自己,表现自己,就消失了,不是死于干旱、高温、冰雹,而是毁于人手:或是被行人踩碎茎叶,或是被城市的养护者一把除去。
它们明知自己的结局不过如此,但第二年这时候,还会不屈不挠地顶开砖块,伸出腰杆,一株,两株……长一回,黄一回,再长一回,再黄一回。没有乡下那种漫坡漫野的恢弘气势,没有那种生命的放纵与狂野,只是默默地、不声不响地独自长成一簇自己的风景———被不被人关注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自己在生长,即使死去也绝不是孬种。望着它们的身影,一瞬间我竟莫名地感动起来,觉得它们真伟大。
我在城市的街头会碰到许多像草一样在城里谋生的农民,他们拘谨着,劳作着,“一镐一锨”地,承受着千辛万苦,试图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夹角中求得一席之地。只是最后又有多少能扎根城市?
我们的城市现在愈来愈干净漂亮,而草也就越发地没有了立足之地。
草一辈子扎根一个地方,无怨无悔,不言不语。假若城市没有了草,也许不会有什么缺憾,我却觉得,少了一道能刺激我们灵魂的风景。■
(曹庚荐自《都市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