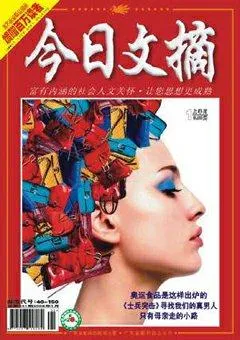揭开我国试跳员神秘面纱
在南京宏光空降装备厂,有一支由10多人组成的降落伞试跳员队伍,这也是全国仅有的一批试跳员。降落伞试跳员,不同于跳伞员,他们要跳最新研制出的降落伞,危险性可想而知。近日记者走近他们,了解他们试伞经历中鲜为人知的故事。
生命系在“保命伞”上
降落伞试跳所在的单位是各类空降空投产品科研、交货试验的职能部门,试跳员是降落伞“空试工”,他们要试跳各型科研样伞及即将交付的抽检产品。由于降落伞试跳是空中作业,尤其是新品,可能出现的危险难以预测,除了极个别的产品,试跳员们每次试跳都会背上主伞和遭遇紧急情况时用的备份伞,备份伞被称为保命伞——试跳员在空中遭遇特殊情况,主伞不能打开,就采取紧急措施,抛掉主伞,打开备份伞,确保平安着陆。
宏光厂现在的试跳员大致分为3个梯队,朱宁、秦凡等试跳员,是50岁的老队员,由八一跳伞队培训;肖龙、赵安飞、李军、时斌、李华勇、谭军来自空降兵部队,他们30多岁,属于第二梯队;2002年时,厂里直接培训了魏红宝、马晓亮、金玉祥这三个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
朱宁:极限低空跳过低于100米
现任试跳站站长的朱宁从1974年开始,从事降落伞试跳已三十余年。他告诉记者,就跳伞而言,留空时间越长,跳伞人员处理各种情况的时间越充分,因而也越安全。但作为一种军事装备,需要适应各种环境,能够满足各种特殊需要。像近年宏光厂的新型伞兵伞,适用的高度不到100米,至今保持着世界跳伞最低高度的纪录。跳这种伞时,试跳员从离机到着陆不到10秒,几乎已达到人类反应的极限,对试跳员的心理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样品研制出来后,虽然有众多专家“保驾”,但面对高度的危险性,大家对谁来承担这“第一跳”都很为难,这时朱宁主动请缨进行第一跳。
那一天,该型产品的真人试跳在美丽的太湖边开展,很多空军首长、企业领导及试验保障人员站在预定着陆场,心情忐忑地等待着。飞机轰鸣,迅速下降到指定高度,舱门打开,朱宁稳定了一下心神,纵身跃出机舱,娴熟地运用各种技能,美丽的伞花顺利张开,大家张开的嘴还来不及欢呼,不到10秒,朱宁已稳稳在预定的地域着陆,中国空降史上的又一项纪录诞生了。
李军:迷失地标背伞走了5公里
李军是试跳站的副站长,大高个子,他1994年从空降兵特招到该厂,已试伞13年。有次他在汤山试跳,结果飞偏了航线,在空中时就觉得不对劲,地标都找不到了,最后他落到了一个水塘边,差点就落入水里,艰难地背着伞走了半小时才回到目的地,算下来大约偏了5公里。“试跳中有种听天由命的感觉。”李军说。
还有一次冬天在河南,他跳下飞机后发现风很大,最后落到了机场铁丝网外的一块坟地中,伞被卡在了墓碑上,加上风大,伞鼓得像个大风帆,自己一点也没法动弹,好在一个老乡经过,帮他解了困。后来他往回走,发现其他几名队员有的被生生卡在铁丝网上,伞在铁丝网另一侧,只能靠别人解救。他还说,在跳科研伞时,曾经两次没打开伞,只能打开备份伞来保命。
魏红宝:征服恐惧一连跳了50次
魏红宝是南京高淳人,1981年出生,今年27岁,2000年从南京宏光技校毕业,直接转到宏光空降装备厂工作。他属于那种一点跳伞经验都没有的队员,在经过半年的地面训练,以及模拟空中姿态后,才开始进入试跳程序。“2001年4月份在山东进行了第一跳,但我第一次倒不怕,第二次竟开始怕了。”他告诉记者,因为跟第一次相比,第二次换了伞型,也换了机型,这是他最紧张的一次,第一次的经历告诉了他伞在空中运行的过程,某个阶段可能发生危险,也就是说他忽然明白了这项工作是有危险的。“毕竟是从天上下来。”不过庆幸的是,有次在山西,他一连跳了50次,终于征服了心理紧张这道槛。
采访最后,记者了解到,这10多名试伞员在这成千上万次的试跳中,虽然遭遇过的危险挺多,但最终都化险为夷,至今未发生过严重事故。 ■
(季小军荐自《扬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