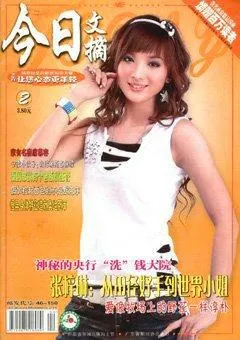维克多先生的小糖果店
李军/译
我四岁的时候,就已经是维克多先生开的糖果商店的老主顾了。无论什么时间,只要店门上的小铃一有声音,维克多先生就会在糖果柜台后面出现,微笑地望着你。他真算得上老了,头上全是好看的白头发。
当各种各样又好看又馋人的东西一下子都摆在一个小孩的眼前,从里面选出一样真是件难事。每当最后选定一种糖果时,心里总有点不痛快,总觉得也许还有另一种糖的味道更好。维克多先生把小孩子选好的糖果装进纸袋里,然后习惯性地停一会儿,什么话也不说,但所有小孩都知道,他的眉毛稍稍一抬,意思是说你还有最后一次选择的机会。只有当钱放到了柜台上,他才会给你绑好纸袋,你也就不能再犹豫不决了。
我们家离电车站有两条街,上下车都会经过维克多先生的小糖果店。有一次,妈妈带我到城区办事。当我们路经电车站回家时,妈妈说:“看看我们能否找到些好东西。”她一边说,一边牵着我来到维克多先生那很长的玻璃柜台前。这个老人从屋里出来,和妈妈交谈了几分钟,我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柜台里的那些糖果样品,临走前妈妈拿钱为我买了一些糖果。
那时我对钱一点也不知道,只是见到妈妈递去一样东西,又接过像包裹之类的东西,慢慢地,交换的概念进入到我头脑中。有一次我竟然穿过两条街,一个人来到维克多先生的小店。我还记得费了些周折才按响了门铃。门开后,我像中了魔一样,缓缓地走到柜台前。
这里是薄荷糖——非常凉爽;那里是果胶糖——吃进嘴里,很甜;紧接着的一个盘里是奶油巧克力……
我每样都挑了一点儿,放在一起,心里甜丝丝的,维克多先生微微弯着腰问:“小伙子,你有这么多钱吗?”
“哦,当然。”我答道,“我有许多钱。”我伸出手,松开手指,把用银锡纸包着的很多粒松籽倒在他手中。他站在那儿看着手心里的东西,然后用敏锐的眼神看了我好久。“这些够吗?”我急忙问。
他微微歪了一下头,耸耸肩说:“我想多了一点。”说完,他转过身去,从那旧式的钱箱里取出两便士搁在我手中:“喏,这是找给你的零钱!”
每当得到妈妈的同意,我总会拿到一两分钱去那家小店换回糖果。从那以后,我也不再注意松籽那回事了。随着一天一天地长大,也就慢慢忘记这件事了。
六七岁的时候,我家搬到另外一个城市。我在那儿长大,结婚,组成了自己的家。妻子和我喂养着各种漂亮的观赏鱼,还开了个店,情况还不错。
一个晴朗的下午,进来一个小女孩,身后跟着她的弟弟,他们有五六岁,我正忙着洗鱼池。他俩睁着又大又圆的眼睛盯着水中来回游动的鱼儿。弟弟用挺大的声音说:“我们能买一些吗?”
“当然,”我说,“只要你付得起钱。”
“噢,我们有很多钱。”小姑娘自信地说。这话听起来竟是那般似曾耳闻。他们看了好一会儿。要了些不同的品种,我把它们装进一个罐子里,又用塑料袋装起来,递给男孩,我叮嘱道:“小心拿着。”
他点点头,转头看姐姐,说:“你给钱吧。”我伸过手去拿钱,但当她松开小手指时,我突然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甚至知道小姑娘将要说些什么。
她递给我三个小硬币。
这个时候,维克多先生那熟悉的面孔好像就在眼前,面前这个小姑娘多像童年的我啊!只有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