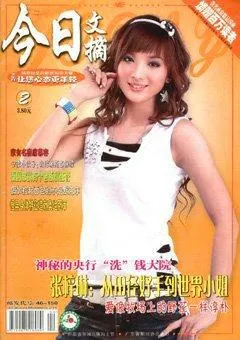怎样评价这个时代的文艺批评
“元理论”的终结与元评论的开始,是我们这个时代文艺批评的基本背景。总体性和普遍性理论的失效,使批评失去了统一的尺度和标准。这是我们批评的困境。但这还不是文艺批评真正的问题。文艺批评真正的要害或问题,在当下主要是没有是非观、价值观和立场。统一标准或尺度的消失,并不意味是非观、价值观和立场也可以不要。让批评发出真正有力的声音,让批评有是非观、价值观和立场,是纠正当下批评被诟病的最好手段,也是维护批评最高正义的惟一途径。
2004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德国作家瓦尔泽的长篇小说《批评家之死》。这部小说2002年在德国出版时,他刚刚过完七十五岁生日。这本书是他献给自己七十五岁生日的礼物,同时他也将因此书引发的巨大争论一起献给了自己。我们抛却这部小说遭到诟病的种族问题的“政治不正确”不谈,单就对那不可一世、呼风唤雨的“文学评论沙皇”的抨击和讽刺,就足以想见文学评论家在当下社会中的面目是多么可憎和可怕:他在最典型的大众传媒——电视上,颐指气使地抨击一部作品,又趾高气扬地鼓吹另一部作品。那是在德国。在中国,批评家的面目可能还要糟糕得多。
这也许是一个不经意的隐喻。事实上,上世纪60年代自美国后现代作家约翰·巴斯发表了《枯竭的文学》之后,各种“终结论”、“死亡论”的声音就不断传来。“抵制理论”、“理论之死”、“作者之死”、“历史之死”,当然也有“批评之死”,前呼后拥此起彼伏。但是,这些终结论或死亡论,并不是言说文学、理论或批评真的“终结”、“死亡”或“枯竭”了。他们都有具体针对的对象。比如巴斯,他的“文学的枯竭”,是挑战现实主义文学、挑战传统文学观念的。因为此时他正站在文学新方向的最前沿。在巴斯看来小说应当是“原创的”、“个人的”,也就是一种他所说的“元小说”。现实主义文学,作为一种“总体化的小说”,从19世纪早期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它构成了小说史上一个短暂的“实验”阶段,尽管也成就了无数大师。在巴斯看来,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实主义那种曾有的反传统的思想已经耗尽。新的“元小说”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再度流行。这才是巴斯宣VfdkD6LyLSvuMYr/wdfZJAGdpKR39q5GRxJNREdm5Ig=布“写实主义实验(现实主义)”已经“枯竭”的真实用意。按照这样的思路,批评家尼尔·路西连续发表了《理论之死》、《批评之死》和《历史之死》等惊世骇俗的文章。在路西看来,文学不可能是一种“稳定”的结构,它有许多特殊范例,但总体性的“稳定”结构是难以包括或不能解释这些特殊性的①。“批评之死”显然是针对这种文学总体性稳定的批评而言的。但是,路西同时认为,文学结构是不稳定的,并不意味着批评就一定会死亡——或者枯竭——它再也不可能像从前那样行动。在这个意义上,批评将会得到更密切的关注。
事实的确如此。当传统的“元理论”被普遍质疑之后,批评家的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我们都会承认,保罗·德曼、德里达、詹姆逊、哈罗德·布鲁姆等大师与其说是理论家,毋宁说是批评家更为确切。之所以说他们是批评家就在于,他们的思想活动并不是在寻找一种“元理论”,而恰恰是在批评自柏拉图以来建构的知识或逻辑的“树状结构”。在“树状结构”的视野里,知识或逻辑是一元的、因果的、线性的、有等级或中心的。但是,在现代主义之后,传统的“元理论”不再被信任,特别是到了德勒兹、瓜塔里时代,他们提出了知识或逻辑的“块茎结构”。在“千座高原”上,一种“游牧”式的思想四处奔放,那种开放的、散漫的、没有中心或等级的思想和批评活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这就是西方当下“元理论”终结之后的思想界的现状。美国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姆逊将这种状况称为“元评论”。他在《元评论》一文中宣告,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连贯、确定和普遍有效的文学理论”或批评已经衰落,取而代之,文学“评论”本身现在应该成为“元评论”——“不是一种正面的、直接的解决或决定,而是对问题本身存在的真正条件的一种评论”。作为“元评论”,批评理论不是要承担直接的解释任务,而是致力于问题本身所据以存在的种种条件或需要的阐发。这样,批评理论就成为通常意义上的理论的理论,或批评的批评,也就是“元评论”:“每一种评论必须同时也是一种评论之评论”。“元评论”意味着返回到批评的“历史环境”上去:“因此真正的解释使注意力回到历史本身,既回到作品的历史环境,也回到评论家的历史环境。”②
在当下中国,文学批评的状况与西方强势文化国家有极大的相似性。批评的“元理论”同样已经瓦解。就像普遍了解的那样,在我国,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基础理论学科,并没有像韦勒克表达的文学研究是由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一起构成的。在韦勒克看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同属于“文学研究”范畴,它们应该是平行的。但是,过去我们所经历的情况通常是,文学理论对于文学批评来说,是具有指导意义和规范作用的。它恰恰是文学批评的“元理论”,因此它不仅仅是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对于文学批评,它构成了权力或等级关系,它是一个超级的“二级学科”,而文学批评不是。进入90年代,随着现代启蒙话语的消退,受到西方批评话语训练的“学院批评”开始崛起。这个新的批评群体出现之后,中国文学理论的“元话语”也开始遭到质疑。这当然不应仅仅看作是西方批评话语的东方之旅,但中国文学理论遭到质疑的历史或社会背景,却与西方大体相似。以现代知识作为背景的中国文学理论,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所起到的伟大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它对于推动欠发达的现代中国文学的建立,也功不可没。即便是在80年代初期,在抵制、反抗“文革”时期文艺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文学理论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也同样无可取代。在过去的时代,文艺理论的特殊地位几乎不能怀疑。所有的关于文学艺术的讨论,最后都要归结于“文学理论”。“文学理论”已经为我们规约了一切,它的“元理论”性质是不能动摇的。40年代初期以来形成的关于文学艺术的思想、方针、路线和政策,至今仍然是我们理解社会主义文艺最重要的依据。无可怀疑,在拯救中华民族危亡、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以及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那个时代文艺理论话语所起到的历史作用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在那样的时代,实现民族的全面动员,使文学艺术服从于国家民族最高利益,使文艺成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发挥齿轮和螺丝钉的作用,是完全可以理解和正确的。
但这也成为文学理论作为“元理论”不可动摇的强大的历史依据。一部作品是否具有合法性,是否能够成为这一理论的有效证明,是判定它是否具有价值的先决条件。但是,在飞速发展的当代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剧烈或激化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当代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文化试验场:各种文化现象、思想潮流,共生于一个巨大而又拥挤的空间。过去我们所理解的“元理论”对当今文艺现象阐释的有效性,正在消失。一种以各种批评理论进行的新的批评实践早已全面展开。正如普遍认同的那样,对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的关注,并不是“西方中心论”或简单的“拿来主义”,事实上,它已经成为建设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主要参照或资源之一。于是,在当代中国,理论批评也同样形成了德勒兹意义上的“千座高原”,“游牧”式的批评正弥漫四方。
在这个意义上,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文艺批评,应该说取得了巨大的历史进步。“元理论”的终结和多样性批评声音的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历史包容性和思想宽容度。但是,一方面是文艺批评巨大的历史进步,一方面是对文艺批评的强烈不满。许多年以来,对文艺批评怨恨、指责的声音不绝于耳。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个“憎恨学派”在憎恨什么,指责批评的人在指责什么。那些浅表的所谓“批评的媒体化”、“市场化”、“吹捧化”等等,还没有对文艺批评构成真正的批评。因为那只是、或从来都是批评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或者我们从相反的方向论证:假如“媒体批评”、“市场化批评”等不存在的话,批评的所有问题是否就可以解决?我曾经表达过,对一个时代文学或批评成就的评价,应该着眼于它的高端成就,而不应该无限片面地夸大它的某个不重要的方面。就如同英国有了莎士比亚、印度有了泰戈尔、美国有了惠特曼、俄国有了托尔斯泰一样,中国现代文学有了鲁迅,中国现代文学就是伟大的文学。现代中国批评界也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但因为有了鲁迅、瞿秋白等,中国现代的文艺批评就是伟大的批评。当下中国的文艺批评还没有出现这样伟大的文艺批评家,但那不是憎恨或指责的理由。在一个转型的时代,一切可能都在孕育、生长。
甚至可以这样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不仅在学院体制内补上了因长期封闭而不了解的西方文艺理论批评课程,培养了数目巨大的专业理论批评人才,而且那些一直在场的文艺理论批评家,在建构中国文艺理论批评新格局、推动理论批评建设、参与、推动文艺创作、阐释或批判文化现象等方面,始终不遗余力。对各种新出现的文学、艺术现象的阐释、解读,比如对现代派文艺、对先锋文学、对新写实小说、对市场文艺、对网络文化、时尚文化、底层写作以及各种文化、文艺现象,批判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批评的不满,应该具体地分析。更多的人习惯于80年代对“元理论”没有质疑的思想方式,一切都有答案,而且是清晰的非此即彼的答案。那时不是“千座高原”,只有一座山峰,对山峰只须仰望而不必思想。文艺批评就在这个“元理论”框架之内。今天的情况已大不相同,一切都没有不变的答案。对这种纷纭甚至纷乱的声音的不适应在所难免。“元理论”或普遍性的丧失,使文艺批评失去了统一的标准或尺度,它再也不是非此即彼式的二元世界。因此,不满意应该是“元理论”、普遍性或不确定性带来的问题,不应该完全由文艺批评来承担。正像前面提到的,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文化试验场,一切问题都让文艺批评来解决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文艺生产领域,参与、影响或左右文艺的因素越来越多,而这些因素是文艺批评家所难以掌控和改变的。
比如市场因素。在引导当下文艺生产的诸种因素中,市场的力量是难以匹敌的。仅就长篇小说创作来说,每年有1200部左右的作品出版。这个巨大的数字里,究竟有多少作品可以在文学艺术的范畴内讨论,确实是一个问题。文学生产的数字庞大,但在艺术上我们却是在“负债经营”,“艺术透支”是市场带来的最大问题之一。且不说商家在绞尽脑汁地策划出版能够占有市场份额的作品(在出版社自负盈亏的机制中,它有合理性的一面),单就生产环节而言,只要有市场号召力的作品出现,跟风的现象就无可避免。从《废都》到《狼图腾》到《藏獒》,都有模仿的作品迅速出版。商业目的对原创作品的消费淹没了原创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意义。它被关注的路径被极大地改变。批评家对作品的阐释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流传和讨论,更多的人不知道文艺批评对这些作品究竟表达怎样的意见。
近年来,文化创意产业突飞猛进,它已经成为左右文艺生产的重要因素。张艺谋、陈凯歌等导演的电影,从《十面埋伏》、《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到《无极》,除了“大投入”、“大制作”等毫无实际意义的概念外,几乎乏善可陈。但是,它们确实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价值。一方面我们会批评这些影片或导演在艺术上的失败,一方面在好莱坞电影帝国横行天下的时候,它们又为民族电影的存活带来了一线希望。这时,我们内心爱恨交织,简单的批评或赞赏都不能表达我们的全部复杂心情。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市场的态度也会发生变化,市场的问题不是我们主观想象的那样简单,它客观上的多面性可能还没有被我们所认识。但它对文艺生产的影响、制约是绝对存在的。
还有评奖制度。任何文学奖项都隐含着自己的评价尺度,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评委也说过,在诺贝尔文学奖的上空,有一层挥之不去的政治阴云。诺贝尔文学奖也是有自己的评价标准的。像左拉、托尔斯泰、勃兰兑斯等都没有获奖。有资料说:1901年瑞典文学院首次颁发文学奖,按当时文坛的众望,此奖非托尔斯泰莫属,可是评委会却把第一顶桂冠戴在了法国诗人苏利—普吕多姆头上。舆论大哗,首先抗议的倒不是俄国人,而是来自评委们的故乡——瑞典四十二位声名卓著的文艺界人士联名给托翁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安慰信,说“此奖本应是您的”。但是托翁终身没有得到这一荣誉。
瑞典文学院对于一切评论历来不予回答,不过私下也承认:“以往出现的偏差我们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从不说谁得了奖谁就是世界上最佳作家,不过你得承认,我们是经过了一年的调查研究才慎重选出获奖人的,我们对每个候选人都有广泛的研究。”①确实,尽管偏差难免,但是历年文学奖获得者毕竟都是令人瞩目的文坛巨匠,决非滥竽充数之辈。
我国的评奖制度“文革”前不多,大概只有电影的“百花奖”、“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等少数几个奖项。1978年以后,“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评选”等奖项陆续设立。然后有“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以及民间设立的各种奖项。然而,没有任何一种文学奖项是没有异议或令每一个人都满意的。“茅盾文学奖”当然也有它的尺度和标准。尽管我们会对一些入选或落选的作品有意见或遗憾,但又完全可以理解。谁设立的奖项,就会授予奖项需要和理想的人。文学奖就是对一种文学意识形态的认同或彰显,就是对一种文学方向的倡导,这就是查尔斯·泰勒所说的“承认的政治”。对意识形态的认同,是一个人进入社会的“准入证”,对文学意识形态的认同程度,也决定了一个作家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承认,所以“承认”是一种“政治”。如果道理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有些作品会获奖,而有些作品会落选。可以肯定的是,获奖作品的艺术方法、政治倾向以及思想内容,都会对一个时期的文艺生产产生影响,特别是那些被普遍关注、影响广泛的奖项。
大学教育和文学史编纂。大学教育是传播文学经典最重要的场所,文学史编纂是确立文学经典最重要的形式。尽管大众文化已经进入了大学教育的课堂,改变了单纯的经典文化教育的内容。但是,大学的精英教育或经典文艺教育,仍然是大学文学艺术教育的主流。而文学史、艺术史的编纂,又是确立文艺经典最重要的形式之一。虽然早在60年代欧洲关于文学经典的讨论中,就有人提出为什么大学课堂一定要讲授莎士比亚(即经典文艺),文艺经典是由谁提出并确立的,我国近十年来也陆续讨论过类似的文艺经典的问题,但强大的精英意识和大学文艺教育体制,仍然坚持着文艺经典观。因此大学文艺教学的基本状况仍然以传承的强大力量影响着当下的文学观念和创作。但值得注意的是,当代文艺的经典化是存在问题的。经典化就是历史化。但当代文艺的“当代性”使这个经典化还缺乏足够的距离和时间,近距离判断的失误在所难免。而且,文学艺术史的编纂,既有文艺经典,也有“文艺史经典”。文艺经典是指普遍认同的经典,是经过历史过滤存活下来的经典;“文艺史经典”,是指虽然不是经典艺术,但在文艺发展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品,或者引发过巨大争论的作品。比如新时期的《班主任》、《伤痕》等,它们都构不成文学经典,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它们的重要性必须写进文学史。类似的情况还在发生,比如“底层写作”等。“文学史经典”也会影响到文学创作和生产。
这些因素虽然都不是具体的文艺批评,但是作为影响文艺生产的因素,它们的作用甚至远远超过了文艺批评。这些因素合力造成的后果,都要文艺批评承担,这是不合理的。批评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承担这一切。即便如此,我们在总体肯定文艺批评取得巨大历史进步的同时,也必须谈到文艺批评真正的问题。在我看来,文艺批评真正的要害或问题,在当下主要是没有是非观、价值观和立场。统一标准或尺度的丧失,并不意味是非观、价值观和立场也可以不要。一个极端或绝对的例子,是近期上映的美籍导演李安的《色·戒》。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汉奸电影。这部根据张爱玲小说演绎的电影,对汉奸的美化,对特殊环境中人的情感和内心变化的同情、欣赏,使它完全丧失了历史叙述的基本立场。如果我们认同李安的叙述的话,那么,历史就是可以任意建构的。个人的理由如果等同于大历史叙述,那么,任何与历史相关的立场和价值就都是一文不值的。值得注意的是,面对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或现象,批评界几乎是集体缄默。更多的人注意的是为什么剪掉以及剪掉了多长时间的“床上戏”。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就这样在一个近似“无厘头”的质询中变成了一场闹剧。这时,我想到了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第二年萨特创作的话剧《死无葬身之地》。几个游击队员被捕后,经历了难以想象的酷刑,他们也有过告发队长的念头,一旦告发他们即可获释,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这不仅是萨特的底线,也是面对正义与非正义战争历史叙述的基本立场。所有的游击队员最后都牺牲了,萨特对法西斯的控诉不仅维护了人类基本的价值尺度,同时也完成了战争环境中对人的具体人性的揭示或考量。但《色·戒》不是,它将人在极端化环境中表现出的偶然性或不确定性镶嵌于大历史叙述中的时候,也改写了历史。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对《色·戒》批评的缺席,反映了批评界在立场、价值观和历史观上的问题,它应该是近年来批评界存在问题的集中反映。而当我们检讨文艺批评问题的时候,这可能是切入要害的最恰当的入口。
对与文学艺术相关问题的阐释、解读是必要的,但过度阐释或言不及义的言辞表演,伤害了批评的尊严,使批评成为另外一个好好先生。批评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一个现象,但也不意味着一味地说好话。一味的好话和粗暴的批评是一回事,是一个事物的两种同质表现。因此,让批评发出真正有力的声音,让批评有是非观、价值观和立场,是纠正当下批评的最好手段,也是维护批评最高正义的惟一途径。
这时,我又想到了文章开始时提到的《批评家之死》的德国作家瓦尔泽。他曾将即将出版的新作《批评家之死》按惯例寄给享有盛名的严肃报纸《法兰克福汇报》(FAZ)连载。没想到《法兰克福汇报》的出版人一反常态,在尊贵的首版上发表了一封罕见的公开信,拒绝了连载建议:“您的大作像国家机密一样被我们研读。《批评家之死》是关于仇恨的文本记录:不是着眼于批评家,而是犹太人之死,FAZ不会刊登有明显叫嚣谋杀和种族仇恨的小说。您经常说:摆脱束缚,真正自由。我今天相信:您的自由就是我们的失败……”①在一个众声喧哗、多音齐鸣的德意志,尚且有如此坦白和不可妥协的声音,这就是是非观和价值观。我们不评价这位出版人对《批评家之死》的批判是否正确,但我们赞赏的是,他是一个有是非观、价值观和立场的人。我们的文艺批评就应该达到这样的程度。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陈剑澜
①尼尔·路西:《批评之死》,阎嘉主编《文学理论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1页。
②詹姆逊:《元评论》,《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一起献给了自己。
①缪培松:《诺贝尔文学奖纵横谈》,载《读者文摘》1985年11期。
①参见http://lib.verycd.com/2006/01/21/0000086021. 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