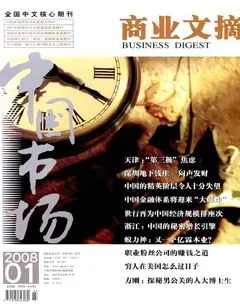《纽约时报》评出2007年十大好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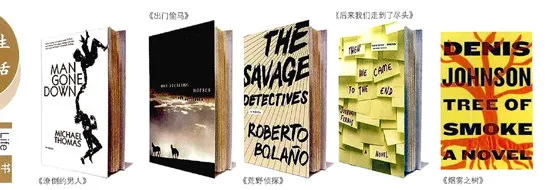
《潦倒的男人》
作者:迈克尔·托马斯
“这部处女作描述了一位黑人作家4天绝望的生活背后破碎的童年。”作者用了400多页以第一人称讲述一位35岁的黑人4天内的经历及其成因:他是一个早熟的孩子,由于一项“社会实验”,得以进入波士顿的白人学校上学。有诗歌和音乐天分的他本可以避免父母酗酒的麻烦,但他后来也养成了酗酒的习惯,没有拿到学位,种族歧视阻碍了他实现自己的梦想。住在布鲁克林的他处于崩溃的边缘,要一边写作一边养活他的白人妻子和三个孩子。他破产了,寄居在朋友家里,必须在这4天内挣到1.2万美元,用于租房和支付孩子的学费并把孩子们从老家接过来。讲述者思考了他的婚姻、工作和种族关系。除了偶尔过于自怜之外,叙述中还难得地显示着乐观。
《出门偷马》
作者:佩尔·彼得森
“在这部不长但充盈的挪威小说中,奥斯陆一位老人希望通过陷入孤独来消除寂寞。”年近70岁的老人特朗德为了过上他渴望已久的宁静沉思的生活,搬到挪威东部一幢偏僻简陋的房子内居住。偶遇一位邻居、童年伙伴乔的弟弟使他回忆起1948年的夏天,他跟他敬爱的父亲一起度过的最后的时光。特朗德的回忆集中于一个下午,他跟乔一起去邻近的农场偷马,那次有趣的冒险以悲剧告终。
《荒野侦探》
作者:罗伯托·波拉诺
一部描写一群文学游击队员的自传式的小说。作者是智利流亡作家,小说出版于1998年,讲述20世纪70年代一群墨西哥年轻诗人的生活。
前100多页是以17岁的墨西哥诗人胡安·加西亚·马德罗的日记的形式叙述的,他在墨西哥城上大学,由于迷恋诗歌,他经常逃学,和一群自称“本能现实主义派”的诗人混在一起。后400页的形式是对利马和贝拉诺的朋友、爱人、熟人和敌人的访谈,透过对这数十名目击者的访谈,勾勒出利马和贝拉诺在美国、奥地利、以色列等地的行踪。诗人们的结局总是很凄惨,利马曾在巴黎住过一段时间,非常穷困,有一次他在路上捡到一张5000法郎的纸币,此后他就总是低着头走路。
《后来我们走到了尽头》
作者:约舒亚·菲利斯
“在菲利斯尖刻、有趣的处女作中,辞退通知满天飞,背景是网络泡沫破灭时芝加哥一家广告公司的办公室。”小说以公司职员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来讲述故事,充分地传达出集体的急躁、唠叨、小气和热心。“我们脾气不好,薪水过高。世界上充斥着互联网资金,我们只是拿到我们应得的一份。我们认为标识设计跟产品性能和分销体系一样重要。酷毙了说的是我们的设计,小儿科说的是别的公司的设计——如果他们真的设计得很好,我们就会向它鞠躬,就像玛雅人向他们的神灵鞠躬一样。”
《烟雾之树》
作者:丹尼斯·约翰逊
丹尼斯·约翰逊是一位真正的美国艺术家,《烟雾之树》是一部精彩的书,读它是很好的消遣,很长但是会很快读完。它具备重要小说的要素:重大历史题材(越战),神秘的文化机构(军事情报),漫长的时间跨度(1963-1970,结尾的背景是1983年),很厚(614页)。”小说围绕的是一个叫斯基普的情报官员,他1967年前往越南参加一个名为“烟雾之树”的行动,可能指的是利用一名越南双重间谍诱使河内方面相信美国正计划攻打“北越”,“烟雾之树”可能指的是蘑菇云。间谍故事只是一个次要情节,烟雾之树也是指虚幻般的战争景观。
《翡翠城里的帝国生活》
作者:拉吉夫·钱德瑞萨克伦
作者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记述美国在伊拉克实行的傲慢的、不适当的管制。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的一年间,联盟临时管理当局负责该国的管理。翡翠城是指位于巴格达原萨达姆官邸周围的美英联盟的总部“绿区”。“翡翠城”内到处鸟语花香、树影婆娑,偌大的游泳池水照着周遭环境,一片和谐的绿区仿佛度假区,与区外的血腥世界形成鲜明对比。
《小野蛮人:大萧条时期在爱荷华一个农场的苦与乐》
作者:卡利什
“卡利什对她的童年的爱恋渗透在这部回忆录中,令读者快乐、惊奇又艳羡。”5岁的时候爸爸不辞而别,她跟祖父母、母亲和兄弟姐妹一家七口同住,祖父母经营着一座农场。大人教他们干活,种土豆、照料牲口、晒干草。他们的生活非常简朴,没有电、没有空闲、没有热水,不会因为年幼而被娇宠,犯错就会挨揍,划伤、割破手后不会跑回家找大人照料。她提供了很多菜谱和偏方,她告诉读者如何剥兔子、煮猪头、炸甲鱼。孩子们赤脚奔跑,养小浣熊,骑还没被驯服的小马,说明美国人的生活曾经是多么简单,周围的人互相都认识,让她得到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
《九人:最高法院的隐秘世界》
作者:杰弗里·图宾
“一位见闻广博的局外人记述了与世隔绝的最高法院的内部运作。”在访问过75名大法官的法律助理以及若干不愿具名的大法官后,图宾发现影响判决的其实不是法律和宪法理论,而是大法官的政治直觉和个性、与其他大法官的私人情谊,以及个人的法理意识形态。他的书中充满着每个人的小故事,以及机锋的话语。
《伊丽莎白·马什的磨难:世界史上的一位女性》
作者:琳达·科利
历史学家科利把马什描写成一个受世界历史事件冲击的女性,大英帝国的崛起改善了她的生活,美国革命又造成她家破产。科利追踪了“被迫不停地奔走”的马什在18世纪遍及几大洲的足迹。她受孕于牙买加,出生于英格兰,在6个城市生活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20岁时候,她被北非海盗绑架,摩洛哥的苏丹想纳她为妾,她谎称自己嫁给了一位同路的英国犯人才得以脱身。被释放后她觉得自己应该报恩,要嫁给她谎称是自己老公的那个人,他欣然同意了。马什的这位丈夫很会经商,她生了一子一女,享受着奢华生活。丈夫破产后去了印度,马什带着子女投奔父母,像其他18世纪遭遇财政困难的女性一样,她写了一本书《女俘虏》,记述自己在摩洛哥的经历。

《其余的只是喧嚣》
作者:亚历克斯·罗斯
《纽约客》的乐评人以20世纪的古典音乐折射20世纪的历史。在20世纪,战争和政治明显地跟音乐纠缠在一起。“由于其难于言喻的本性,音乐很容易被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被用于政治目的。”希特勒演说时的动作跟马勒的指挥风格有些类似。有段时间,古典音乐作品因为受到纳粹的欢迎而被认为失去了其道德高度。一些作曲家因此而努力抛弃古典音乐形式,转而探索其他选择,以至于50年代出现了各种吵闹刺耳的实验音乐。60年代初期,美国希望证明资本主义和高雅文化是相容的,音乐成了“冷战”的工具。军备竞赛扩展成科学竞赛,随后又变成文化竞赛。用于文化事业的数百万美元来自肯尼迪政府,虽然杰奎琳·肯尼迪曾经讥笑说肯尼迪唯一真正喜欢的曲子是《向总统致敬》。
(摘自:中国经济网 编辑:何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