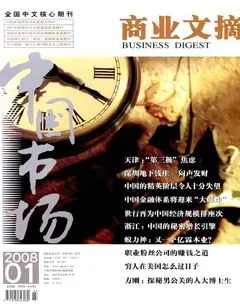“80后投资部落”:富豪第二代的PE投资生活
电脑屏幕上,汪远志(化名)的战队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他的上牙咬着自己的下嘴唇,但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于是“砰”的一声,甩开了电脑键盘的右手重重地敲在桌子上,嘴里还爆了一句粗口。
混迹其中,汪远志和他的朋友们和其他人并没有不同:二十多岁,顶着一张自以为成熟的娃娃脸,仍然爱玩游戏。但他们背后,是至少一两亿的资产,其中有一些省市首富的子女,有的人家里甚至有3家上市公司。
在汪远志这些年轻的财富二代看来,“如何用已有的钱赚到更多的钱”,才是他们区别于其他同龄人、需要认真思考的事情。资本市场的火爆以及VC(Venture Capital,创业投资,以下简称VC)退出的高利润也吸引了这个群体,最近他们开始抱团在上海寻找股权投资项目。
“小项目练手,大项目跟投”
一年前戴寅从湖北武汉来到上海,那时他还不是很了解VC是什么。一年后,他和几个合伙人组建了自己的基金公司同辉创投,并担任执行董事。投入到基金公司的钱,是家里给的。
“这种模式,在这个圈子里很流行。”比如每个人都有1000万人民币,单靠这些钱还不足以设立一只基金。于是就找10个这样的人,1亿元设立一个基金公司,然后把这个公司制的基金委托给自己设置的基金管理公司。“聘请职业经理人来做具体投资。”
戴寅最近特别忙,原因是在看好几个Pre-IPO(临上市前)项目。同辉创投的单比投资额在800万到3000万人民币之间,范围更是跨越了从数字媒体到工业等的12个领域。而颇让人惊讶的是,主导着这些事情的戴寅,今年刚22岁。1986年生人。上海这批80后投资人中,戴寅或许是目前年纪最小的。
“他什么都投。”这个圈子里的人评价说,“如果中东有足够好的项目,他也会投”。
与戴寅的激进不同,大部分80后投资人看得比较多的“还是新经济领域的东西”,因为传统领域比如机械制造业,“很多创新模式实际上我们看不懂。”汪远志认为,这群人自己摆弄手机上网、打游戏,“把自己置于用户的角度,很多新经济领域的东西反而更看得懂。”他同时也说,相对新鲜、风险较高的新经济领域的创新实际上也更吸引他们。
但现实也摆在他们面前:20多岁,对做投资还一知半解,交学费是不可避免的,小额的天使投资是他们练手之地。“天使投资金额比较小”,少量的资金能够买来一定的投资经验。
除去职业经理人投资的项目,这群80后投资人“自己操刀的,大都是天使投资(Angle Investment)”。其中目前曝光度比较高的陈豪,就帮英国的蓝海天使投资管理着3000万美元的天使基金。已经做了两次“天使”的其中一位投资人说,“用来练手”。
每隔一段时间,这群80后投资人都会聚在一起,“在一个私密的环境里”,对挑选出来的四五个项目发表各自的意见。“为了印证彼此对项目的看法。”汪远志说,他自己把这当作是增强项目判断力的一种训练。“不可能因为想吃独食而有所保留。”对一个投资项目,他们更希望有人能一起投。“有时候企业不愿意有太多的股东,那就采用代持的方式进去。”
从实业到资本的一跃
“这是一群天生的商人,赚钱能力很强”,这是杨沛对这群80后财富二代投资人的描述。
在汪远志看来,他觉得这辈子自己只能做个“生意人”,但他所做的生意又注定要和父母的不一样。
如果让他回想小时候的生活,就是“别人家小孩子放学后到处玩,我就得帮助父母照看生意,跟着他们到处跑”。这几乎是汪远志现在所处的这个圈子里30多个人共同的经历,他们中90%以上的人家里都做着各种各样的生意。因此几岁起,或许自己的名字都还写不利落,他们就已经开始拿提成了。
“这导致,他们判断一个人,首先是会不会成为自己的顾客;判断一件事情,着眼点肯定是能不能给自己带来回报。”杨沛说,他们相处的时间中,有40%以上都在谈论具体投资项目、什么项目赚钱。
1982年出生的陈豪,当年在华东理工大学的校园里,“第一次被人看到还是骑自行车,第二次是骑助动车,第三次就换成了汽车”。他的创业开始于旧书,当时大四学生在甩卖旧书,一段时间后来不及卖掉的旧书就只能按斤卖给废品站。基于此他开了一个二手书市场,从废品站按斤购入,然后半价卖出。半年后他在校园里有了自己的门面,所卖商品也从旧书扩展到了化妆品、鞋子、文曲星、电话卡等等。大三时陈豪就通过卖移动的促销手机卡积累了几百万。而在接手英国蓝海天使投资在中国的业务之前,25岁的陈豪已经在管理6家企业了。
“家里都是做商业的,我们很难不走这样一条路。”其中一位80后投资人说,但也不会再走父母曾经走过的老路。“这些产业现在的利润都已经很薄了。”上述人士称,他们的父母也在担心什么时候这些产业会做不下去,所以也在想调整方向。“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势,我进不进入家里的企业,结果并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一场证明自己的游戏?
这是真实的事情。一天,80后投资人这个圈子里的其中一位给另外一位打电话。电话被接起后,打电话那位闷了半天说,“你忙吗?”接电话的说,“不是很忙。”又是一段沉默,然后打电话的又问,“你忙不忙?”接电话的说,“还好,有点。”于是打电话的就说,“那你忙吧。”对话到此结束,据说打电话的这位原来是想约接电话的这位去打游戏。
“他们的内心其实非常孤单,非常需要沟通。”杨沛说,聚会时他们总有说不完的话,当年和陈豪一聊就是3天,“茶馆关门了,转战到办公室”。
尽管已经20出头,但这群人在父母眼里依然只是小孩,尽管在很多时候他们的想法确实很天真,比如“娶个老婆在家帮我打游戏练级”;父母的朋友也把他们当小孩,很多事情不会给他们机会发表意见。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屑于“吃喝玩乐、混沌度日”的所谓富家子生活。这扇门被关上了,“与普通人交朋友”这扇门却没有被打开。据了解,投资项目讨论会现场必须保证一定的私密性,他们才会畅所欲言,“如果有媒体在场,他们会有被卖的感觉”。怕讲不好,会丢家里人和自己的脸。而他们几乎都“不敢找女朋友”。
“他们急于证明自己的能力。”杨沛说,不见得是赚在绝对值上比父母这一辈子更多的钱,“而是要证明自己能够赚钱”。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骨瘦如柴”;20出头的人差不多“个个都是工作狂”,走近了能听到颈椎和脊椎摇动时发出的“咯咯”声;穿着在身上晃荡的西服出入各种场合,“看更多的项目,了解更多的事情,认识更多有价值的人”。
“我们聚会时谈的最多的是赚钱,以及如何赚钱。”汪远志说,不仅仅是VC、PE领域的案例,还有股票投资、房地产投资、股指期货等等,国家的经济走势也是热点话题之一。“只要能赚钱的都会涉及。”
赚到了钱、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之后,又想做什么?
“那是以后的事情。”杨沛说。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 编辑:何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