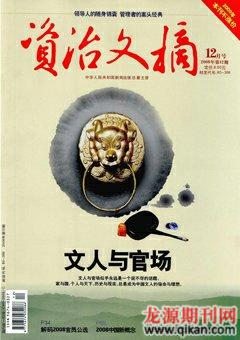走不远的文人王禹
赵锋利
文人就是文人,
文人不可能成为政治意义上的大家,
而只能是工具意义上的文人。
文人不愿意老当文人,喜欢往仕途上挤。“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十年寒窗苦,不就是图个金榜题名时吗?特别是在文坛上卓有建树的一些大文人,总是想找个能实现自身价值施展才华抱负的平台,以酬经邦济世之志。但高处不胜寒,挤上仕途的文人多数走的不太顺。王禹就是这样一个文人。
公元998年(宋真宗咸平元年),大宋王朝第三代皇帝真宗登基之始。这天,天刚蒙蒙亮,汴京城里的大街上聚集了三四百个书生。领头的是新科进士孙何。他们列队为王禹送行。王禹时任知制诰(文字秘书),主管起草皇帝诏令,这是一个多少文人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绝好位子。但王禹却从这个位子上下来了。事情直接起因是他在预修《太宗实录》时对宫中不宜公开的东西毫无掩饰地秉笔直书,被小人们抓住了把柄,在皇帝面前告了刁状。结果龙颜大怒,以“议论轻重其间”的罪名将他罢黜,贬为黄州知州。
孙何他们列队为一个被罢黜之人送行,这在世态炎凉的官场是绝无仅有的。仅此王禹就足以感到欣慰。出城门很远了,他还依依回望,外面的晨雾还没有完全散去,京师城楼变得遥远而又模糊。京城,还能回得来吗?
他这是第三次遭到贬黜了。回首平生,感慨良多:29岁中进士,始任成武主簿,一年后升长州知县。后被宋太宗召进京来,当场殿试。他笔下生花, 洋洋洒洒,太宗连连赞赏,即封为右拾遗、直史馆,紧接着又任左司谏、知制诰,成为了皇帝的近臣。在京师官场上一时如日中天,前景看好。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上了一份《端供箴》,针对朝廷的腐化奢侈,指责大臣们“一裘之费,百家衣裳”, “一食之用,千人口腹”, “顺知府库,聚民膏血”,希望,皇帝多注意那些 “室无环堵”、“地无立锥”的贫苦百姓。第二年京师大旱,他又上疏建议从君到臣依次减少俸禄,主动提出自己首先减俸,以济苍生。
这分明是一剂苦方子。
不买皇帝的账,第一次被贬
喜欢听好话,而不喜欢别人说不好,这似乎是人的天性。下自凡夫俗子,上到帝王执宰,基本上概莫能外。参透此道者大都三缄其口,他们明白犯颜直谏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但王禹仍说这些逆耳之言,这不能不遭到权臣和同僚的憎恶,同时也使皇帝受到了点不大不小的刺激。由欣赏到反感,往往不需要多少过渡。紧接着又发生的一件事,简直就叫皇上对王禹无法容忍了。
淳化二年,庐州有个名叫道安的尼姑,状告左散骑常侍、著名文学家徐铉与妻甥姜氏通奸。姜氏乃道安之嫂,事情说得有鼻子有眼。
这时的王禹身兼多职,除给皇帝起草诏书外,还兼判大理寺事。他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周密勘察,反复论证,确定道安纯属诬陷,提出依法治道安诬告之罪。也不知道安这妖尼施展了何等法术,太宗皇帝竟公开予以袒护,下诏赦免道安。王禹竟不买账,坚持执法为徐铉雪诬,抗疏“请论道安罪”。这样一来皇帝的脸子马上拉了下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着王禹为商州团练副使,即日赴任,不得再签书公事。钦此。
这是王禹第一次被贬逐放。大概是宋太祖曾立下过“不杀士大夫”的誓约,崇尚文治,奖励儒术,希望能“以宽大养士人之正气”。太宗皇帝对王禹没有简单的“咔嚓”了事,而是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惩治办法。
触犯太宗忌讳,再贬滁州
文人毕竟是有用处的,或粉饰太平,或装潢门面,或参与政治… …并不是所有的文人只会风花雪月,咏诗作赋,也有不少治国安邦之才。并且真文人、 大文人太少了,满朝文武百官真正管用的能有几人?宋太宗自然清楚这些。罢黜王禹是出了口恶气,但也少了一个干才。王禹虽不识时务,但没有篡朝的野心, 对皇权不至于构成什么威胁。于是在淳化四年,太宗又召王禹入京,王禹又重新成为副部长级的礼部员外郎,再知制诰。太宗这次多了一个心眼,既要用他,又要防他,特地安排宰相注意他“赋性刚绝,不能容物”的性格,要时时“戒之”。
文人的秉性是难以改变的,有着“991事件”切肤之痛的王禹,在复出之后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认真总结一下经验教训,遇事稍稍钳口,以求自安;要么,一如既往,仍言之所当言,谏之所当谏。王禹选择了第二种。
995年(太宗至道元年),宋太祖的开宝皇后病逝,太宗不成服,群臣不临表。王禹奏曰:“后尝母仪天下,当尊用旧礼”,这一下触犯了太宗的忌讳。王禹再贬滁州。
这对于王禹又是一次致命的沉重打击。苦恼、困惑、悲愤、失落、无奈… …交织在一起。还有,他要找出这次遭贬的原因何在。“虚名既高,忌才者众。直道难进,黜官亦多”,王禹还真的找出了此次出滁的症结。既然“直道难进”那就避直求易吧,这只是一般人的思维方式,对于王禹来讲,就很难说了,能不能改变他的“直道”模式只能是一个悬念。
好了伤疤忘了疼,第三次被贬
事情过去两年后,朝廷的政治结构发生了变化。997年,真宗即位。不服输的王禹抓住机遇,即上疏言事:一、谨边防,通盟好,使辇运之民有所休息 ; 二、 减冗兵,并冗吏,使山泽之饶,稍流于下; 三、艰难选举,使人官不滥; 四、沙汰僧尼,使疲民无耗 ; 五、 亲大臣远小人,使忠良蹇谔之土,知进而不疑,奸险倾巧之徒,知退而有惧。
王禹这五条建议颇有见地。考察宋代政治得失,宋之所以积贫积弱,原因之一是冗兵、冗吏太多。真宗皇帝恐怕当时也不一定有这般见识,可能出于对上一届班子有看法,所以对王禹这五条也就大加赞赏。于是王禹又得以还朝,复为知制诰。
不管是老皇帝,还是新皇帝,心理结构大致都是相同的。他们既不喜欢下级品德高尚,又不喜欢下级才能卓越,而是认为这两种下级都是潜在的威胁。而恰恰两者都具备的王禹偏偏“好了疮疤忘了疼”,淡忘了“直道难进”的反思,依然不避訾议,敢犯雷霆,颇有点不撞倒南墙不回头的味道,以至叫皇帝和小人们抓住了把柄,于是就有了第三次罢黜的悲剧。
王禹一生,宦海沉浮,三起三落。从某种意义上讲,王禹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从政的一个缩影,王禹的沉浮,代表着中国古代文人的心路历程。说白了,文人就是文人,文人不可能成为政治意义上的大家,而只能是工具意义上的文人。
从一定意义上说,文人最多只能在一定社会事务的管理领域内活动,而不可能活跃于政坛,更谈不上甩出什么历史性的大手笔。仕途之中不懂屠龙术是正常的,那是对大政治家的要求。而非理性的表述方式却始终是危险的,因为自身的存在是一切政治活动的基础,过于偏激只会使得一定的社会冲突加剧。文人们并非完全不懂这些,并非看不到宦海波翻浪涌,既有珍贝,也有泥沙,既有平流,也有暗礁。但往往他们总认为天降大任,匡正时弊非我莫属,忍不住要说出来,讲出来。他们还没有完全弄清楚这一种现实:统治阶级思想固化的堡垒在名义上好比一些名山圣水或文化古迹之类的玩艺儿,岂是容人随意添加乱写乱画的,哪怕你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一旦新式的建筑图在根本上否定了庞大的旧式建筑,那么悲剧只能接二连三地发生。
我们无意去指责王禹,相反更多的是对他直道直言的耿直性格的敬重。因为有了性格的耿直,才能产生正直的人格。我想王禹、范仲淹、苏轼他们都会有这样的基本信条:人毕竟是人,人不仅需要衣食住行功名利禄的满足,更需要人格的正直。所以他们在不拒绝功名利禄的同时,又不去趋奉功名利禄。正是他们这些正直的人格,为几千年封建时代的历史涂抹上了几许亮色,起码能让我们在打开尘封的历史时不至于因为那上面凝结了太多的由一己私欲而起的贪婪与龌龊而感到过于失望。
(摘自《中外文摘》 2004年第22期)
王禹简介
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巨野(今属山东)人,出身贫寒,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当过翰林学士,三任知制诰,又三次受黜外放,他为人刚直,怀有正直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和来自儒家传统的政治伦理观,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敢于说话。他自称要“兼磨断佞剑,拟树直言旗。”在第三次遭贬斥去黄州时,还是很不服气地寄诗给当权者说:“未甘便葬江鱼腹,敢向台阶请罪名。”他把自己的文集题作《小畜集》,就是表示有“兼济天下” 之志。他的散文,言之有物,清丽疏朗,在宋初文坛上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