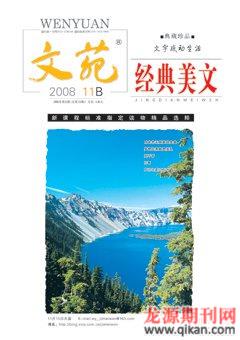我和父亲里根
(美)帕蒂·戴维斯
一
在我大约10岁的时候,父亲和我开车去一个在我整个孩提时代都属于我们家的牧场。在路上,我们谈到了父亲的爱马南希·D,还有她那即将出生的幼驹。这可不是一次计划中的生育:一匹别人赠送给父亲的阿帕卢萨雄马,勇敢地跨越过两道围栏,与南希·D相会,并且成功地当了爸爸。
刚开进牧场的粮仓空地,就看见了负责照看牧场的雷,我们立刻意识到,一定发生了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他的脸上带着明显的泪痕,双眼因哭泣而红肿,他低着头站在父亲面前,不愿直视父亲的目光。前一天夜里,南希·D因未知的病毒感染而身亡。没有任何症状,没有任何迹象,病毒就这样出其不意地、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杀害了南希·D,还有她肚子里未出生的孩子!
我的眼里立刻噙满泪水,因为南希·D是我生平骑过的第一匹马。当我还很小的时候,通常是父亲骑在马上,把我抱放在他前面的马鞍上。等我稍大些时,他举我坐到南希·D的背上,牵着她带我溜圈。这天,当我注视着背对蔚蓝色晴空的父亲时,发现他的眼里竟然没有一滴泪!他抬着头,望着那一片蔚蓝,眼睛里透出的是无限的深情、无限的温柔……在那一刻,思绪仿佛正把他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你为什么不哭呢?”我含着眼泪问父亲。
他慈爱地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望着我的眼睛。“因为,”他说道,“我正在回想和南希·D经历的所有美好时光。我们一起度过了那么多令人怀念的光景。”
这是我人生中关于如何看待死亡的第一堂课——超越它,去回顾已有的生活,哪怕仅有零星美好瞬间的存在,那也是生活和生命的意义,那也是珍贵的记忆。这些都是我们在生命的旅途中要经历和承受的,也是父亲正在努力教给我的。
二
父亲教会他所有的孩子骑自行车,都是用一样的方式。当助学车轮被拿掉后,他就跟在我们后面跑,用手抓住车座后部,好让我们有安全感。某一天,在我们无意识的情况下,他会松开手。我还记得,我回头望去,期望看到父亲还在保护着我时,却发现我已经在没有父亲的辅助下,自己骑出了一段距离——他正站在那儿,冲我招着手,微笑着。
我和同胞兄弟姐妹们都有着相同的记忆——童年的回忆,但是,我们长大以后的路却不尽相同。我们之间有年龄差。莫莉和迈克尔几乎比我大10岁,罗恩比我小6岁。他们不是在那激情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长大的——他们不是在此之前就过了青春期,就是在一切平息了以后才到青春期。而我却被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我这一代人,经过一路跌跌撞撞,至今已到了积累自己人生财富和智慧的阶段。但当我们回首往昔,观看身后留下的被扯断的精神及情感的纽带时,我们注意到了另一点:还有一些维系着的纽带没有被扯断。无论我们怎样努力想把自己从这条纽带上挣开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注定是和我们的前辈、和生育我们的父母、和我们甚至不认识的祖先血肉相连的。而此刻,我们终于长大了,知道要用一双充满爱心的手牵着这些纽带,顺着它们,让它们带我们回到当年断开的地方。
在历史记载上,没有哪一代人曾像出生在生育高峰——在无刺激的20世纪50年代中吃母乳长大的这一代人那样,情绪激昂地在文艺复兴活动中专门和父母抗争。现在,我们均已到了不惑之年。我们平静下来,目光变得清晰,但我们正在失去自己的父母。
因为我们当年斗争得太激烈,走得太远,我们现在的回程就会更长。我们要经过漫长而深刻的心路历程,才能使我们的心灵重新归位,来体会将要与自己双亲道别的感受。我们其中那些曾狂怒地走完上世纪60年代的人们,可能当初这样做是因为革命,但是,我们忘记了首先应松开自己心灵上的桎梏。现在,随着父母一辈日渐衰老,我们的心灵开始呼唤,呼唤着我们要把心胸比以往再敞开一些,找回我们在像吸毒上瘾一样不顾一切发泄愤怒以前所拥有的纯真和爱。
我们中间有些人已经返途。我们的双脚鲜血淋漓,但是我们的心灵却得到了升华。有时我反躬自问,如果我父母没有现在这样长寿,或是我没有经过自己的反思而翻然悔悟的话,我的生活又将会是什么样。可能我回来得太晚了,可能我已被留在了无言的距离里。
三
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和父母过不去,我对着整个美国发出最强烈的反抗之声。我不赞同父亲的政治决策,我无情地将自己的观点畅言无忌。一个与我同龄的女友曾对我说:“无可非议的是,得有某个人当咱们这一代的代言人,能代表我们大家说出共有的愤怒。在某种意义上,你就是我们这一代的象征——气愤的女儿当头棒喝她的父亲。然而凑巧的是,你的父亲是美国总统。”
“太棒了,”我答道,“我真高兴能完成这个任务。”
好几次,我父亲都请求我去他那里谈谈,听听他的观点。我的回答则是,我早已知道了他的观点。现在一想起这些,我就不寒而栗。即使我已经知道了他的观点又有何妨呢?他只是想要交流,而我却拒绝了他,伤害了他的感情。我还自以为这是在为裁军和世界和平出力呢。核武器固然危险和可怕,但如果我们这一代连自己的愤怒是多么伤人都不明白的话。岂不是同样危险和可怕吗?
时间与疾病加在一起,使我即使有千言万语,也无法向父亲诉说。如今,他的头不再向外歪斜,他的眼睛总是看着我们的上方。我们已经度过了纷乱和互不联系的那段岁月,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对他亲口说出我的忏悔。
私下里,我经常嫉妒我的兄弟姐妹,因为在政治观点上,他们与父亲从来不像我与父亲那样相左。这使他们的生活更为和谐。而我的不和谐却经常出现,现在仍是这样。
莫莉一直是个彻底的保守派—— 一个忠实的共和党人。我弟弟罗恩则持中间立场—— 一块他自己圈定的非军事化区域。迈克尔则成功地当上了保守派的广播节目主持人。他对共和党的忠诚则从未被质疑过。
我现在经常希望,如果当初我的信仰能少一些、更有弹性一些、更适中一些就好了。我后悔自己在表述政治信仰时所用的方式,其实任何信仰的本身,根本是不会改变的。现在,当父亲已经离职这么多年后,当他不再参与政治讨论时,或他根本不再关注政治问题时,我们之间的不同,对我来说,始终是个缺口,一道永远没有填平的沟壑。
于是我选择避开这个缺口,走向另一个方向。我选择只当他的女儿。
四
现在,我总是希望能再听听父亲的声音和他讲的故事,他那蔚蓝闪烁的眼睛,照亮了孩子的心灵和想象力,但是我只能用回声来激励自己。
有一次,在我们去牧场的路上,他停住车,告诉一个正在山坡上的人说,他所采摘的蓝羽扇豆是受保护的植物。父亲非常礼貌地对他解释着,于是那個人抓着他的非法采摘之物,马上从山坡上走了下来。父亲总是希望,无论何时何地,花草和野生动物都应有自己的归属之地。我在5岁时,就能辨认出哪条是响尾蛇,我知道用绕一个大圈的方法来躲避它。我也知道,除非万不得已,千万别伤害它。
他坚信应该让孩子们对生活中的灾难做好准备,否则一旦灾祸发生,震惊和突变将使他们措手不及。他会给我们设想一些情景,让我们面对和处理,然后耐心地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面对人生危难,唯有知识才能给予帮助。
有一次他问我,“如果你的睡房起了火,堵住通往门口的路,你怎么办?”
在电影里看过许多类似情景,我立刻回答道,“我跑着穿过去。”
“那你就会死掉的,”父亲平静地说道,“当你与火焰的距离近至两英尺时,高温就会灼伤你的肺。”
“那我就打碎玻璃跑到院子里去。”
“那好,”他点头称道,“那你用什么方法打碎玻璃呢?”
“用椅子。”
我几乎立刻清楚地意识到,教程的重要部分即将开始了。因为这时的父亲,就会探身向我用非常缓慢但认真的语气对我说,急切地希望他的忠告能在我心中扎根。“你拉出一个抽屉,”他这样告诉我,“用它来击破玻璃。那样形成的就是一个齐整的缺口,你爬出来时就不会被玻璃划伤了。”
他教会我怎样防御火灾、怎样面对空袭警报和地震,但是他就是忘记了教会我如何面对将要失去他这一灾难。他没有教我用任何方法来面对我的翻然悔悟。这些是深藏在我内心的痛苦记忆,真希望还有治愈的可能,可我还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