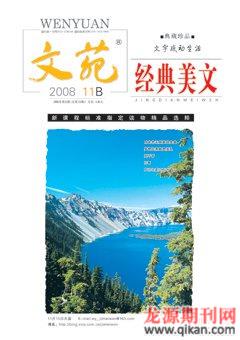寻找第一个自我
苏小红
法国哲学家、生命哲学和直觉主义代表柏格森在他的哲学著作《时间与自由意志》中讲道:人有两个自我。第二个自我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往往把第一个自我掩盖起来,成为第一个自我的影子。
生命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莎士比亚也曾这样慨叹。
这种现象生活中并不少见。我们生活在我们自己之外,几乎看不到我们自己的任何东西,只看到自己的影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为了自己而生活,而是为了外界生活的需要而活着。我们不在思想,而在说话;我们不在动作,而在被外在所动作,从而成了外界的奴隶。
柏格森说:“要自由地动作即是要恢复对于自己的掌握并回到纯粹的绵延。”
柏格森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犹太思想家,与爱因斯坦、弗洛伊德和马丁·布伯并行。他所提出的“绵延”这一核心概念,是指人的心理深处的一种意识状态,一个连续的无间断的心理流。在绵延中,只有一个纯粹的流动,它是先后无别的陆续出现,是过去、现在、将来的互相渗透。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为了社会生活的需要等功利目的,本来连续的相互渗透的意识形态往往被分裂,让我们无法把握生命的流动和本质。
如果一百个人的眼里会品读出一百个哈姆雷特,那就姑且让我把柏格森的“绵延”理解为萨特所说的“本质”。什么是本质?萨特说本质就是选择的常数。人的心理深处,“一个连续的无间断的心理流”,不正是一次又一次选择为常数的本质吗?它掩盖在第二个自我的影子背后。
恢复对自己的掌握,就是要寻找第一个自我。其途径是有必要组织内在的抵抗,以保持身上的灵动想象和自由天性,不被外在所奴役。一旦拥有这种灵动想象和自由天性,我们便寻找到属于自我的精神家园,一个完全属于自我的空间。
正如多丽丝·莱辛幽幽的发问:“你可仍保有自己的空间?你的灵魂,你自有的,不可缺少的空间,在那里你的声音可以对你一人说话,在那里你可以纵情梦想。”
许多人迷失了方向,终其一生也找不到回归的门扉。而在163年前,瓦尔登湖畔的冰还未完全消融的一天,美国作家梭罗向《小妇人》的作者阿尔卡特(Alcott)借来一柄斧头,独自来到瓦尔登森林,砍伐高耸的松树以建造他的小木屋,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天地。
吸引梭罗住到湖畔的原因,是他“要生活得有闲暇,并有机会看到春天的来临。”因为在梭罗看来,被生活所奴役,整天劳作不息却还无法改善生活,这是极其痛苦和可怜的。他用亲身实践告诉世人——满足人最基本的生存要求并不困难;当一个人脑海中充斥着一个又一个欲望时,他便会成为生活的奴隶。
在瓦尔登湖畔两年多的独居日子里,梭罗静谧而又寂寞。他打趣说:“我爱孤独。我没有碰到比寂寞更好的同伴了。”瓦尔登湖畔的小木屋成了他身躯和灵魂的居所,在这个精神家园里,他与瓦尔登森林的生灵为伴,凝望苍穹的星月沉思,与自然和自我对话。当你触碰梭罗的沉思,月光下的瓦尔登湖便会泛起阵阵涟漪,湖水的清澈,荡漾着,从你的眼神流淌入心田……
或许梭罗只是个孤独的过客,但他活得简单而馥郁,快乐而纯粹。我甚而猜想,一定是他在瓦尔登湖畔沉思的时候,思想抖落,坠入湖中,摇曳的水击破了影子,梭罗看到了第一个自我。
你呢?
毕竟,無尽的、不可测的时间长河啊,分给每个人的是多么少的一部分,它立刻就被永恒吞噬了。寻找第一个自我,也许只是闪念之间,却容不得徘徊、犹豫和丝毫的迟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