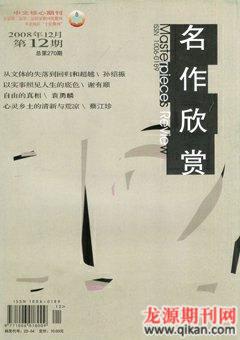服饰之战:绚烂下的悲凉
邓如冰
对张爱玲这样的一位“衣服狂”(clothes-crazy)来说,从服饰的角度去进入和理解她的作品,是我们曾长期忽视而又极其必要的方式。“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服装是随身带着的袖珍戏剧。”“我们各自生活在自己的衣服里。”这样的语言并不是这位才气纵横的女作家头脑中某一时刻的电光一闪,而是某种事物长期占据她的神经以至于进入她的思维而呈现的一种表达惯性。这一事物就是张爱玲一生的最爱——服饰。在去世的三年前,她在《对照记》中以半调侃的口吻将自己称为“衣服狂”(clothes-crazy)①,已在事实上注解了服饰在其整个生命和创作中的重要性。而这一切,要从她1943年正式登上文坛后的第一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说起。
正是在这部初出茅庐的小说里,服饰就已经显示了它非凡的意义。服饰如此深刻地参与到了情节发展和人物的心理变化之中,以至于如果不仔细分析其中的服饰描写,简直不能很好地理解小说的人物、结构和主题。小说中关于服饰描写的篇幅很多,每一款服装、每一件饰物都美轮美奂:姜汁黄朵云绉旗袍、瓷青薄绸旗袍、夜蓝绉纱包头、高跟织金拖鞋、朱漆描金折枝梅木屐、灿灿精光的金刚石手镯……共同织就了一个绚烂华美的服饰世界。然而,绚烂华美只是小说的表层,在故事深处却是另一番景象:危机四伏、烽烟四起,你来我往、机关算尽——每一件服饰都意味着微妙的交锋。简言之,《沉香屑 第一炉香》是一场围绕服饰进行的女人之间的战争,战争双方打头阵的是这两位:葛薇龙和她的姑妈梁太太。
像许多二十世纪初期的女学生一样,薇龙把人生目标设计为“个人奋斗”式的一生,她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改变自己的命运。来到姑妈家试图讨要生活费和学费,就是为了好好读书,完成在香港的学业。然而,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她就由“个人奋斗”变成了“沉沦堕落”,其间的既巨大又微妙的心理变化与服饰息息相关。薇龙第一次发现服饰的“不对劲”是在她家的女佣人陈妈身上:
(陈妈)穿着一件簇新蓝竹布罩衫,浆得挺硬。人一窘,便在蓝布褂里打旋磨,擦得那竹布淅沥沙啦响。她和梁太太家的睇睇和睨儿一般的打着辫子,她那根辫子却扎得杀气腾腾,像武侠小说里的九节钢鞭。薇龙忽然之间觉得自己并不认识她,从来没有用客观的眼光看过她一眼——原来自己家里做熟了的佣人是这样的上不得台盘!
薇龙貌似“客观”的眼光其实已经带上了很强的主观色彩,就是因为之前曾经在梁太太家作过短暂的停留,她下意识地开始把陈妈与梁家的佣人睇睇和睨儿进行对比,后者是甜甜腻腻的“糖醋排骨之流”,相比之下,陈妈自然“杀气腾腾”、“上不得台盘”了。陈妈穿的“蓝竹布罩衫”其实薇龙并不陌生,她在学校长期穿的制服就是“翠蓝竹布衫”。“竹布”是一种平纹棉布,因其价格低廉,多为平民和贫穷家庭所用,自然是与富贵人家所钟爱的纱、绸、缎不能同日而语的。薇龙仅仅是几天前在梁家打了个转,就已经不由自主地受到了梁家“淫逸空气”的影响,自己给自己抬高了身价。她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还没有正式走进姑妈的门,她就已经不是从前的她了。——服饰如此精微地表现了人物的心理变化。
薇龙自以为是清醒、精明的,几天前在姑妈家的头一次会面中,她一边发现了姑妈名不虚传的“坏名声”:“如今看这情形,竟是真的了,我平白来搅在浑水里,女孩子家,就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一边又告诫自己:“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但姑妈是比她老练得多、“有本领”得多的人,她给薇龙设计的圈套是不动声色的:
梁太太道:“你有打网球的衣服么?”薇龙道:“就是学校里的运动衣。”梁太太道:“哦!我知道,老长的灯笼裤子,怪模怪样的,你拿我的运动衣去试试尺寸,明天裁缝来了,我叫他给你做去。”便叫睨儿去寻出一件鹅黄丝质衬衫,鸽灰短裤;薇龙穿了觉得太大,睨儿替她用别针把腰间折了起来。
在不经意间,姑妈通过贬低薇龙过去的衣服否定了她的过去(包括她过去的理想),并通过为她设计新的衣服设计了她的未来——成为一个像她一样的人,以身体和美色换取金钱,一个“小号”的梁太太。此刻的薇龙在意识中还在做着她的求学之梦,而那丝质衬衫柔滑的质地和柔和的色彩却已悄无声息地在她的心中扎下根来,当她这时再来看本来极熟悉的穿着“蓝布褂”的陈妈时,就免不了要另换一种“眼光”了。
梁太太——薇龙姑妈——有她自己的生活法则,她是个彻底的“物质主义者”,但她不要薇龙式的“个人奋斗”,她愿以身体、美貌、青春、生命的代价换取物质。年轻时她“独排众议,毅然嫁了一个年逾耳顺的富人,专候他死。他死了,可惜死得略微晚了些——她已经老了;她永远也不能填满心里的饥荒。”“她需要爱——许多人的爱”,她得到爱的方法是利用薇龙这样的年轻女子为她勾引男性,她再利用这些男性填补内心的饥荒。梁太太像个毒兽,眼睛半睁半闭,有着攫取目光,专以别人的血来填补内心的饥荒。她是一个毒气森然的“女魔鬼”,这一点,从她第一次出现在薇龙眼前的装扮看就已表现得很明显:
汽车门开了,一个娇小个子的西装少妇跨出车来,一身黑,黑草帽檐上垂下绿色的面网,面网上扣着一个指甲大小的绿宝石蜘蛛,在日光中闪闪烁烁,正爬在她腮帮子上,一亮一暗,亮的时候像一颗欲坠未坠的泪珠,暗的时候便像一粒青痣。那面网足有两三码长,像围巾似的兜在肩上,飘飘拂拂。
……毕竟上了几岁年纪,白腻中略透青苍,嘴唇上一抹紫黑色的胭脂,是这一季巴黎新拟的“桑子红”。薇龙却认识那一双似睡非睡的眼睛……美人老去了,眼睛却没有老。
“一身黑”的梁太太是美丽、神秘的,但面网上的“指甲大小的绿宝石蜘蛛”却暗示了她身上的“毒性”,嘴唇上紫黑的胭脂像将干未干的血迹,更显诡谲狠毒——这是一只美丽的毒蜘蛛。薇龙总是不由自主地将她与危险、狠毒的动物联系在一起,通过她手上的道具、她身边的环境感受到这一点:姑妈拿着扇子时,感到“扇子里筛入几丝黄金色的阳光,拂过她的嘴边,正像一只老虎猫的须,振振欲飞。”“……仙人掌,正是含苞欲放,那苍绿的厚叶子,四下里探着头,像一巢青蛇,那枝头的一捻红,便像吐出的蛇信子。”她那擦满蔻丹的手指总被写成是“血滴滴”的:
梁太太正擦完蔻丹,尖尖地翘着两只手,等它干。两只雪白的手,仿佛才上过梭子似的,夹破了指尖,血滴滴的。
梁太太一面笑,一面把一只血滴滴的食指点住了薇龙……
嘴唇上的血,指头上的血,梁太太就是这“鬼界”里面的人面兽身的“吸血鬼”,她的家是个“鬼气森森”的世界。这个“鬼界”的基本法则是以身体交换物质,只要来到这个“鬼界”,不管是哪个女性,都会变成“女鬼”。“糖醋排骨”睇睇和睨儿(名字本身就包含着梁太太式的“风情、窥视、夺取”)就是证明,而薇龙即将成为鬼界中的又一名“新鬼”。
在薇龙和姑妈之间,一直有着微妙而激烈的战争:姑妈要拉拢薇龙,就要“进攻”,要她彻底成为自己的奴隶,彻底臣服鬼界法则;薇龙则要“抗争”,争取利用姑妈的钱“好好念书”,实现她的“个人奋斗”之梦,抵抗女性以身体换取物质的命运。而在这进门之前的第一个回合中,薇龙就已败北,——尽管她并未完全意识到。
第二个回合发生在来到梁家的第一天,虽然薇龙凭直觉感到姑妈家是个危险的地方,并且她如林黛玉进贾府般的时时小心,步步在意,自以为“行得正,立得正”,却在这第一个夜晚就一头钻进了梁太太为她精心设计的圈套——衣橱中:
薇龙打开了皮箱,预备把衣服腾到抽屉里,开了壁橱一看,里面却挂满了衣服,金翠辉煌,不觉咦了一声道:“这是谁的?想必是姑妈忘了把这橱腾空出来。”她到底不脱孩子气,忍不住锁上了房门,偷偷的一件一件试着穿,却都合身,她突然省悟,原来这都是姑妈特地为她置备的。家常的织锦袍子,纱的,绸的,软缎的,短外套,长外套,海滩上用的披风,睡衣,浴衣,夜礼服,喝鸡尾酒的下午服,在家见客穿的半正式的晚餐服,色色俱全。一个女学生哪里用得了这么多?薇龙连忙把身上的一件晚餐服剥了下来,向床上一抛,人也就膝盖一软,在床上坐下了,脸上一阵一阵的发热,低声道:“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讨人,有什么分别?”坐了一会,又站起来把衣服一件一件重新挂在衣架上,衣服的肋下原先挂着白缎子小荷包,装满了丁香花末子,熏得满橱香喷喷的。……薇龙一夜也不曾合眼,才合眼便恍惚在那里试衣服,试了一件又一件。毛织品,毛茸茸的像富于挑拨性的爵士乐;厚沉沉的丝绒,像忧郁的古典化的歌剧的主题歌;柔滑的软缎,像《蓝色多瑙河》,凉阴阴的匝着人,流遍了全身。才迷迷糊糊盹了一会,音乐调子一变,又惊醒了。楼下正奏着气喘吁吁的伦巴舞曲,薇龙不由想起壁橱里那条紫色电光绸的长裙子,跳起伦巴舞来,一踢一踢,淅沥沙啦响。想到这里,便细声对楼下的一切说道:“看看也好!”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将原文引下,是因为这一夜的“衣橱经验”对小说的情节发展和薇龙心理的变化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如果说上一次姑妈让薇龙试穿运动服只是“小试牛刀”的试探的话,这一次的“金翠辉煌”的衣橱就是一个华丽的圈套、一个美丽的引诱、一次温情 的腐蚀、一次强大又凌厉的全面的宣战。那一排排款式不同、质地上乘的衣裙就是姑妈的武器,它们将薇龙的防线层层剥落,终于以温情的面目尖锐地刺中了薇龙的身体。尽管薇龙的意识中清楚地知道这些衣服的真正含义:“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讨人,有什么分别?”然而梦境之中的她还是禁不住一件一件地试穿那些衣服。再也明显不过的是,梦境中的薇龙与现实中的薇龙是合二为一的,那些服饰如富贵、柔美、高雅的音乐般浸润着她的整个身心,她将来可能拥有的“一般女孩子们所憧憬着的”物质生活已在她眼前徐徐展开,并已开始在服饰的暗示下(毛茸茸的、厚沉沉的、古典性的、挑拨性的、忧郁的、柔滑的……)感受那将要到来的丰富的、多彩的、复杂的、不再单调的生活。薇龙在意识中不能认同这一切,但她在梦境中接受了这些诱惑。——这一次的“衣橱体验”是薇龙心理变化的分水岭,是她的“个人奋斗”的理想与出卖身体的现实之间的激烈斗争。当她决定住下来“看看也好”时,象征着她将要向姑妈屈服,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交到这个“女魔鬼”的手中。
薇龙和姑妈之间的战争还在进行着,只不过方式更加隐晦:她悄悄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夜里念书念到天亮,还悄悄计划着找一个“合适的人”,幻想着“遇到真正喜欢我的人,自然会明白的,决不会相信那些无聊的流言”。她虚弱地抗争着,然而姑妈手中的绳索却越套越紧。姑妈与薇龙之间第三回合的较量发生在一个雨夜,这一次,她还与一位男性同伙——老情人汕头搪瓷大王司徒协联手,齐打伙地一起对薇龙实施诱拐。他们试图降伏薇龙的武器是一只饰物——“金刚石手镯”:
车厢里没有点灯,可是那镯子的灿灿精光,却把梁太太的红指甲照亮了。……薇龙托着梁太太的手,只管啧啧称赏,不想喀拉一声,说时迟,那时快,司徒协已经探过手来给她戴上了同样的一只金刚石镯子,那过程的迅疾便和侦探出其不意地给犯人套上手铐一般。薇龙吓了一跳,一时说不出话,只管把手去解那镯子,想把它硬褪下来。……
手镯如手铐,假如薇龙接受了它,就意味成了姑妈的“犯人”,一生都被拷住,不得解脱。薇龙非常明白这只手镯的分量,她已经看见姑妈带着一蓬一蓬的杀气向自己步步逼近,“梁太太牺牲年青女孩子来笼络司徒协,不见得是第一次。她需要薇龙作同样的牺牲,也不见得限于这一次”。她开始意识到,在这场“战争”中,自己不是姑妈的对手,她想到了逃跑:“唯一推却的办法是离开这儿。”
然而,兵败如山倒。“三个月的工夫,她对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这三个月,正是薇龙“混”在衣橱的三个月:“她得了许多穿衣服的机会:晚宴,茶会,音乐会,牌局。”那一排排不同款式的衣服把她领到了色彩各异的物质生活中,让她“穿也穿了,吃也吃了,交际场中,也小小地有了些名了;普通一般女孩子们所憧憬着的一切,都尝试到了”。但同时,也把她的意志一点一点地腐蚀掉了。姑妈的家,其实就是一个高级妓院,来来去去的都是一些妓女和嫖客:居住在这里的都是清一色的女性,她们都是给梁太太弄人的妓女,睇睇、睨儿、薇龙,包括梁太太自己,无不如此;每一个来到这儿的男人,司徒协、乔琪乔、醉醺醺的英国军官,都是寻欢作乐、醉生梦死的嫖客。薇龙爱上了花花公子乔琪乔,然而乔琪乔也只不过是把他当作妓女,这一点,薇龙从第一次见到他时就感觉到了:
薇龙那天穿着一件瓷青薄绸旗袍,给他那双眼睛一看,她觉得她的手臂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也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
这个绝妙的比喻恰当地传达出薇龙的尴尬感受:乔琪乔那双阅人无数的眼睛已遍览她的身体,而且是她主动送上门将自己的身体交给他的。实际上,在他的眼中,薇龙与一个卖身的妓女没有什么两样,他先是引诱、然后又抛弃了她:“我不能答应你结婚,我也不能答应你爱,我只能答应你快乐。”他玩世不恭、事无忌惮地剥削着薇龙的身体、蹂躏着她的情感。他也是梁太太的同谋者,他们共同谋划并期待着薇龙成为他们共同的奴隶。
三个月的工夫,“鬼界”的法则通过身上的衣服渗入到血液中,薇龙的人生观也完全改变,当初“好好读书”的雄心壮志烟消云散,变成了“活到哪里算哪里”的消极悲观。薇龙最后向梁太太的“投降”也是以她对手镯的态度的转变为标志的:
薇龙垂着头,小声道:“我没有钱,但是……我可以赚钱。”梁太太向她瞟了一眼,咬着嘴唇,微微一笑。薇龙被她激红了脸,辩道:“怎么见得我不能赚钱?我并没问司徒协开口要什么,他就给了我那只手镯。”
当葛薇龙彻底接受手镯的时候,就是她彻底“败北”、彻底向姑妈臣服的时候:她接受了手镯、衣服——衣橱里的一切,接受了乔琪乔、司徒协——向她索取身体的一切男性,接受了姑妈为自己设计的角色——以身体换取金钱,接受了“就等于卖了给梁太太与乔琪乔,不是替乔琪乔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的命运。她自己终于也成了他们的同伙,与他们一起残酷地践踏着自己的身体、青春、尊严、生命,终致把灵魂放逐到“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之中。
在张爱玲的眼里,现实生活与薇龙那装满华美服饰的衣橱是具有某种同质性的:
衣橱里黑洞洞的,丁香末子香得使人发晕。那里面还是悠久的过去的空气,温雅、悠闲、无所谓时间。
散发着熏人气息的衣橱是一个美丽、充满诱惑、然而却致命的圈套,象征着那“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的现实”,表面极为绚烂,实质却无比荒凉。像薇龙这样的女性自踏出家门,就注定会走向“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的命运,仿佛身不由己地踏入了充满毒水的泥潭,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溃烂和堕落,身心满是创痛。张爱玲写薇龙的悲剧,不是因为对她个人失望,而是因为对现实失望,对人、尤其对女人的终极命运感到悲凉。葛薇龙的悲剧之所以成为悲剧,不是因为她个人“自甘堕落”,而是因为她是在奋斗之时的堕落、抗争之后的颓败、飞升之后的下坠,因此才显得格外惊心和悲凉。她始终在与自己的内心作战,在坚守理想和向现实妥协、在她希望成为和不愿意变成的那个人之间作战,但她注定要成为一个战败者。同时,她也始终在与另一个女人作战,这个女人要把她变成她不愿意成为的那个人,而这个女人是她的亲人。这悲凉中的悲凉。——在张爱玲的笔下,女性在“铁闺阁”内被男性压迫的命运是一种常态,也不是她的创举,她的惊人之处,是善于写女性之间的战争,这样的战争常常发生在家庭之内、至亲之间,在不经意间,一个女人死在了另一个女人的杀人不见血的刀下,——这样的模式,贯穿于整部《传奇》之中。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服饰的地位如此重要,它每一次出现都推动着情节的发展,揭示着人物内心的变化,预示着人物命运的起落。这是张爱玲这个“衣服狂”必然会在她的小说中采取的无意识行为。不仅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在整部《传奇》里,服饰结构着小说,塑造着人物,还更是一个庞大的象征体系,它的深刻寓意正待我们一一揭示。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
①张爱玲《对照记》,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