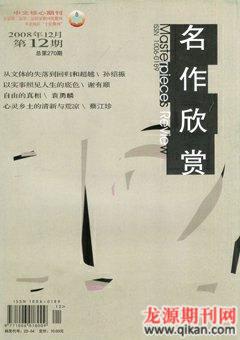新旧道德的“对话”
陈桂良
在茅盾创作的短篇小说中,《水藻行》是一篇独特的并具有人性、人道意义的短篇小说。小说写于1936年2月,由日本作家山上正义译成日文,发表于1937年5月东京《改造》杂志19卷5期,原文则刊于同年6月上海《月报》1卷6期。这是茅盾应日本《改造》杂志社的山本实彦先生之约撰写的,唯一的一篇先在国外发表的小说。小说发表后,并未在国内产生像《春蚕》《林家铺子》等作品那样的强烈反响。因为,在人们心目中茅盾是以政治家的头脑、社会科学家的眼光从事文学创作的,他的作品几乎都具有政治意味和社会色彩,都是国家、民族、社会重大问题的不同层面的反映。而在当时抗日战争时期,《水藻行》不仅没有一丝抗日的影子,也未正面描写农村的尖锐矛盾和斗争,只描写了农村中两男一女眼泪欢笑吃饭睡觉与恋爱等共同生活的情景,难怪作品在当时国内遭到冷遇。然而,《水藻行》之所以这样写,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外国读者的阅读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作者在题材和创作方法上进行多样化尝试的一种体现。因为在日常生活情感纠葛的背后,同样可以反映农民的追求和反抗。确如鲁迅先生当年在介绍《水藻行》等一批短篇小说给日本读者时说的那样:“……创作中的短篇小说是较有成绩的,尽管这些作品还称不上什么杰作,要是比起最近流行的外国人写的,以中国事情为题材的东西来,却并不显得更低劣。从真实这点来看,应该说是很优秀的。”①
《水藻行》主要从人性视角切入描写财喜、秀生、秀生妻子之间的情感纠葛,侧重表现农村伦理道德和伦常观念的变化。其中的男主角农民财喜,不同于以往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那种由于苦难生活的重压,从肉体到灵魂都被摧垮了、扭曲了的病态的农民形象。他不仅有健全的体魄,还有健全的灵魂。②他有高大的身材,厚实的胸膛,两只臂膊像一对钢钳。他热爱劳动,且是干活的好手,浑身有着使不完的力气。尽管生活把他剥夺得只剩下光杆一身,但他并不像思想保守的老通宝那样“认命”,敢于向贫困挑战,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新的生活。他生性善良,富有人道主义意识,同情秀生,“真可怜呵,病、穷、心里又懊恼”。他帮助秀生撑起这个极艰难的家,粗活重活一马当先。他也很关心秀生,当秀生对生活失去信心,认为“死了干净”时,他希望秀生能好好活着;当秀生满身是雪,冷得缩成一团蹲在船边的时候,他将自己的那件破棉袄盖在他的身上;秀生发病时,天没亮,他就去城里药铺去为他赎药。苦难生活的重压,并没有压垮他的肉体和灵魂,反而磨砺了超乎常人的意志和力量。当仗势欺人的乡长硬逼着病在床上的秀生去筑路时,他能挺身而出,敢于抡起“一对钢钳”一样的臂膊,向乡长发出“你这狗,给我滚出去”的怒吼;当秀生担心乡长去报“局”惩罚他,他不顾个人安危,“天塌下来,有我财喜”,颇有些“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侠客气概。在这里,农民身上的那些闪光的东西,如任劳任怨,正直善良,乐观向上,见义勇为,救弱扶贫等种种美德得到了充分表现,让人们看到了农民前进的动力。
然而,像财喜这样本应过上富裕生活的农民,却成了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赤贫户,虽已近不惑之年,却没有家室妻小,只好寄居在堂侄秀生家里谋生,这是为什么呢?与财喜相比,秀生年轻十岁,但却显得比财喜还要苍老,面孔没有血色、浮肿、臂膊消瘦如干柴。“吃了今天的,没有明天;当了夏衣,赎不出冬衣”的极度贫困和地方官僚的催粮、收捐、讨债,逼得他苦不堪言,以至于产生“我活厌了,活着是受罪”的想法,这又是为什么呢?通过对“为什么”的探问,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深刻社会意义的理解。小说通过描写财喜和秀生比老通宝还落魄的生活遭遇,意在探索农民的贫困生活日甚一日恶化下去的原因,强化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本质的揭示。这是小说的一个方面的意义。
《水藻行》在展示苦难时代农民命运的同时,又从人性视角描写农民独特的性爱关系,透视农村伦理道德观念的新变化,以此折射出那个时代农民丰富的精神世界,则别具一种深刻性。小说写财喜寄居秀生家,日久天长,与同样具有体格健壮、充满青春活力的秀生妻子相爱后产生的情感纠葛。在财喜看来,秀生,一个等于病废的男人,配不上他的妻子。所以“确信他们这一对真不配”,而秀生的妻子和他在一起才是相配的,“那女人应该享受做一个人的权利”。 财喜把健康和劳动看作是男女相欢恋的理由,是衡量男女配与不配的尺度。这里反应了财喜对传统伦理观念的蔑视,对于享受应得的精神生活的追求。可以说,秀生妻子的怀孕,既是他们俩人性本能的自然情欲所致,也是财喜的这种新道德观指导的结果。然而,这种新道德观与传统旧道德观之间产生冲突则势所必然,两者之间的“对话”也自然难免。
小说第二部分写财喜在草垛旁看见挺着大肚子的秀生妻子,财喜的关心带出了她对另一件使她伤胎气肚子痛事情的诉苦:
“昨夜里,他又寻我的气……骂了一会儿,小肚子旁边吃了他一踢。恐怕是伤了胎气了……”
财喜却怒叫道:“怎么?你不声张,让他打?他是哪一门子的好汉,配打你?他骂了些什么?”
“他说,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他的,他不要!”
“哼!亏他有脸说出这句话!他一个男子汉,自己留个种也做不到呢!”
在这里自然的体能资源和人为的封建伦理开始了新旧道德的间接对话。财喜根据他的新道德观,确信秀生妻子“这么一个壮健的,做起工来比差不多的小伙子还强些的女人,实在没有理由忍受那病鬼的丈夫的打骂”。所以,当秀生妻子向他诉苦自己被丈夫打骂时,他显得十分恼怒,“自己留个种也做不到”的人,还“配打你?”而秀生之所以敢肆无忌惮地以暴力相加于他妻子,是因为旧道德对“夫权”、“父权”在家庭中至高无上权利和地位的维护。在封建道德里,一向以奉行“三纲五常”为美德,并视“一夫多妻”的婚姻制为伦常之道。违反此道者,则为乱伦。“夫为妻纲”,要求妻子唯丈夫之命是从,妻子没有思想、独立的人格和一切自由,而丈夫对妻子的思想行为乃至人身却有绝对的控制权。秀生明白妻子与财喜的关系,他狠心地打骂妻子就是为了维护自己“夫权”的权利和地位。
秀生妻子是个性情温顺的良家妇女,她身强体健,干起活来比差不多的小伙子还强。她尽心竭力照顾生病的丈夫,体贴入微,什么苦都吃,无怨无悔,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媳妇。但就是这样,还不足以换来她在家庭中最低限度的人身安全。面对病废丈夫的打骂,她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可谓忍辱负重,根本就没有什么地位平等可言,一切自由都消失在“三从四德”这精神镣铐之中。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的“五四”运动虽已过去十多年了,然而封建伦理道德对妇女从肉体到精神的压迫和摧残却未尝有何改变,难怪茅盾在一篇叫《问题是原封不动地搁着》的文章中,用极冷静但极愤懑的言词深入到这最需要革命的封建底层中去:“表面上看来,中国妇女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正像中国革命问题也似乎已经得到了解决一般。实际则不然。……‘革命以来中国何尝把旧的封建势力根本推翻?封建势力改换了面目依然存在。我们现在所见的一切好像有利于妇女的新法令,实也只有限于不损伤封建势力的范围以内的。诚然有了妇女协会,然而衙门一样的救济所一样的妇女协会何尝有损于封建势力的一分一毫呵!”③由此可见茅盾对妇女解放问题的关注。
如果说,以上只是新旧道德之间的一次间接“对话”,那么,小说的第四部分,作者借财喜所唱的一支活泼而俚俗的民间情歌刺激秀生,在对立中把自然情欲和人为制度的道德对话又推进了一步,展开了一场新旧道德间的直接“对话”。
歌词是这样的:
姐儿年纪十八九:/大奶奶,抖又抖,/大屁股,扭又扭;/早晨挑菜城里去,/亲丈夫,挂在扁担头。/五十里路打转回。/煞忙里,碰见野老公,——/羊棚口:/一把抱住摔筋斗。
这支有小丈夫的青年女子和野老公摔筋斗的情歌,显然是作者有意选择用来突出自然情欲和人为制度间对话这一基础的。财喜由于比别人早些打完了满满一船蕰草,提前离开港汊,高兴而哼起了他们村里人常唱的这支情歌,这原本是一种十分自然的开心、快乐的表现,殊不知秀生听了歌词内容,觉得这歌句句都是针对自己的,以为财喜是在故意嘲笑他,在向他示威。他虽然知道自己“是没有用的人”,不配享有“夫权”,但他还是决心以死殉权。为维护一个做丈夫的权利和尊严,他愤然提出严正的抗议:“财——喜”,“我,是没用的人,病块,做不动,可是,还有一口气,情愿饿死,不情愿做开眼乌龟!”是的,“做开眼乌龟”对于一个做丈夫的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耻辱,所以,他不惜以“情愿饿死”来捍卫他那摇摇欲坠的“夫权”。
在财喜看来,自己和秀生妻子的关系,至少不应是秀生妻子被责难的理由。有时他也后悔同秀生妻子的不轨行为,但他又觉得秀生妻子在这一行为上是没有过错的,表现出一种自然而朴素的新的认识。秀生妻子接受财喜的情爱,享受着“大自然赋予她做一个人的权利”,应该说与荡妇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在《水藻行》中,我们可以看到造成秀生老婆受虐除了她对丈夫“不贞”之外,还有秀生对她腹中的胎儿子嗣身份的个人私有权问题。这子嗣问题是封建家庭中造成父权至上的真正根因,也是秀生觉得自己向老婆肆虐不但“有理”而且“道德”的心理动因。④因而当财喜要求秀生“你不准再打你的老婆!这样一个女人,你还不称意?她肚子里有孩子,这是我们家的根呢……”时,秀生发疯了似的跳了起来,声音尖到变哑,“不用你管!……是我的老婆,打死了有我抵命!”矛盾进一步激化,秀生为维护他的“夫权”、“父权”,不惜第二次以命相拼,态度也显得更为坚决。
财喜觉得秀生妻子对秀生是很尽心的,除了多和一个男人睡过觉,什么也没有变,仍然是秀生的老婆。凡是她本份内的事,她都尽力做而且做得很好。他对子嗣私有权问题也不斤斤计较,表现出格外的宽宏大量,认为秀生妻子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也罢,是我的也罢,归根一句话……总是我们家的种啊!”秀生虽无能力履行“为人父者”的天然职责,但他仅凭旧道德赋予的“父权”,耍起对胎儿“生死予夺”的威风,在他看来,老婆肚子里的孩子是人家的,是个野种,自己有权处置他,狠心打骂妻子是他的权利,用不着人家来指手画脚。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熏染的结果。这里,茅盾形象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深层问题。
尽管财喜持有他自己的新道德观,但当他看到秀生“做开眼乌龟”表现出的痛苦和暴躁,他的心头就会涌出“疚悔”,对秀生的同情和怜悯也油然而生,这使他常常陷于复杂的爱情纠葛和思想矛盾之中。一方面,作为一个苦了大半辈子的光棍汉,对于不期而遇的爱情生活是那样的依恋,他虽然不想伤害秀生,但实际上已经伤害了秀生;另一方面,为摆脱自己所处的难堪处境,他曾打算离开这个家,但转念一想,自己走了,“田里地里的那些工作,秀生一个人干的了么?”“孩子是一朵花!秀生、秀生大娘也应该好好活着!”这样想着,他又改变了主意,不走了。他把自己的去与留和秀生、秀生妻子还有孩子的好好活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足见财喜的善良、朴实和正直。对爱情的追求和对弱小者的爱怜,在财喜心里两者实难统一。通过对财喜复杂内心世界的展示,让我们看到了财喜虽然一贫如洗,但他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追求,敢于以自己的新道德观向传统伦理道德进行挑战,为妇女遭受的不公平而呼号。在这个形象身上,散发着鲜明的时代气息。
为了情爱问题财喜与秀生虽然发生了难以互谅的争吵,但既已形成的至密关系又使他们同命相依,难以分离。因而,当财喜看到雪中的秀生萎缩在船上时,自然会把自己的破棉袄盖在他的身上;当秀生发病时,财喜自然就去城里药铺去为他买药;当乡长要硬逼着病在床上的秀生去筑路时,财喜自然能挺身而出,斥逐乡长。这就使我们感到,财喜与秀生妻子的关系,秀生与财喜的矛盾都是建立当时农村经济衰败而导致这个家庭生活水平低下,财喜无以自立,秀生又要倚重财喜的劳力等现实基础之上的,而且也暗示了它的社会历史的真正含义,使我们对畸形社会的畸形现象有了更为深切的认识。
读完小说,我们对财喜的“越轨”行动并没有产生厌恶之感,反而引起同情和赞许,原因就在人物的精神世界是高尚的。在新旧道德的“对话”中,财喜在男女爱情方面表现出的带有预见性的新道德观,反映了贫苦农民在精神领域的独特追求,给人们以发人深思的伦理思考。同时说明茅盾从对农民精神世界独特追求的深入开掘中,同样能发现触及社会本质的某些东西,从而对社会弊病作出合乎规律的剖析。
本文是2006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常规性课题《走出解读经典的误区:茅盾创作的多重文本意义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课题编号:06CGWX29YBM)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金华职业技术学院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
① 鲁迅:《〈中国杰作小说〉小引》,《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99页。
② 王嘉良:《茅盾小说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64页。
③ 茅盾:《问题是原封不动地搁着》,《妇女杂志》17卷特大号,1931年1月。
④ 李广德:《茅盾短篇小说〈水藻行〉研究述评》,《湖州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