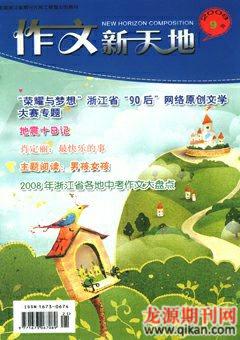谁把名字镌刻在心上
王不在
到某一天,当你惊讶地发现,你与曾经亲密的异性同学或朋友突然有了距离感,我要高兴地告诉你:亲爱的,你正在慢慢地长大。到那个时候,男孩与女孩之间开始有了各自的小秘密,你们互相排斥,又互相吸引,你们开始对一种叫作“爱情”的东西充满疑惑,头脑里还时不时产生一些莫名的冲动——我要说的是,这些都是正常的,是你们成长路途中不可或缺的一些体验。但是,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吗?是不是将他的名字深深地刻在自己的身体上,又或者是两个人在雪地里的一夜长途漫步?很显然,不是的。可能每个人对“爱”都有着自己不同的定义,但是,当我们没有真正读懂“爱”的时候,它只能是一个甜蜜的希望,一份朦胧的期待,一种小心翼翼的憧憬。
我知道,对你们来说,这期的话题会挑战某些“禁忌”,但我还是希望,这是一堂没有让你们失望的爱情课。
小女孩恋爱起来总喜欢做一些惊天动地的举动。想想好不容易恋爱了,换件新衣服、换个新发型怎么能铭记如此重大的爱情,总要来点更有纪念更有意义的事情吧。恋爱中的人都很大胆,所以选择文身是他们认为不错的纪念方式。我的文身店就开在这座城市的地铁商城里,位置有点儿偏,不过没关系,我的技术不错,通常客人想要文朵荷花我绝对不会文成牡丹。
店里来得最多的客人是恋爱中的小青年。这些家伙要文身我多半不劝,这能劝得住吗?只要一进门,她们就会说:“来吧。我要把他的名字刺在身上。”无论那个名字是讨厌的“刘小飞”还是俗气的“张红运”,她们都不介意。我只能说幸好,一个肤白貌美的姑娘没有左青龙右白虎实在是万幸。一个小时以后,吱吱作响的文身机文过身体后,她们就成了身上带着某个人名字的姑娘,谁也不能阻止她们享受这样一个疼痛而甜蜜的过程。
但总有后悔的吧。比如我面前这个文着“刘小飞”的女孩,她就后悔得肠子都青了。这属于我另外的一批客人,他们多半是一个人来或者是被曾经骂过她们重色轻友的姐妹带来。脆弱,怕疼,文身机还没有碰到身体,就“哎哟哎哟”地叫嚷,一点都不勇敢。文着“刘小飞”名字的姑娘来我店里,她希望我能把那该死的三个字袪除:“彻底去掉,我不要看见它们!”
她真是一个情绪化的女孩,三个月前还说:“请文大一点儿,这么小怎么看得见啊。”现在,她文在胸前的三个字希望我袪除。好吧,我用肉色再按照原来的轨迹再文了一次,会留下一片隐约的小影子,但这不算什么吧。
这个姑娘第三次来的时候,我怀疑我要叫她林振轩,是的,她最新的恋人叫林振轩,她希望我把这个名字文在刘小飞曾经的位置上。真够利索的,这么短的时间又恋爱了。我和她开玩笑:“下一次拜托找一个名字比较类似点的人恋爱吧,刘大飞或者是刘小力都行,你就不用那么疼痛了。”
文好了三个字,我告诉她,你这个位置的皮肤已经太脆弱了,最好以后不要来文身馆了。我的意思估计她也明白,我真心希望他们能永远爱下去。
她出门的时候,我希望以后永远不要再见到她。毕竟她是一个很率真也很漂亮的女孩,应该有个好归宿。可是我错了,一年以后,她还是来找我,希望我把这个名字去掉。
显然我是不应该去做这笔生意的,但我实在缠不过她的央求,何况,我还要靠这点钱来维持我的生活。可是等她脱下衣服,我只有满眼的触目惊心,她的那块皮肤已经彻底毁灭了,像一个丑陋的伤疤,上面的字也已经不再是“林振轩”,而变成“谢骥”。“我去年没有在南京,我去了厦门,在那里认识了他,又文了一次,但现在我们分开了。”
我尽量用轻松的语气告诉她,这块地方已经永远也不能恢复白皙完美了,而且这个名字也不能袪除。“为什么?为什么!我还想要下一次恋爱啊!”她抱着我的胳膊,稀里哗啦地大哭起来。
曾经为了学文身,和现在我考驾照一样,都要学该死的的理论知识,这些知识我到现在全都忘光了,不过有个小故事我一直都记在心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文身者大多数是女人,原因是为了纪念在战争中失去的爱人,她们一般文上小鸟、蝴蝶、红玫瑰,或是爱人的名字。她们永不消除,以此来纪念心中的真爱。
我是不是该告诉这个女孩,如果你的爱情不能像那些大兵的妻子一样忠贞不渝,那么,我宁愿你的爱情是轻微的,没有疼痛的。至少在每一次失恋过后,你交给下一次爱情的是完整的身体和完美的心。
(选自《女报·时尚》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