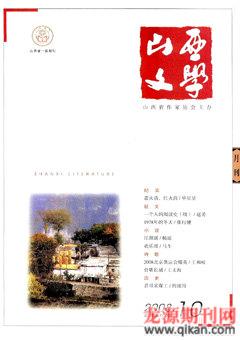小说的天空绚烂多彩(创作谈)
杨 遥
小说写了快十年,发了大概六七十篇,写创作谈是第一次。早于二十年前就开始读小说,几乎每天都不中断,但能记得起的小说,少得可怜,而且能说上来的基本是金庸、古龙的武侠和几个短篇。一些伟大的作品,能回忆起来的只是小说的一些细节和场景,故事完全说不上来,当时读这些小说,却一定是它们的故事和情节吸引了我。而且,在读《百年孤独》、《愤怒的葡萄》、《八月之光》、《雪国》这些伟大的经典作品时,感觉到的不是荒诞和陌生,而是一种亲切的认同感,觉得它们描写叙述的事情都发生在我们这个不足2000平方公里的中国内陆小县。
拿起笔的时候,我就希望自己能写出非同凡响的小说,可以避开以往阅读过的那些作品的影响,但知道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是一种宿命。我看到很多人的世界,惊讶而新奇,和我生活的世界如此不同,比和拉丁美洲的差别都大。这时“厚重”这个词压住了我,几乎每一个编辑和写字的人都告诉我,作品要厚重,这个词让我琢磨了好多年。我几乎一直生活在农村,性和生存是农民的主题,男人们找媳妇很少挑剔,只要女方不是奇丑,没有一些恶性遗传即可。有些条件不好的大龄男人,更是不加选择,瘸子、聋子、哑巴、小儿麻痹症患者等女人都是他们选择的对象。还有条件更次的,花钱从更偏远落后的四川、云贵山区买女人。还有的女人,因为丢了一百元钱,在街上号啕大哭,抑郁得患了癌症不治而亡。当我把这样的生活写下时,我不知道什么样的题材比它们更厚重?
然后,我又仔细读作品,巴别尔的简洁,胡安·鲁尔福的冷峻,沈从文的直接,莫言的绚烂狂欢,贾平凹的神秘与传统,马原的自信与结构,苏童的优雅精致,余华的严肃残酷,石舒清的从容飘逸,李锐、何顿对方言的得心应手,王朔充满真诚和上进的调侃都让我着迷,而他们是如此不同。蒋韵的《想像一个歌手》让我想到萧红的《呼兰河传》,尽管这两个小说毫无共同处,但都一样简单直接,一样可以看到作者惊人的才华。还有沈从文在《湘西散记》中,写水手们找竹楼上那些白脸长身的女人,竟看不出半点猥亵,让人窥视到一个作家心灵的纯洁。这时我觉得小说可以笨拙、飘逸、荒诞、简单、苦涩、尖锐、宽容、松散……几乎每一个形容词都可以用在小说头上,而且哪一种小说都可能写得有滋有味,这众多的可能性使得小说如此迷人,在文学消费疲软的时候,还有人喜欢它。这样的想法可能有些,但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备忘录》中对小说的多种可能性做了肯定。近日重读鲁迅,在鲁迅二十几篇短短的小说中,竟然一篇和一篇不一样,怎一个“厚重”了得?
《广场上的狐狸精》是一个荒诞不经的小说,写男人的欲望。《江湖谣》是受了博尔赫斯《恶棍列传》的影响,正在写的江湖系列中的一篇。感谢编辑的宽容,让这两个小说有面世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