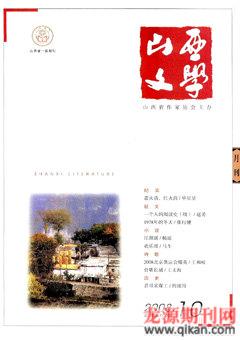广场上的狐狸精
杨 遥
自从古代成为一个词语,世界上的狐狸精就几乎没有了。我觉得狐狸精比大熊猫更宝贵,可是没有人提出要保护狐狸精,也没有人去做学问研究狐狸精是什么时候消失的,我总是臆想世界上或许还有一两个狐狸精,她们幻化为绝世美女,躲在某个地方,等待书生。我希望自己能成为那个幸运的书生,认识世界上最后一个狐狸精,哪怕她们把我精液吸尽、鲜血喝干。
黄昏时候,我去街上溜达。还没到广场,就远远看见围着一群人,我猜测是干什么的:跳街舞、扭秧歌、耍猴,或者是一个悲惨的乞丐,想了半天,也觉得不可能有什么新鲜玩意。这个城市待一天和一年一样,你要是待上一年,会觉得一万年都是这样。但我还是走过去,人多的地方总是会有意外的美女,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美女更吸引人。而且,这些美女中或许就有狐狸精。
到了跟前,人围得水泄不通,我特别想看到里边到底有啥,用劲往里挤,想象不出有多少年没这样和别人挤过了,担心会有脾气不好的粗野的家伙门板一样堵在我面前,骂我或打我。但后面有更大的力量推我,显然和我有一样想法的人不少。身边的那些女人、女孩和我身子贴得很紧,有些敏感部位不住地亲密接触。没有身后的力量,我没有勇气往里挤了。我想看看用劲推我的人是谁?但只能扭扭脖子,挤得根本动不了。我从身后闻到一股浓烈的酒味,一支灼热的烟头仿佛要触到我脸上。不知道谁在这么拥挤的地方抽烟,但在背后这种强大力量的推动下,终于挤进来了。
人群中间有一女的,刹那间我几乎要窒息了,你不知道她有多美!我也说不上来,我只觉得自己的心咚咚直跳,眼睛一下也不想离开。在一瞬间,我脑海中蹦出一个词“狐狸精”。而且,我发现周围的人像我一样,眼睛都贪婪地向这个女的身上望去。这么多人,动作如此一致,还是第一次见到。
女人坐在地上,伸出一双匀称、细致的腿,脚白得像太阳一样耀眼,我想自己要是能变做一只小小的蚂蚁,爬到女人脚上呆一秒钟,被她一脚踩死也知足了。但接下来看到的一句话让我目瞪口呆,女人前面的地上写着“谁愿意要我,带我回家”。
那一刻,我没有思想了。我觉得我的中部崛起,指挥我的左脚或者右脚就要迈出去。我那时的样子,像猪八戒见了女妖精。但鬼使神差的我没有迈出去,一种奇怪的声音吸引了我。我听到周围一大片急促的呼吸声,像大群的鱼困在缺氧的水中,那种声音集中到一起,有点惊心动魄。男人们一个个眼睛充血,嘴掉涎水,仿佛呆了一样。然后,又是整齐的一种声音,几乎每个人都嘘了一声,是女人稍稍动了一下脚指头。这时,我努力控制自己的思维,看到女人周围的男人们中邪一样一动不动,只是眼睛紧紧盯着女人细微的每一个举动,他们的头部动作和面部表情像被指挥棒统一指挥着。这些人中问有头发剃得精光,胳膊上纹着龙的小青年;也有赤裸着上半身,在胸脯和背上纹着弥勒佛和关公的壮汉;还有一身精英打扮的公司白领、一副领导模样的大腹便便的中年人、穿着破破烂烂的民工、拿着扫帚的清洁工……
我又仔细看了一下女人前面地上的字,“谁愿意要我,带我回家!”没错,是这几个字。女人双目微闭,似乎在养神,又似乎在期待,她的表情从容、安静,不像个色情狂,一本正经的像做这个事情天经地义。
下滑的太阳光线掠过一幢高楼,在人群中间投下一片阴影,女人坐在阴影中,轻轻耸了一下鼻子,人群又是一阵骚动。光线从高楼上移走,女人的身子慢慢亮了,然后站在她背面的人群也慢慢亮了,仿佛她是光一样。
刚才看到的几个纹龙的小青年互相推搡着,眼睛里是兴奋的光。看到他们的表情,我心里有些急,可是怎样也迈不出步子,这么多人,众目睽睽,即使真的可以带她回家,也……
大多数的人可能和我的想法一样,大家心里想,但不敢,又不甘心就这样走了。背后有两个人小声议论:“这么漂亮一个女的,比电影演员都漂亮,让别人带回家,一定是有阴谋,或者她是个神经病。”“是啊,一定有问题。”两个人议论,但并不走。他们鼻子、嘴里急促的热气和眼睛灼热的光更加强烈。
太阳落山,光渐渐暗下来,女人好长时间没有动静,像一尊雕塑。在微光下,能看到她长长的睫毛在大理石一样洁白的脸上投下的剪影。
人群越围越大,已经扩展到马路上,过往的车辆都被堵住,但还是有远处的人听到消息打车过来,过来的人已经几乎不可能挤进来,但人们还是不住地赶来。那天估计大半个城市的人都赶到这儿,马路占满后,人群又挤到附近小巷里。有的人过来时,从自己住的地方出来打车,怎样也走不到广场,转了个圈,又转到自己门口。然后他像亲眼目睹过一样,给人们讲里面女人的故事。
后来,天真的黑了。夜色驱赶走一大批人,还有些人肚子饿了,也有些要回去做饭,给孩子喂奶,与情人约会……
广场上的人慢慢散了,月亮出来,清冽的光洁白、柔和,在轻轻的晚风下,使夜晚增加了不少妩媚。还在围观着的人们从周围卖小吃的那儿买来东西,广场上响起一大片吃东西的声音,这种声音瘟疫一样传染,大概有两个多小时,一直有人在叽叽喳喳吃东西。女人在中间安静地坐着,有时会轻微地动一下某个部位,仿佛不食人间烟火。围观的人群大概已经审美疲劳,不像刚才那样反响大。
夜开始加深,蚊子之类的虫子一群一群飞来,在头顶雾一样不散。有人开始打呵欠,然后越来越多的呵欠打起来。又过了好长时间,月亮不见了,天色墨黑,几盏昏暗的路灯没有使东西变得亮起来,而是增加了一丝诡异的色彩。一滴雨掉在胳膊上,大而清脆。黑云越聚越多,感觉天比地要厚许多。在大片的雨降落下来之前,走了一大群人。他们边走边打呵欠,还不断返脸看一下广场中心。这个时候,女子其实已经看不见了,到处都是浓重的黑,女子待的地方只是更黑一点,只能看到一团黑糊糊的影子。这个时候,我往前走了一步,觉得时机成熟了,那些无聊的人们终于没有耐心了,我要带这个美丽的女人回家。可是,在我往中心走的时候,听到还有几个人也往前走,其中一个走的脚步声一顿一顿,像是一个瘸子。不知道谁和我一样执著、专心?这样想的时候,一道闪电划破天空,在雷声还没有响起来前,我看到还有其他三个人没有回。其中一个如我听到的那样,是一个瘸子,满脸络腮胡子,看不出实际年龄;一个穿着制服,像公安,也像保安;一个是神情猥琐、身体壮硕的乞丐。他们和我一样,没有想到还有人没回。
雷声响了,大地颤了一下,第二道闪电发出耀眼的光。那个壮硕的乞丐往前走了一步,我的心咚一下要跳出来,也跟着往前走一步,制服、瘸子也往前走了一步。乞丐忽然毫无征兆地把手中拿着的饮料瓶朝瘸子头上扔去,然后趁瘸子没有反应过来,一脚踹去。战争终于爆发了。我朝制服看去,希望他能制止,但内心更希望那两个人拼个两败俱伤。制服面无表情地朝我走来,他的手插在兜里,鼓鼓囊囊的,像拿着什么凶器。我的心
凛了一下,抓起一块人们坐过的砖头。雨突然大了,像千军万马在奔腾,衣服马上被浇湿,眼睛根本睁不开。我胡乱挥舞着手中的砖头,希望雨下的再大点,把瘸子淋走,把乞丐淋走,把制服淋走。又一道闪电,雨仿佛顿了一下,瘸子已经和乞丐抱在一起在地上翻滚。制服并没有走过来,而是用手捂在脸上,雨落在他的头上顺着伸直的手和胳膊流下来,瀑布一样。我愣了一下,举着砖头朝他奔去。
水像从地上冒出来,四面高处的水都向广场流过来。鞋浸在水里,水顺着腿迅速往上涨。天越压越低,仿佛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挤碎。雨不是在下,而像我们进入竖起来的河流里。闪电像频频爆炸的电灯泡。
瘸子和乞丐从水里站起来,手拉着手朝广场角上的亭子跑去。制服瞧着我,那眼神是想去躲雨,又怕我把女人带走。这时一道闪电击在附近的一个大烟囱上,半截烟囱掉下来,发出惊天动地的声音。我望了一下制服,他的眼光在鼓励我,也在邀请我。我又望了一下女人,她那个地方仿佛有一层奇异的光。今天这雨下得真是怪异,什么时候这个地方下过这么大的雨,刚才天还那么晴朗。不知道谁先伸出手,我和制服已经走到一起,女人的身子浸在水里,但也好像浮在水面上。水已经淹到我们的膝盖,我们根本走不快。一道一道的雷电跟在我们后面,世界仿佛到了末日,我们好像永远也走不到那个亭子。
这时,不知道从哪儿漂来一根巨木,我们两人扶着木头朝亭子走去,瘸子和乞丐居然也没有到,好像在半路等我们一样,我们四个一起抓住木头。雷忽然停了,闪电也没有了,刚开始我们觉得一定有更大的雷电在积蓄,提心吊胆地等着,但等了好长时间,什么也没有等到。四周漆黑一片,只有哗哗的水声。我们看不到亭子,只好凭印象往前走,但我们四人的印象根本不一致,走了几步,又发生争执。我最先放开巨木,朝印象中的亭子走去,此时,不像在广场上走路,更像在水中游泳。摸了好长时间,我的膝盖碰到了台阶,心里一喜,到了。这时我奇迹般地发现自己能模模糊糊看到周围的东西了,确实是亭子,水已经没了它一半。然后我看到其他三个人从三个方向爬上亭子,一个比一个狼狈。我们四人站在一起,浑身上下都湿透了,我和瘸子的鞋也丢了。而且我们都感觉冷,尽管是在夏天,都冷得瑟瑟发抖。我们不约而同地挤在一起。
雨停了,云朵大块大块朝周围飞开,星星出来了,冰冷;月亮出来了,像一张死人的脸。我们都朝女人方向望去,什么也看不到,四周都是水,哗哗地流淌着。风使我们更冷了,我们四个紧紧抱在一起,为了取暖,用劲跳着,边跳边大叫。
广场上的水越来越少,天空开始发白。女人待的地方出现些模糊的东西。我们几乎又是不约而同地感觉到,朝那个方向走去,但大家心里都紧张,走起路来小心翼翼,仿佛地上到处都是地雷。
一辆车轮的声音忽然出现在耳边,一个拾垃圾的老头推着一辆独轮车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他头发霜一样白,走起路来十分敏捷,像一只猴子。我的心猛烈跳动起来,步子稍微快了点。老头推着车子走得飞快,几乎眨眼间就到了女人那儿,他停下,把地上的东西抱起来放车上,然后又快速离开。我没有看清楚他抱起来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像一个女人,像一堆衣服,像一些皮毛,还像一块泡沫塑料。
我想看看他到底拿走什么,追着他的背影跑起来。路过女人待过的那块地方,遗憾地什么也没有看到,地上干干净净,一点痕迹也没有。老头推着车拐进一条小巷,我追进去,听见后面也有几个声音,知道那三个人也追上来了。我加快速度,仿佛怕那三个人追上我。老头的速度想象不到的快,我离他的背影越来越远,这时,制服赶上来了,乞丐超过我了。我回头看,瘸子正气喘吁吁地跑着,踩在一块瓜皮上,摔倒了。我加紧速度,继续奔跑,在前面一个拐弯处,忽然看见乞丐正站在一家卖早点的铺子前,手里拿着根油条在吃。我的肚子咕咕叫了起来,但我继续奔跑,我呼吸急促,像狗一样吐着舌头,心仿佛要跳出来:又拐了几个弯,老头一点也看不到了,然后我发现自己站在大街上的一个十字路口,那个制服站在路中心的指挥台上,一本正经地指挥着交通,我认真看了一下,就是昨天那个制服。我又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仿佛不是昨天那个制服。
他身子笔挺、动作标准,来往的车辆在他的指挥下井然有序。新的一天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