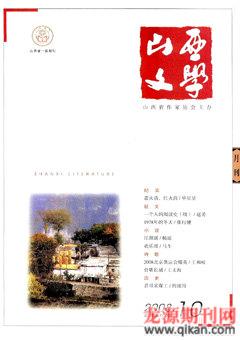江湖谣
杨 遥
青春年少的时候,我们都向往江湖上的事情。
高大的唐槐上那口古钟一响,下课了。我们争先恐后地奔向槐树下,争抢槐荚。把它捣碎,掺上沥青,捏成小球,晒干坚硬如铁,是最好的暗器。我不记得怎样转到了初中班教室门前,有个学生站在室外的窗户边,他正在流鼻血。一滴一滴的血掉在青色的窗砖上,砖的颜色变成铁锈色。还有一些掉在地上的黄土中,一小块土的颜色变得很深,却看不出是血。那个夏天一下酷热起来。
“血,你流鼻血了?”
一张丑陋的脸转向我,一大滴血正像一条红色的虫子从他鼻孔里钻出来。他的两只眼睛一大一小,小的那个几乎只是一条缝。我觉得他的这只眼睛一定瞎了,心中一凛,一股凉意爬上我的脊背。他鼻子上的那只红虫子掉下来了,砸在面前的浮土中,像一朵水花溅在平静的水面上,又一块黄土的颜色变深。他的那只大眼睛里蓄满泪水。
“血,你流鼻血了!”
他从窗台上摊开的作业本上随便撕下一张纸,在鼻子上擦了擦,整个脸一下变成花的,血还在流。他又撕了一张纸,弄下一条搓成绳,塞鼻孔里。他朝我笑了笑,我感觉很恐怖,赶紧逃离这个窗口。
第二天,我就打听到他叫钟飞。一个比我年长的同学是他朋友,晚上领我去他家。那晚的月亮很大很圆。钟飞家住在一个非常大的旧院里,据说以前是一家地主的,土改的时候分给很多人家。漆黑的大门已经破败不堪,上面的油漆皱起皮,门上满是裂缝。照壁上的砖雕也残破不全,一些掉在地上和废弃的砖瓦堆在一起。原本整齐的院子东家一个猪圈,西家拴一条狗,院子里到处是鸡屎。最里边的两间屋子是钟飞家,外边看起来还算高大,进入里面却像钻进了地洞。屋子里黑糊糊的,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电灯,点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外边的一间屋子四角堆满了杂物,在中间留下一条狭窄的过道,穿过过道进了里间,亮了些。顶棚和四壁黑糊糊的满是污垢。炕周围的墙壁上有几只壁橱,门紧闭着。我想打开这些门,里面一定藏着暗道,但一晚上,也没有机会看到壁橱打开。
钟飞对我们的到来感到很高兴,用一个大茶缸给我们倒水,茶缸上积满了水垢。我不想喝热水,揭开水瓮,舀起一瓢凉水,瓢是用铜做的,喝水的时候舌头触到瓢上一层薄薄的水苔,滑溜溜的。
我问钟飞:“你昨天鼻血是怎么回事?”我提的问题含糊不清,但钟飞明白了我的意思。他说:“老师冤枉我,让我站院子里把课文抄一遍。流鼻血了,我不想擦,我看能流到什么时候?”我对钟飞隐隐约约有了些崇拜。
那天晚上,我们在钟飞家坐了好长时间,一直没有见到他的父母。
钟飞家很快成了我们的乐园,他非常喜欢别人来,他的父母经常不在家。
他父亲的眼睛和他一样,一只眯着,人们叫他“瞎老三”。他长得黄瘦,唯一的爱好就是下棋。夏天,他扛一柄锄头去地里,走到街头看见有人下棋,就走不动了,把锄头立在那儿,会一直看完。假如有人让他替一把,他上去就再也不下来了,别人骂他或者推他也没用,他尿急了也不下,会一直憋着,憋不住了,尿就随着他的裤管流了下来,人们发现,骂他一声,你这个驴!他也不恼,换个地方继续下。有一次和村里的一个光棍一直下了一天一夜,谁也没有挪地方,没有吃饭,等到别人去了光棍家里,一股臭味,两个人胡子老长,手指发黄,目光呆滞。那人在他们每人肩膀上拍了一巴掌。他们像才醒过来似的,想往起站,但都腿麻得站不起来。
不久,瞎老三做了光棍。他的老婆喝农药死了。那是一个傍晚,有好多蝙蝠在天上飞来飞去。我们脱了鞋扔天上,据说蝙蝠会钻进去,但没有一只蝙蝠钻进去,我们仍然乐此不疲。钟飞的母亲从外边回来,刚走到外边院子,就一屁股坐地下,号啕大哭起来。瞎老三从外边回来,揪着他老婆的头发往回拖,边拖边说:“丢了钱还哭,这么大人还丢钱,丢不丢人?”女人护着头发说:“丢钱不丢人,丢人才丢人。”对这饶舌的话我们都听不懂,只是觉得丢钱是一件很大的事,我们谁丢了钱,回家都会挨打的。那天瞎老三特别凶恶,他老婆哭得十分伤心。那个傍晚恐怖极了,我们都不吭声,好多好多的蝙蝠在头顶上飞舞,夜在它们的飞翔中一点一点黑下去。出来很多大人劝他们,平时感觉很窝囊的瞎老三被人越劝越厉害,他大声说:“这么大人还丢钱?丢了钱还胡说八道。”女人的哭声更大,更委屈,说:“不能活了。”“不能活了你去死,孙子才拦你。”两人越闹越激烈,劝架的人都摇摇头,走开。我找钟飞,钟飞不见了。这时那些黑色的蝙蝠仿佛也消失在夜色中了,各家呼喊吃饭的声音响了起来。我吃完饭和母亲讲钟飞家打架的事,父亲一脸严肃地说:“小孩子不要乱讲别人家的事。”晚上睡着,我还梦见他们一直在吵架。
第二天,刚起来,就听见人们说瞎老三的老婆喝上农药死了。我饭也没有吃,跑向钟飞家里。远远看见他们院子里围着一大群人,知道肯定出事了。到了近前,听见嘶哑而伤心的哭泣声。然后看见瞎老三跪在地上,边哭边不停地用头碰前面的地,地上已被砸出一个泥坑,他头上满是土。钟飞的母亲躺在地上,脸色发青,嘴里好像还有白沫子。我感觉害怕,想知道钟飞现在做什么。进了他们屋子,见钟飞在收拾东西,正把铺盖卷起来往一个尼龙袋子里放,铺盖卷得有些大,他让我帮忙。我问:“你要干什么?”“离开这个地方。”我觉得惊诧极了,但十分愿意帮钟飞这个忙,那个时候好像一直希望身边出些新奇的事情。我只是问:“你不上学了?”“不上了,我要去挣钱。”钟飞的眼睛里有泪水,但他不往出哭。
钟飞的母亲下葬以后,关于她的死还有些说法。我们小孩子都以为是她丢了钱,一笔很大的钱,自己心疼内疚,丈夫又责怪,想不开死的。但大人们的话隐隐约约提到是因为另一个女人,瞎老三和那个女人好了,老婆气不过死了。
那个女人是邻村的,我们谁都认识。她叫“二分钱”,我们经常跟在她后面丢土块。她本来不傻,模样还俊俏。曾有个儿子,儿子九岁的时候,不知怎么跑到猪圈里去玩,正好母猪刚下了崽,护崽,把他咬着了,大人们听到哭喊声赶去的时候,他已经面目全非,身上头上都是伤。送到医院,伤看好的时候,却发觉人傻了。一趁人不注意,就到街上乱跑,他不穿衣服,而且奇怪的是他走路还闭着眼睛。他的母亲经常跟着他,想把他弄回去很难。有一次,他跑到铁路上,被火车撞死了。他死了之后,好像他的魂附到了他母亲身上。女人傻了,也经常不穿衣服跑出来,闭着眼睛走路。她丈夫嫌丢人,扔下她走了。谁给她点钱或吃的,她就和谁好。没想到瞎老三和她好了。
大人们的话肯定没错,因为不久,瞎老三就搬到二分钱家去住。人们经常见到瞎老三跟在二分钱屁股后面,手里拿着衣服。人们喊:“老三,下盘棋吧?”瞎老三回答,“顾不上啊。”瞎老三把精力都耗在二分钱身上,怕她不穿衣服跑出来,怕她出事,怕男人们偷她。
家里只剩下钟飞一个人,他有两个姐姐早出
嫁了。所以他打消了出走的念头,他变得特别勤快。除了和我们玩之外,还学习各种技术。修自行车、裱刷、油漆、木匠、泥匠等等,他几乎对所有的技术活都感兴趣,他在我们眼中成了一个能人。但他不用这些来挣钱,他也不给别人当学徒,他只是因为喜欢这些。他的学费和伙食,两个姐姐给他解决。
一次,没有别人的时候,我让钟飞打开墙上的壁橱让我瞧瞧。开始,钟飞怎样也不答应。我一直磨,他就是不答应。我上了炕自己去开,他一把把我拖下来,我的膝盖在炕沿上碰了一下,生疼生疼。我想发火,看到钟飞先发火了,他没有说话,那只独眼像火在烧。我觉得很没劲,拉开门,使劲摔了一下走了。从那天开始,我见了钟飞远远就躲开,躲不开也不和他说话。一天放学后,钟飞拦住我,说:“你想不想去看了?”我觉得我好像听错了,看钟飞,他很认真。我抵制不住内心的好奇,问:“你真的让我看?”钟飞点了点头。我们在去他家的路上,钟飞突然说:“我送你一把链子枪吧?”我警觉地看着他说:“你不想让我去看,我就不去了。”我装作要走的样子。钟飞拉住我,叹了口气说:“想看就看吧,可那有什么好看的,里面都是烂东西,一直没人收拾,我才不想让你看。”我不信钟飞的鬼话,一定要看。其实链子枪我也是想要的,这个玩意儿大概是小时候最好的一件玩具了。它是用铁丝窝好枪架,用自行车链条做枪膛,然后再镶一个敲掉底火的子弹壳。玩的时候,装一根火柴棍,一扣扳机,皮筋弹回去,会把火柴棍射出去,还有响声和硝烟。
到了钟飞家,他说:“你真的要看?”我说:“一定要看。”他说:“你可不要后悔。”我说:“决不后悔。”钟飞打开了一个壁橱,一股霉味从里边散发出来,壁橱并不深,没有我想像中的暗道,里面放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四壁也是黑糊糊的,颜色比外边有些浅。钟飞打开一个又打开一个,每个里面都是些烂东西和灰尘的味道,令人窒息。我失望极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古代的人做壁橱的时候不弄个暗道。
不久,钟飞就把这些壁橱里的东西都扔了,因为以前他也很少打开,没注意里面是些什么东西。然后,钟飞开始了对房子的改造,他要把房子隔成两间,一间腾出来出租。我们觉得钟飞的想法是个好主意,都来帮忙。钟飞先在里间屋子的墙上开了个门,这个门是他自己做的。他从木匠那儿借来工具,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些木料,每天早上和放学后开工。几天后,一个像模像样的门做好了,镶上玻璃,谁看了都觉得不错。接着,钟飞要在两间屋子中间砌一堵墙。我们帮助搬东西,和泥。又是几天后,一堵墙在屋子中间出现了,干了之后又抹上白灰,后来刷上墙粉,一堵漂亮的墙在他手中诞生了。我们都对他十分佩服,家里的大人听说这些活都是钟飞干的,也十分吃惊。村里的好多大人一个人也干不了这么多活。
房子改造好后,钟飞开始招徕房客。他的第一个房客是一个个子很小的外地人,我们称他为神秘人。他五十多岁,长一个扁扁的鼻子,一个人出来租房。他几乎很少说话,也很少出门,更奇怪的是什么活儿也不干。每隔上一个月,就有一个女人来找他。他说是他妻子。他们两人在一起也很少说话,女人来住上几天就走了,下个月再来。人们都觉得他很奇怪,大人们猜测他可能在家乡出了事,跑出来躲。钟飞觉得这个人很不好玩,过了半年就要撵他走。这个人还想住,主动给他加房钱,但钟飞说什么也不留他了,这个可怜的人只好拿着他不多的行李去别处租房。
钟飞的第二个房客是河北人,第一个是外乡,第二个却是外省了。我们兴奋地想,钟飞的第三个房客似乎会是外国人。这次房客是夫妻俩,年龄也不小,却是跑江湖的。男的姓张,人们叫他老张。他们带着一些竹子做的圈圈,赶各处的庙会。这样的人我们以前经常在庙会上见,找一块地方,用绳子围起来,里面摆些玩具或饮料。谁想玩,花钱拿几个圈圈,在绳子外面瞄准了扔套里面的东西,套中啥拿啥,套不中就让摊主挣钱了。想不到这样神秘的人住到了钟飞家里,我们很兴奋。此后,去了钟飞家,我们就去老张那边。老张夫妻俩都是很和蔼的人,给我们讲些外面见识到的事情。但他们不经常在家里,哪里有庙会就往哪里赶。他们不在的时候,我们躺在钟飞家炕上,根据各自的经验和想像,讲江湖上的事情。钟飞说他上完初中就不上了,他也要去闯江湖,做老张那样的人。我们都很羡慕。有人说:“再找个像老张老婆那样的女人,一起闯江湖,更过瘾。”钟飞不说话,但大家更兴奋了,隐隐觉得老婆很重要。
钟飞上完初中果然不上学了。瞎老三的心每天都花在二分钱身上,不管他。他的两个姐姐也不硬管他。再说,在村里,上完初中辍学的人太多了,一起玩的人中间还有几个。
钟飞一不上学,马上就想怎样挣钱。比起他的手艺,他显然更钟情江湖生活。他拜老张为师,学习江湖上的规矩。我们见了他,他经常炫耀自己知道的江湖上的事情。而且,他大概也打算从套圈圈开始,因为他买回些竹竿,做圈圈。老张是一个慷慨的人,把自己的手艺和技术传授给了他。钟飞做好圈圈后,遇到下一个庙会,就跟着老张出发了。
日子飞快,青春的成长仿佛是一日间的事情。我上完高中,上了大学,那些不上学的同学好多已经结了婚,我假期回来的时候,见到他们领着自己漂亮或不漂亮的妻子一副幸福的样子。还有的怀里已经抱上孩子,小小的婴儿在爸爸怀里怎么看都像一个玩具。钟飞还在跑江湖,偶尔能见到他,他的脸上过早地写满了沧桑,仿佛时光从他身上硬硬抽去一截。一次,他非要请我喝酒,拗不过他的好意,我答应了。原以为在家里随便吃点,没想到他竟领我去一家小饭店。点菜的时候,我要了最便宜的煮花生米和炒豆腐,他说:“怎么能没有肉呢?”非让我点一个,我不点。他说:“我做主了。”点了一盘红烧肉。
“还在套圈圈?”
“嗯。以后不套了,挣不了钱。”
“老张他们夫妻俩不是一直干这个也挺好吗?”
“他们老了,用钱不多了。我要结婚,要养活孩子。”钟飞的情绪有些消沉。
我劝他少喝些,但他拿起杯子来就干。
他说:“你能和我一起吃饭是看得起我,我干。”
我觉得我们之间有了一道鸿沟,疏远了。
钟飞说:“你大概有女朋友了吧?”
我摇摇头,他不信。他说:“咱们同学差不多都结婚了,只剩下我。”
我说:“也不只剩下你,还有虎子。再说,别人结婚都是他家里给他娶的,我看咱们同学娶媳妇大概只有你能凭自己娶上。”
说到这里,钟飞有些得意。他说:“咱们不说虎子,但我只能靠自己。你说是不是?”
我点了点头。虎子是我们的另一个同学,是一个奇怪的人,一直什么也不干,只靠父母。平时特别爱和人抬杠,先是认为1999年地球会大爆炸,现在又认为将要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一瓶酒很快喝完了。钟飞还要要,我拦住了。我大概只喝了三两多,但头晕得厉害。我抢着去结账,钟飞拦住我,说啥也不让我结。他掏出一把
钱,几乎都是一块的,中间夹着一张五十的,一看就是假钱。因为前段时间我拿这样的一张钱买东西,被卖东西的发现,说这是标准的台湾版假币,当时窘得我不知道脸往哪儿搁。钟飞拦住我,拿着那些零钞和假钱去结账,我觉得很难受。我示意老板收下他的假钱。老板是一个聪明的人,也认识我们俩,收下他的假钱,还把零头找回来。送钟飞同的路上,他很得意,他说:“你知道吗?我刚才花的是一张假钱,老板竟然没有发现,还找了我钱。我也不知道怎样就收了一张狗日的假钱,他妈的,套一次圈圈才一块钱,他给了我五十的假钱,我找了他四十九啊!”
把钟飞送到家里。多少年过去,他们这个院子有的人家拆了旧的房子盖成新的,还有的在自己家院子口做了个小门,单个独立出来。我想起从前我们和钟飞一起做门、砌墙的事情,那时我们都以为自己会干一番大事业,尤其是钟飞,觉得他将来一定很了不起。院子中的那些猪圈和鸡舍废弃了,但并没有拆掉,人们还用以前的遗迹占着公共的空地。上面满是碎石和土块,长满了杂草。有一处有人种上了玉米,倒也长得郁郁葱葱。钟飞家的房子没有动,但明显感觉老了,不知道是自己长大见了些高楼大厦,还是周围房子的比较,觉得他的这两间屋子矮小极了。在门口我看到老张,他也老了,中间的头发基本掉光了。和他打了个招呼,他并没有认出我,但看到钟飞喝多了,他也跟过来。钟飞做的那个门变形了,歪歪扭扭的,有一块玻璃碎了,没有换,用透明胶布粘着,像人脸上长了一道恐怖的伤疤。他的屋子很黑,拉着灯,却很昏暗。墙上的壁橱、黑色的墙壁和屋顶使时光倒流。我想起第一次到他家,水瓮里铜瓢上的那薄薄的水苔。我给他倒水,暖壶是空的。老张去隔壁拿。钟飞呼呼睡着了,我非常想打开壁橱再看看,到底有没有暗道,但没有动手。老张拿水过来,桌子上有一个空罐头瓶,我用它给钟飞倒满水。钟飞在炕上痛苦地呻吟,我让老张照看他,说明天再过来。
第二天,我买了些水果去看钟飞,他为自己前一天喝多感觉有些害羞,不多说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想起以前我们整天躺在他这炕上,天南地北胡扯,觉得现在有些尴尬。没有坐多长时间,我要走,钟飞客气地送出来,把我一直送出他们这个大大的院子。
毕业、找工作、失恋,再辗转颠簸,日子像上紧发条一样,由不得自己停下来。只有年底的时候回次家。钟飞的消息一直不大好,他现在似乎什么都做,除了赶庙会,还做建筑小工、装煤、卖年画等,但是一直没有娶上媳妇。他的丑陋是一个原因,但是比他更加丑陋的人也有娶上的。主要是他没有钱,他尽管勤快,但做的都是卑微的活儿。还有他的那个瞎老三父亲,这么多年了,一直呵护着二分钱,但他没有收入来源,两人的生活都靠子女资助,姐姐们的孩子已经长大,要照顾自己的家庭,担子大半落在钟飞身上。钟飞没有怨言地扛起这个担子,还担上了父亲的坏名声。
我的奔波也没有效果,家里出了变故,需要我照顾,便回到家乡当了老师,这使我想起鲁迅先生《在酒楼》上和魏连殳的那段对话,像一只苍蝇,嗡嗡飞了半天,又转回来。在现实面前,我慢慢妥协。我感觉像一条自以为是的鱼,被海浪抛到沙滩上,风吹日晒鸟虫叮咬,渐渐变成一具骨架。更糟糕的是和周围生活格格不入,我教的小学年级里,居然有我同学的孩子。
很快,我和钟飞又走到一起。我理解了钟飞找不上老婆的那种焦虑。我们诅咒那些浅薄无知的女人。小时候听故事,勤劳、勇敢的人往往能娶上公主。钟飞勤劳、手巧、憨厚、孝顺父母,而且他在给我讲的闯江湖的故事中,也是勇敢的主角,可是就是没有女人愿意嫁给他。
钟飞的生活目标其实很简单,娶个媳妇,好好活着。不像我有许多乱七八糟的想法。但是除了一些需要匹配的条件外,钱是最重要的一关。钟飞手中的积蓄离昂贵的彩礼还有一大段距离,他的父亲还是个无底洞。但钟飞从来没有绝望过,他是我见过的人中最勤劳、最能吃苦的一个。
每年农历三月十八,村里举办庙会,纪念晋国大夫羊舌。紧邻的一个大镇的也是这个时间。以前我有种错觉,觉得世界上的庙会大概都是农历三月十八。和钟飞在一起,才知道各地的庙会大不相同,他手中有一个邻近三省的庙会时间表,即内蒙、陕西、河北,这些各地的庙会时间大不相同,但几乎有大半连缀在一起,设计好的话,可以赶完一个去另一个,一年能赶一百多天。钟飞在家里除了自己的地,还又承包了十亩别人的。每年天气暖和的时候,庙会就开始了,耕种也开始了。钟飞白天赶庙会,早上晚上种地。地种好之后,托他父亲帮忙照看一下,锄锄草,他开始了一年的庙会生涯。
有一年暑假,他在河北的一个小镇赶庙会,我闲着没事,坐火车去找他。我是午后抵达的。那是山区的一个镇子,好像有铁矿,也算繁华。到了那个镇上,却没有多少新奇的感觉。一条主要街道上,挤满了人,卖的东西都是极平常的,显眼的是几个穿着藏服卖药的人。镇子外边有一条干涸的小河,在河边找到钟飞。这次他套的是镜框。还是拉着绳子围起来,里面摆满各种样子的镜框。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些漂亮的镜框,形状各异,造型很独特,工艺品一样;质地有铜的、木料的、树脂的、塑料的;更主要的是每个镜框里都镶嵌着一张美丽的图片,有夺人心魄的美女、娇憨可爱的宝宝、幸福的恋人、高档的小车等,在这荒凉的河滩上,显得有些怪异而有趣。套的人并不多,钟飞也没有多大精神,他的注意力好像被附近一个跳舞的吸引住了。那边搭着高高的台子,台上有一个穿得很少的女人扭来扭去,做出各种诱惑人的动作,喇叭在高声说:“快来,快来,快入场,表演马上就要开始了。”走到跟前,钟飞才看见我。他很高兴,仰起脸,站起来,用劲地和我握手。他的脸上满是灰尘,皮肤很粗,皱纹也明显,我心里有些酸。
钟飞说:“住处给你找好了,吃饭了吗?”我说:“不饿。”钟飞说:“那好,我也没吃,咱们一会儿一起吃。”说完他又盯着对面的舞女看。我问:“生意怎样啊?”“一般。”那个女的扭了一会儿,换了一个出来,喇叭还是重复着刚才那几句话,大概表演还没有开始。
我拿起近处的一个镜框,图片是荡秋千的少女,穿着白色的裙子,天真无邪,裙摆微微飘起来,仿佛要飞。我问:“怎么不找个热闹的地方?”“地盘费贵。”又过了一会儿,来了一大一小两个孩子,每人要套一元钱的,钟飞给他们每人数了十个圈圈。很快他们就套完了,还想套,但大的没钱了,他在小的耳边嘀咕了一会儿,小的不情愿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元钱。钟飞又给了大的十个圈圈,他扔出八个,仍然什么也没有套着。小的向大的要一个,大的推了他一把,说:“我来,我品住了。”小的说:“我要那个。”他指着一个小狗图案的说。大的扔出最后两个圈圈,没有套住。小的几乎要哭了,大的说:“我本来要套汽车的,是你说要套小狗,套汽车我绝对没问题。”又说:“我们一会儿再来,你等着。”
套圈圈的人不多,零星来几个,套一两元钱
的就走了,有一个还套中了一个镜框。钟飞说:“游戏也在进步啊,刚开始弄这个,想套的人得排队。现在有了跳床、旋转木马、过山车、飞机、歌舞,玩这个的少了。”说完,他又看了一眼那边的歌舞。表演大概开始了,声音很吵,外面跳舞的女的也回去了。钟飞的神情有些黯然。
钟飞出去买了几根油条,我没有饿的感觉,勉强吃了半根。钟飞的注意力一直在歌舞那边。我说:“你想看的话过去看看,我给你看摊子。”钟飞说:“要看咱们等会儿完的时候一起去看吧?”我说:“我不爱看这个。”钟飞说:“要去一起去,我一个人绝对不去。”
夏天的午后异常漫长,我没有想到钟飞做的活儿是这样无趣。只有有人过来玩的时候我们才有点精神,但玩的人一直不多,大部分时间是在等待。周围很嘈杂,这种热闹更显示出钟飞摊子的冷清。过了一会儿,我厌倦了,又去镇上转了一圈,没有新的发现。庙场院有戏,大概是河北梆子,看的人稀啦啦的,坐着看的只有二三十个,大多是老人。旁边站着些年轻的男女,自顾自说话,并不关心台子上唱什么。我对戏也没有兴趣,转了一圈出来,买了两瓶矿泉水。回去的时候,钟飞的生意还是很冷清。一会儿功夫,我发现那些漂亮的镜框上面竞满是灰尘,像尘封了多少年。那处的歌舞大概表演完了,又有女的出来站在外面高高的台子上扭,衣服还是和以前一样的少。钟飞正扭头看。递了一瓶水给他,我走近台子,远处看似很妖艳的女子,到了近前,脸上泛着油光和汗水,微笑和舞蹈的动作机械得像木偶,眼睛里没有喜悦或悲哀,像木头刻的一样。我回去,让钟飞过去看,钟飞迟疑了一下,摇摇头。我找出块布子,擦那些镜框。钟飞有些不好意思,说:“刚擦过,不管用的,别擦了。”
戏散之后,街上的人多了起来,像潮水一样,一袋烟工夫后,又少了。天开始慢慢黑下来,河里没有水,顺着河床吹来的风带着微微的凉气。我和钟飞开始收拾摊子,歌舞那边的声音更加大了,等我们回去的时候,它的灯亮了起来。
钟飞住在一个农民家里,大炕,一天两元钱,行李自带。我们进去的时候,炕上已经躺着些人。钟飞说:“我的兄弟。”一个躺着的人往旁边挪了挪身子。钟飞说:“晚上睡我旁边。”以前也和别人同居过,但像在一个大炕上和这么多陌生的人睡一起还是第一次。
吃过晚饭后,镇上的戏开了,咿咿呀呀的声音隔着很远仍然传了过来。钟飞说:“看戏去吧?”我说:“不爱看。”“那出去转转吧。”躺着也没事,便随着钟飞出去。晚上,街上的人也不少,都是一群一伙的年轻男女,他们热烈地调笑着,夜晚因了他们而生动起来。和他们一比,我的青春消失得太快。钟飞显然也不爱看戏,进戏院转了一圈,就出来了,向河滩走。我知道钟飞是想去看歌舞。河滩上比白天又冷清了许多,许多摆摊的已经回去,剩下那个大篷歌舞便突兀地热闹。他们不知道从哪儿接了电,灯光亮得刺眼,一大群人站在篷子口,像扑火的飞蛾。远远就听见强劲的音乐和喇叭传出的刺耳的声音。到了近前,还是有穿得很少的女人在高高的台子上扭。不知道她们到底有多少人,像这样一直扭下去,也真够累的。钟飞说:“进去瞧瞧吧?”我说:“你真的想去看?”钟飞很认真地点了点头。和他到了卖票的跟前,一张票居然要十元钱。十元钱要套一百个圈圈,钟飞得等多长时间。我说:“你进去吧,我在外面等。”钟飞没有理会我的话,已把票买好。进去以后,里面已经有不少人,但表演还没有开始。一些人显然来得早,等得已经不耐烦,嚷嚷着让快点开始。几个表情阴郁的年轻男子手里拿着橡胶棒,一声不吭地盯着声音大的地方。说话的人慢慢注意到了目光,声音低了下去。我觉得这里的气氛怪怪的,想走。可是一想到花了二十元钱,便舍不得走。外面的声音仍然很热闹,隔一会儿有一个穿的很少的女子出去换外面扭的那个。我感到里面一点意思也没有,还不如外边热闹。就这样大概等了二十分钟,篷子里人满满的了,一个年轻女的宣布表演开始。有七八个女子上了临时搭好的台子,音乐响了起来,这些女的开始扭动,随着音乐的加强,她们开始脱自己本来很少的衣服,台下的观众屏住呼吸,但隐隐能感到有股骚动。一个曲子完了,这些蹦跳的女的尽管穿得那么少,还是一个个满身满脸的汗。她们披上一件薄薄的纱质的衣服,接过旁边的男的递过的水,一杯水还没有喝完,那些阴郁的男子催她们上台。音乐又响了起来,这些女子抛下刚才披上的纱衣,卖命地扭了起来。周围的男人都是兴高采烈的模样,我心里却很难受。中间她们又休息了一回,又扭了一曲,灯光都亮了,阴郁的男人们开始清场。观众们还意犹未尽,有些人嘴里嘟哝着。其中的一个女子被一个阴郁的男子指挥着去外面继续招徕观众。
出了大篷,清爽的空气扑面而来,戏还没有完,街上到处是川流不息的年轻人,刚才的那些像梦魇一样。到了一个小酒馆前,钟飞不走了,说:“喝酒去!”此时我也非常想喝酒。没等菜上来,我们先干了一杯。
钟飞说:“你看到了吧。她们都是被拐骗、强迫的。我听一个老江湖说,她们都是农村的孩子,被这些班主以招收舞蹈演员的名义骗来,一到他们手里,自由也没有了,被强迫着跳脱衣舞,谁要是不听话,就挨打,被轮奸。”
“她们不想跑吗?”
“谁跑得了?平时不允许出去,一旦上街,就有人跟着。再说,她们没有身份证,没有钱,跑出来好人们谁敢收留这些不明不白的女人?还不是跑出狼群又落入虎口。”
“没人管吗?”
“他们只收管理费。管还敢出来跳?不瞒你说,我已经跟这个班到过好多地方了。也向相关部门举报过,可他们只是被赶走或被罚几个款,根本没人认真查。”
我知道钟飞说的一定没错,现在仿佛只有事情弄得大了才有人管,一般个人的安危或喜乐,是没有人关心的。
“咱们得救她们。”钟飞突然说。
“救她们?”想到那些神情阴郁的男子和他们手中的橡胶棒,我的正义心就慢慢萎缩了。
我和钟飞一杯接一杯喝酒,每想出一个办法,马上觉得不行。一瓶酒完了,也没有想到个好的办法。眼前的事情奇怪极了,明明它是错的,但就是没有办法,我对自己失望到了极点。
回了农家的那个住处,炕上躺的人更多了,有几个在小声说话,大多已经睡着了。戏还没有完。这是多么歌舞升平的一个夜晚啊,可是那些可怜的女子,一定还在用劲跳着。
那个晚上,我喝多了。半夜感觉有人踩了我一脚,懒得动。然后被尿憋醒,去院子里解决时,见对面过来一个人,是钟飞。很奇怪。还没有等我问他,他先说:“上厕所。”说完就回屋去了。我解完手,看到河滩那边有一道红光,头晕,没有多想,同去倒在炕上。
第二天醒来,头还疼,听到人们嚷嚷河滩那边着火了。钟飞还在旁边呼呼睡着,拍醒他,说:“河边着火了。”他胡乱套上衣服,我们上了街。好多好多的人出来,都朝河边走,路上大声猜测和议沦着这件事。
到了河边,已经有一大群人围着。昨天表演
歌舞的地方,黑糊糊的一片,那些帐篷和木头搭的架子都烧没了,还在微微冒着白烟。神情阴郁的男子们沮丧着脸,站在外边用些长长的竿子挑里面的东西,可是里边黑糊糊的,什么也没有了。一个身体臃肿的胖子围着烧了的场地转来转去叹着气。那些年轻的女子不见了。周围有些警察,在询问情况。
我看了看钟飞,他还一副没睡醒的样子。看不见东西的那只眼紧闭着,但像一把锋利的刀子,能让人感觉里面的光,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双手抱在胸前,十分镇定,活脱脱一副大侠的样子。
那些年的夏天,仿佛又回来。我们握着木头做的大刀、链条做的火枪,躺在钟飞家的炕上,恣意地谈论着江湖上的事情。令狐冲、乔峰、李寻欢都是我们向往的对象。我们以后在江湖上都可以遇到自己挚爱的人,我们为了她们可以生、可以死,江山、富贵只不过是过眼烟云。一只眼的钟飞比谁都更像大侠,他那只眼睛肯定是在一场恶战中瞎的,而且是为了抢救一个美女。
过了一会儿,来了几个武警,牵着一只警犬。钟飞看着他们从远处走来,脸色变了一下。然后他拽了拽我的衣脚。我不知道这个警犬会嗅出些什么。我们下了河道,河道里干干的,都是石头和细沙子,走上去有些硌脚。记得人们说过,趟过有水的地方,警犬就闻不到了。河边人们来来往往,有些人已经开始摆摊子。没有人注意我们悄悄离开。我们渴望找到一处有水的地方,可是转遍了小城的周围,也没有发现这样的地方。
警犬没有追来。钟飞退了房,我帮他拿着东西,我们坐上回家的车。路上钟飞一声不吭。车是慢车,每一个小站停下,都有人上车和下车。车上到处都是煤灰。我们到了家,东西也没有放,跑到附近的水库里,痛痛快快游了半天。钟飞把那些竹子做的圈圈拴在一起,绑了块大石头,沉入水底。他说再也不跑江湖了。
钟飞跟上建筑工队当了小工,每天脸晒得黑红黑红。很快他就能拿起泥刀,大工缺的时候,让他当二把刀。秋后收了玉米,有人给钟飞介绍他的一个亲戚,是个瘸子。钟飞没有犹豫,答应了。他们很快办了婚事。
婚后钟飞还是特别勤快,遇到什么做什么,挣了每一分钱都交给老婆。年底的时候,他在街上卖画,穿着厚厚的棉大衣,戴着一顶绒线做的帽子,脸冻得发紫。每一个顾客过来都十分殷勤,认真地和他们讨价还价。中午怕耽误生意,不回家吃饭。瘸子老婆给他送吃的,装一个军用饭盒里,钟飞几口就拨完了,然后向周围的人家讨点水喝。天黑得看不见了,才收摊。
谁都觉得钟飞普通极了,可我知道钟飞是过过江湖日子的,他肯定还有好多我不知道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