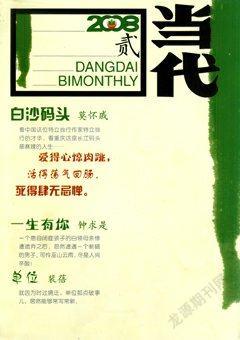我的母亲
思 公
思公,原名彭红,北京人,生于1955年9月26日。198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88年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获硕士学位。1970年起北京某工厂做工8年,曾服务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杂志社、北京师范大学一分校、中国光大公司等单位。
本人的博客被搜狐博客首页和文化传媒群名录推荐http://sigong.blog.sohu.com,在美国出版过文集《解不开的中国结》。
我母亲马上80岁了,她每天最操心的大事就是我是否回家吃饭。如果我回家她就拖着半身不遂的身子去厨房,先洗洗菜,做点准备。我常和母亲聊天,很多事她总重复说,对我而言,有点烦闷,但有时也让我吓一跳,例如,她恨以色列欺负巴勒斯坦人,有一次说起,让小孩当人体炸弹不好,她竟气愤地说:我愿意带着小孩去炸他们。我知道老太太说的是气话。但想想她的一生,真的挺神奇。这首先要归结到她的苗人血统。
老太太的祖上虽不是特大的官,但她家的故事很有名。她祖上是湖北恩施那边的苗王,与清军打仗,不知是败了,还是降了,还是战死。总之苗王的孩子被清朝一个大将军收养了,取名叫樊燮。小孩子长大也成了将军,太平军攻打长沙时,他被湖广总督官文派去增援,此时湖南巡抚请左宗棠为师爷,整个湖南全听师爷的。樊是个二品总兵,看不惯,大敌当前与左宗棠闹起来,官司打到北京。一方是湖广总督官文,一方是曾国藩、胡林翼等,满朝谏官纷纷上折言此事。其中年轻的翰林潘祖荫一篇宏文洋洋洒洒,支持曾胡二人。据说文中一句“大清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深得上心。结果樊被免职,左升官,潘成名。此事算是清末一个著名事件了。人们也一般了解到此。
因为母亲是樊家人,所以我知道后来的故事。这个樊燮输了官司气得不成,自己堂堂大将军,输给了一个举人,更是输给了潘的文章,都是吃了没文化的亏。从此发誓让孩子读书,他把两个男孩子关在木楼上,锯掉梯子,全心读书,送饭菜时,现搬来梯子出入,并让两个孩子身穿女服,言何日得举人,何日换男装。如此蛮干,结果一成一败。其二子樊樊山得举人、中进士、点翰林,仕途通达,不仅官做到巡抚,而且著作等身。但其兄,由于苦读成疾,英年早逝。樊山兄弟情深,将其哥之子收养,我母亲系其哥之后,但也算樊之曾孙女。她出生时樊樊山还健在,对我母亲极疼爱。民国时樊是著名清朝遗老,与袁世凯、徐世昌、劳乃宣等过从甚密。另外他酷爱书画古玩、戏曲诗词,对齐白石有知遇之恩,对梅兰芳一家也有提携吹捧之力。“文革”中,我家毁了不少字画,据母亲讲,有几幅是张之洞、翁同龢送的字。母亲说她是亲眼看着樊樊山死的,吃着酥糖,一下子噎住,就卡死了。
母亲从小生活在大宅门,说起往事,很有意思。她是独生女,脾气也挺大的。小时学习成绩很好,总不明白今天小孩怎么成天学习辛苦异常,她们那会儿,没耽误玩,学习也很好。抗日战争爆发,我外公去了重庆,我母亲在北京女附中读书,很快就左倾了。她读了不少苏联的小说,又恨日本人,所以1942年就和一些同学跑到晋察冀根据地参加革命,一直在晋察冀城工部。
我曾问过母亲,家里条件挺好,为什么去革命。她也说,是呀,那时看到的坏事并不多,哪有现在这么多。在城里看过从黄泛区来的难民,很惨,穷人死在路上的也有,为这我就要革命了。我参加革命主要为打日本,她说,其实,日本兵在北平城还是挺文明的,但不当亡国奴的道理还是可懂的。真正要革命,就要打日本。她说过不少当时解放区的事,她说日本人在城里看着挺文明,到了农村可就和野兽一样。她看到了穷人怎么个穷法,人穷成那样,别人也就不把你当人看。她见过村里成堆被日本人杀死的尸体,老人、小孩都有。她去解放区不久,就赶上大扫荡,当时她发了疟疾,高烧不退,刘仁派了个小警卫员和一头骡子,让他们随几个带着婴儿的妇女一起行动。那些孩子是一些领导的。她们东躲西藏了几个月,最后她的病居然好了,但那些婴儿几乎一个也没活下来。过后,她被派往延安,走到附近,封锁太严被迫折回,就去华北联大政治班,毕业后继续在城工部工作。
母亲对解放区的生活印象很深,也很怀念,觉得那时同志关系真好。她曾见邓拓(边区《晋察冀日报》社长)单吃鸡蛋炒饭,还去提过意见。后来有关领导特意解释,因为他写文章用脑子,特批的。一次鬼子来了,和她一起的一个男大学生、一起钻了地道,但洞很狭窄,该大学生一米八的大个,在一处被卡住,后边的人骂个不停,他就在那儿哭。结果这个人不久就偷偷跑回家了。还有她对解放区奇怪的夫妻关系印象也较深,男女双方长期不见,见到后,相互握手,这个说张同志你好,那个说小李同志好。前几天家里来了个老头,走后母亲说,他到解放区时,才14岁,是她朋友的弟弟。她们对他特好,结果他觉得我们都像资产阶级小姐,左极了。没想到他后来划了个大“右派”,一直倒霉到退休。
抗战时,母亲经常到北平从事地下工作,向家里要了400块大洋,开了个照相馆当秘密联系站。1945年初,她在北平被日本宪兵队抓到,施了一通刑后,日本人看她年纪小,认为可利用,就把她关在宪兵队对面一个汉奸家,诱使她联系其他同志。但她居然利用一次机会,穿上汉奸老婆的衣服逃跑了。而与她同时被捕的一个同志最后牺牲了。她回解放区后,就调到天津,先在日本纱厂做工运,后又考入南开大学做学运,是当时南开地下党领导之一。她说其实自己在南开一点书都没念。天津解放,她和当时的市长黄敬一起进城。她对姚依林、刘仁、黄敬等领导印象很好。她说黄敬特有才气,也敢干,资本家请他跳舞,他也敢去,从早到深夜地工作,精力旺盛。做报告,一张嘴就几小时,开会就打瞌睡,但别人说什么都知道,睁开眼可以接着你说。
解放不久,她即调回北京,在市委地方工业局。当时她的办公室对面有一张桌子,人家说是毛岸英的。毛岸英自己要求到工厂锻炼,就给了他个办公桌,但据说他没用过,直接下到工厂,并很快就去了朝鲜,那里很少有人见过他。我母亲仅见了他一次。我母亲比较单纯,天性不喜欢政治。解放后,一心想学习,搞技术,开始先被送到中央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前身),但人去了,突然发现档案中的被捕问题没有正式结论,结果回来等组织做结论,时间一拖,错过了。不久中央各部委从地方调人,她就进了电力部。在电力部,她还是一心想学本事,搞技术。正好不久中央开始有一个干部进大学读书的政策,干部可参加考试进入大学本科,单独管理,俗称干部班。当时我母亲已经30多了,顺利考进清华,和所有本科生一起读火力发电专业。我还记得小时候,一到暑假,就去清华住到我妈的宿舍。她当时已经有三个孩子,还兼着干部班支部的党务工作,硬是和在校本科学生一起苦读五年,一起考试,拿到毕业证书。
我母亲说她当时各科成绩相当好,回部里时,张彬副部长高兴得很,冒出一句:好好学习钱正英部长,弄得我妈很奇怪。很快我母亲就被任命为电力部最大的一个设计院的副院长,兼副总工程师。妈妈后来回忆说,这简直坑苦了她。她在大学学的是火电专业,而要负责的是设计一座发电厂的所有技术问题,等于刚刚大学毕业去干大专家的活。那些年,我们很少见到她,不是去哪个工地,就是下哪个厂。我们小时候就没有父母管过我们的印象。家里什么家具也没有,除了从公家租的床、桌子、椅子、书架、一套沙发,就是几个纸箱子。家里的事全是保姆管。有印象的是邻居、亲属,他们都对我们很好。
对我来说,一切都天翻地覆,是从“文革”开始的。在大学做领导的父亲1966年先被打倒,由于牵涉到一个中央专案,从此被关押,然后送干校监管劳动,直到1973年才回京。母亲也因被捕问题和与北京旧市委的关系被打倒,关进牛棚达三年之久。我家楼房墙上都是打倒父母的大标语,家被抄了五六次。由于住地和母亲单位很近,所以我亲眼见到很多难忘的情景。当时各单位礼堂经常放电影,我们小孩总能溜进去看。有一天听说放刘少奇访问印尼的批判片,我和楼里的小孩儿一起去,当钻进礼堂时,发现先开批斗大会,正看到母亲在台上被人押着挨斗,吓得我赶快跑了,电影都没看。“文革”结束后她告诉我们,她挨了上百场斗。另外她们单位当时总是押着一群牛鬼蛇神去对面一个工厂劳动,我见过多次,而押着他们的就有我同班同学的母亲,每次我见到都赶快藏起来。我妈放出来后说当时就想看看自己的孩子。母亲还说过,有一次听说我在外面打架,她哭着求看管人员,别欺负她的孩子。
我母亲几年后回来,她头发全白了。我们兄弟姐妹都是破衣烂衫,身上长了很多虱子。我记得母亲一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用开水烫所有被褥、衣服。由于当时只发少量的生活费,很多东西买不起。姥姥家有个缝纫机,我母亲就找破布给我们做衣服,自己纳鞋底,做鞋子。她甚至学做木匠,钉箱子。她到处买处理品,烂水果、猪骨头,这渐渐成了她的习惯。今天我家还有很多布,都是她为了做衣服,在不同时期买的。1975年她恢复工作,任电力规划设计总局副局长,但她的记忆力坏了,每天丢三落四,上厕所总把腰带忘在那里。她每天骑个破极了的自行车上班,下班就去买便宜菜。她总觉得愧对孩子,所以我们的事,成了她心中最大的事。直到我们都考上大学,她才心安了。有一段,她最自豪的就是向人讲自己孩子,如我弟弟在MIT,我妹妹在哈佛,也会说我怎么从工人考上大学到留学。现在她记性更差了,很多事都记不清了。但奇怪的是,她对自己在大宅门里的童年生活越来越留恋,一件件小事都能说得很详细。她经常坐在电视前和电视说话,看到不好的事,朝电视嚷,和电视辩论。她对坏人坏事嫉恶如仇,总不理解为什么没人去管。
我母亲16岁参加革命改了名,几乎没什么人知道她的真名,其实那是很好听的名字——樊巧。
责任编辑 洪清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