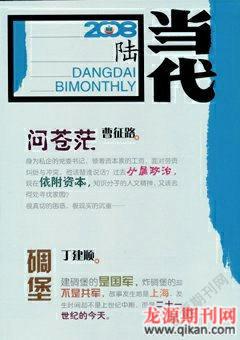荆芥
王 松
王 松,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2年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数学系,曾当过知青、电视导演等,现为天津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曾在《收获》、《人民文学》、《十月》、《当代》、《花城》、《钟山》、《大家》、《中国作家》等国内各大文学期刊发表长、中、短篇小说作品700余万字。
那时候,冯伯在我们这条街上并不起眼。
我们这条街虽然不长,却住着很多令人尊敬的人。他们多是在小医院工作。在我们这条街的附近有一间卫生院,由于规模很小,就被人们称为小医院。小医院的职工宿舍就在我们这条街上。每当住在这里的医生或护士上班下班,街上的人们总会很礼貌地跟他们打招呼。我们这条街上的人都很尊重知识,也尊重科学,因此深知搞医的人很了不起,他们不仅能挽救人的生命,甚至还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冯伯也在小医院工作。但他的工作是看大门,因此走在街上也就不太引人注意,只有我们这些小孩子经常跟在他身后冯伯冯伯地叫。那时冯伯的年纪并不很大,只有四十来岁,我们叫他冯伯,是因为他比我们的父辈稍长几岁,再有就是他的外表。冯伯没结过婚,家里只他一个人,所以身上的衣服就不很整洁,从外表看去也有些早衰,总是蓬乱的头发已夹杂着灰白,走路驼着背,低着头,脖子直直地向前伸着,给人的感觉像是五六十岁的样子。我们有时喊冯伯喊得高兴,还会喊出一串歌谣来:
冯伯冯伯伸着脖儿!
低头像乌龟!
抬头像罗锅儿!
冯伯听了从不生气,有时还会掏出一些小瓶子或注射器一类的小东西给我们玩儿。那时候的医用注射器还是玻璃的,用过之后经过高温消毒还可以重复使用。我们经常把注射器当做水枪,用来射击落在树上的蜻蜓。蜻蜓的翅膀被喷了水,一飞就会掉落下来。但后来这个游戏就被禁止了。禁止我们这个游戏的是罗平。罗平也住在我们这条街上,是小医院的医生,而且是主任医生。由于小医院规模小,各种科室不是分得很细,因此罗平这个主任就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统统兼管。罗平主任一次在街上发现我们在玩注射器,就捉住其中一个孩子问,这东西是哪来的?又问,是不是从医院偷出来的?我们当然不承认是偷的,就理直气壮地告诉他,是冯伯给的。冯伯给的?罗平主任听了立刻皱起眉头。恰在这时冯伯朝这边走过来。罗平主任就招招手,把冯伯叫到跟前问,这东西是你给他们的吗?冯伯看了点点头,说是。罗平主任一听立刻威严地看着冯伯,说这种医疗器械,怎么可以随便从医院拿出来给他们玩儿?冯伯解释说,这些注射器都已经报废,不能再用了。罗平主任说如果报废就应该销毁,对医疗垃圾的处理是有严格规定的,这你不懂吗?冯伯的脸立刻涨红起来,嗫嚅了一下说,我已经……用开水煮过了,应该……没问题。你认为没问题就没问题吗?你不过是一个在传达室看大门的,你懂多少医学知识?罗平主任这样说罢,就将我们手里的注射器都拿去了。
我们必须承认,罗平主任这样做在道理上是没错的,如果这些注射器真的没有消毒干净,上面还沾染着什么细菌或病毒,这种可能性从理论上并不是不存在。但问题是罗平主任最后说的那句话,他对冯伯说,你不过是一个在传达室看大门的,你懂多少医学知识?他对冯伯这种轻蔑的态度让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冯伯虽然只在小医院的传达室看大门,但我们知道,他的确懂很多医学知识。比如他经常给我们讲,小孩子在长身体的时候火力很旺盛,火力旺就容易阴虚,因此应该多吃一些红薯和山药。红薯和山药都是在土里生长的根茎食物,属阴,吃这些东西正好可以补阴虚。他说不仅是小孩子,红薯和山药是老少皆宜的食物,谁吃了都会有益处。再比如,他每到春天就会告诉我们,春天身体燥热,要多吃一些萝卜。那时萝卜还很便宜,几分钱就可以买很多,吃了萝卜再喝一些茉莉花茶,这样可以润燥。他说到这里还告诉了我们一句谚语:“萝卜就热茶,气得大夫满街爬。”那时我们想,冯伯知道这样多的事情,就算他在小医院的传达室看大门,怎么能说他不懂医学知识呢?
冯伯后来真正引起街上人们的注意,是因为小北京的父亲。
小北京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因为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街上的人就都叫她小北京。据说小北京过去真是北京人,结婚以后才搬来我们这条街上。但她的男人没过几年就在一场意外事故中死了。那时她男人是在一家汽车运输场工作,一次站在墙边指挥同事倒车,嘴里喊着“倒!倒!”,就让那辆几吨重的大卡车倒在了自己身上。据当时在场的人说,小北京的男人死得很惨,他的下身还好好地站立在墙边,上身和脑袋却已像肉饼一样地被挤压在墙上,人们为他收尸时只好用铲子将他小心翼翼地铲下来。小北京从此失掉经济来源,每月只靠她男人厂里给的一点补助生活。后来经罗平主任介绍,让她为小医院浆洗一些床单和褥单,这样才有了一点收入。一次小北京来小医院送洗好的床单,在门口偶然遇到冯伯,就说起她父亲的事。小北京说她父亲的胃口最近一直不好,吃了饭就胀气,有时还会呕吐,来医院让罗平主任看过几次也不见效,这几天眼看越吐越厉害,她真担心他的胃里是不是长了什么东西。冯伯一向对小北京很好,对她家里的事也很热心,听了立刻就说,我去看一看吧。当时小北京还不太相信,说你去看看?来医院这里让罗平主任看过几次都不管事,你能看出什么呢?冯伯只是笑笑,说去看个试试吧。于是这天下午,冯伯下班就来到小北京的家里。冯伯先给小北京的父亲摸了一下脉象,又让他吐出舌头看了看,没说什么就转身走了。冯伯在这个下午去菜市场买了一条半斤多重的活鲫鱼,又去药店买了两味中药回来。他在家里先将鱼鳞刮掉,剖开洗净,将这两味药材装进鱼肚,用黄泥封好,然后就放到火炉上慢慢烧烤。待烧熟烤干,从鱼肚里取出中药碾成粉末,就给小北京的父亲送去,嘱他用米汤送服,每天两次。小北京的父亲听了将信将疑,闻了闻这包药粉,味道也有些怪怪的,但咬一咬牙还是按照冯伯的话把这些药粉吃下去。不想三天以后竟然真就见了效果,不仅胃不再胀满,也不再打嗝儿,心里感到舒服了很多。这件事立刻就在我们这条街上传开了。人们都无法相信,尽管冯伯经常能说出一些“萝卜就热茶”之类的医学常识,但小北京父亲的胃病毕竟是一种顽疾,连小医院的罗平主任都束手无策,他怎么会轻而易举就能治好呢?第二天上午,罗平主任就来找冯伯。当时冯伯正在街上一边调制一种叫鱼鳞胶的东西,一边向周围的人们讲解,他说这种鱼鳞胶是用给小北京父亲配药的那条活鲫鱼做的。做这种鱼鳞胶的方法很有讲究,要先将刮下的鱼鳞淘洗干净,放到沸水里反复烹煮,待煮烂去渣,再加进一些佐料放到阴凉处晾凉,这样就成了像胶冻一样的东西,每天吃一小块,会对牙齿很有好处。罗平主任走过来时,冯伯正在用麻油调拌鱼鳞胶,小盆里散发出一股好闻的腥香气息。罗平主任伸头朝小盆里看了看,然后皱皱眉问,晓燕她父亲的药是你给送去的?
罗平主任是指小北京。小北京姓严,叫严晓燕。
冯伯抬起头看看罗平主任,说是。
听说是用鲫鱼做的?
还有两味中药。
哪两味中药?
苍术和绿矾。
用多少?
各两钱。
谁告诉你的苍术、绿矾和鲫鱼放到一起可以治胃病?
冯伯并没立即回答,只是很认真地看看罗平主任。
罗平主任又说,鱼在中药里是发物,怎么可以随便给胃病患者吃?
冯伯沉了一下,才说,《本草纲目》里说,凡任何鱼均有火,唯鲫鱼无火,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所有的鱼都是有发性的,只有鲫鱼没有发性。罗平主任听了嗤的一声,说《本草纲目》?你也懂《本草纲目》?冯伯就不再说话了,只是埋下头去继续调制鱼鳞胶。
罗平主任看一眼又问,这……是什么东西?
冯伯说,鱼鳞胶。
弄这东西干什么?
可以治牙齿松动。
罗平主任朝围在旁边的人们环顾一下,又沉了沉说,你以为晓燕的父亲是吃了你那些奇怪的药才好的吗?他得的是什么病你知道吗?是胃扩张,而且已经有些下垂,他是经过我的治疗病情才有好转的,我今天告诉你,不是随便谁都可以开药方的,这要有处方权,如果连一个在医院看大门的都可以胡乱开药治病,还要我们这些医生干什么?罗平主任又斜了冯伯一眼说,你以后只要把大门看好,把传达室的卫生做好就行了。
他这样说罢,又朝冯伯手里的鱼鳞胶瞥一眼就转身走了。
罗平主任这样来对冯伯说话自然不仅仅是因为开药的事。街上的人们都知道,自从小北京死了男人,罗平主任一直对她很关心,冯伯这样为小北京的父亲治病不仅很伤罗平主任的面子,也会让他很不舒服。在罗平主任对冯伯说这些话时,我就站在旁边的人群里。我发现罗平主任走后,冯伯的脸色很难看。我知道冯伯虽然平时很少说话,却是一个很有自尊的人,罗平主任的这些话一定深深刺伤了他。冯伯在这个下午没去小医院上班。他去商店买了一些白酒,就在家里独自喝起来。冯伯平时并不常喝酒,他喝酒的时候就说明心情很好或很不好。他曾在一次酒后告诉我,一个人是无法跟自己说话的,但喝了酒就不一样了,人在酒后就可以跟自己说话,所以他每当想跟自己说话的时候就喝一些酒。冯伯在这个下午一定喝了很多酒。晚上我去他的家里,因为他曾答应过要给我一只装盘尼西林的小药瓶。我推开门一看吓了一跳,只见冯伯横躺在地上,跟前吐了一摊污物,屋里满是呛人的酒气。那时我还很小,我怕冯伯这样躺在地上会受凉,想把他弄到床上去,但是搬了搬却没有搬动。于是我想了一下,就跑去叫小北京。我想冯伯为小北京的父亲治好了胃病,现在冯伯有事她当然应该来帮一下忙。但小北京没在家。我立刻又跑去小医院。我知道如果小北京不在家里就一定是去了小医院,而且应该在罗平主任那里。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在罗平主任的诊室里见到过小北京。关于罗平主任和小北京的事,我们这条街上的人早有传闻。罗平主任也是一个人生活,但据说他是结过婚的,他的妻子在郊区的农村,罗平主任却从来不去看她,就像是没有这个人一样。有一年过春节,那个女人曾来找过罗平主任,当时街上的很多人都看见了,是一个很结实的女人,只是脸有些黑,牙也从嘴里向外龇出来。据说罗平主任跟这个女人的婚姻从一开始就不太情愿。罗平主任的父亲在解放前也是一个医生,而且是一个很特殊的名医,好像在一间国民党的什么中央医院工作,专为一些政府要员看病。解放那年,他父亲不敢留在大陆,就跟随国民党军队跑到台湾去了。罗平主任为这件事一直抬不起头来,因此大学毕业后就只好找了一个家庭成分好的乡下姑娘草草成婚。但罗平主任只跟这女人住了很短一段时间就打发她回乡下去了,而且从此再也没去看过她。那一次那个女人来找罗平主任,不知罗平主任跟她说了些什么,她当天下午就抹着眼泪走了。尽管事后罗平主任向街上的人们解释,说他早已不想再跟这个女人过下去,但街上的人们在背后还是有些议论,说罗平主任这样做对那个女人很不公平,如果他不想再跟人家过下去,就应该干干脆脆地离开她,这样不跟人家过又不跟人家离,一个女人能被拖几年呢?
我在这个晚上来到小医院,在罗平主任的诊室门口伸头看了看,并没有发现罗平主任和小北京。我想,他们两人也许是在里面。罗平主任的诊室是里外套间,外面一间接诊,里面的一间作检查用。这时我发现,那间检查室的房门关得紧紧的,于是也没多想就过去敲了敲,又敲了敲,嘴里喊着严阿姨!严阿姨!这样敲了一阵,见里面没动静,正要再敲,就见房门慢慢打开了,罗平主任好像刚洗过手,一边用毛巾擦着走出来。他脸色难看地问我,这样叮叮哐哐地敲门,有什么事?我没回答,朝他身后看了看,发现小北京果然在里面,正一边整理着衣服一边捋头发。罗平主任又回过头去对小北京说,我已经检查过了,你的身体没什么大问题,放心吧。小北京哦哦了两声,就走过来问我,找我有事吗?我不想当着罗平主任说出冯伯喝醉酒的事,于是想了想对她说,你……快回去吧。小北京一愣问,怎么了,是不是我家里……出什么事了?我说不是,然后又迟疑了一下才说,是……冯伯家的事。冯伯家的事?罗平主任立刻回头看看我,冯伯家有什么事?我只好说,冯伯摔到地上了,我想让严阿姨帮我……把他弄到床上去。罗平主任皱皱眉说,街上那么多人,你为什么偏偏跑来这里找她?我这时已经不想再跟罗平主任多说什么,于是就用眼睛看着小北京。小北京似乎犹豫了一下,又看一眼罗平主任,但还是立刻拉起我从小医院里出来。
在这个晚上,我和小北京赶来冯伯家时,冯伯已经从地上起来。他大概是想自己爬到床上去,但试了试没有成功,所以就蜷着腿坐在地上,两手扒着床沿,把头靠在上面仍然昏睡。我和小北京费了很大气力才把他弄到床上去。冯伯显然刚又吐过,身上的衣服满是污渍。小北京竟然是一个很细心的女人,也很会照顾人,她先将冯伯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他盖上被子,又用温水拧了一条毛巾来为他擦脸。我在一旁看着,忽然对小北京的感觉很好,她这样悉心地照顾冯伯让我的心里感到一些温暖。冯伯这时就像一个乖孩子,躺在那里任由小北京摆布,嘴里不时发出哦哦的呻吟。小北京忙完这一切就准备回去了,她对我说,太晚了,你没什么事也回去吧。我又在冯伯的家里呆了一会儿,见他还没有醒来的意思,就也走出来。
这时外面的天已经大黑下来。
我在走过街角时,忽听有人在暗处说话。我起初并没在意,走到近前才听出来,竟是罗平主任和小北京。显然,小北京是刚才从冯伯的家里出来时,在街上遇到从小医院下班回来的罗平主任。罗平主任说话的口气不太好听,好像是让小北京去他那里,但小北京说她累了,有什么话就在街上说吧。罗平主任就酸涩地说,你当然是累了,你去伺候那样一个酒鬼,还沾得一身酒臭气,你能不累吗?小北京立刻说,你说话不要这样难听好不好?冯伯曾给我父亲治过病,他现在有事了,我去帮他一下有什么不可以呢?罗平主任冷冷一笑说,他给你父亲治过病?你也认为你父亲的病是他给治好的吗?小北京说当然是他治好的,我不管你怎样说,我父亲就是吃了他的药才见好转的。好吧,罗平主任哼一声说,就算你父亲的病真是吃了他的药才好的,那也不过是他蒙上的。小北京立刻不服气地说,蒙上的?治病这种事是可以随便蒙的吗?罗平主任说,你想过没有,他不过是一个在医院看大门的,每天发一发报纸还可以,怎么可能会给人治病呢?难道你宁愿不相信我也要去相信他吗?
罗平主任说的话我也曾不止一次想过。冯伯并不是医生,他怎么会给人治病呢?据冯伯说,他小的时候从没上过学,写字还是做工以后自己偷偷学的,那么他的那些医学知识又是从哪里得来的?我那时虽然还不能真正理解中医的博大精深,却也深知这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不仅要懂脉理,还要熟谙各种药性,这不是随便谁都可以做到的。我不得不承认,冯伯的确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虽然没上过学,但我经常看到他在家里翻看一些很厚的书,那些书大都已经很破旧,纸页也有些发黄,却被他保存得很完好,每一本书还都精心地包上书皮。我曾经问过他这是些什么书。冯伯只是笑笑,他告诉我,其实罗平主任说的话也有些道理,并不是随便谁都可以当医生的,这要有天分,还要有德行。冯伯说,一个不适合当医生的人就是当一辈子医生也不会是一个真正的医生,而天生就适合做医生的人即使没当医生,他的骨子里也还是一个医生。冯伯又对我说,据他观察,我将来就很适合做医生。我问为什么。冯伯说不为什么,只是一种感觉。他说我现在还小,等将来再大一点就可以教我一些脉理。冯伯的话说到了我的心里。也许是受了冯伯的影响,我的确很喜欢中医。我曾经无数次地想像过,如果有一天我给人家诊脉会是什么样子,我想,一定很神气。我对冯伯说,我将来倒不一定非要做一个医生,但一定要像他那样懂很多医学知识。
我想,一个人如果能给别人治病,那种感觉真是太好了。
自从冯伯给小北京的父亲治好了胃病,小北京总觉得应该感谢冯伯一下。那时候还不兴去外面的饭馆吃饭,小北京就想把冯伯请到家里来,亲手为他做几个菜。但她请了几次冯伯都没有来。后来小北京有些不高兴了,问冯伯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嫌她的家里脏,或是她做菜的手艺不好。冯伯一听小北京这样说,才只好在一天晚上来到小北京的家里。小北京的父亲不在家,好像是去了乡下。小北京的父亲有钓鱼的嗜好,平时就经常住在乡下的亲戚家。小北京在这天晚上给冯伯炒了几个很像样的菜,又拿出一瓶白酒。冯伯坐在桌前显得有些局促,连忙摆手说不喝酒。小北京抿嘴一笑问,是不会喝,还是不想喝?冯伯说不会喝。小北京说如果不会喝就不对了,那一次……她说到这里故意停下。显然,她是指那一次冯伯独自在家里喝醉酒的事。冯伯的脸立刻红起来,只好让小北京给自己的杯子里斟了酒。小北京正要给自己也斟一些酒,冯伯抬起头看看她,忽然说,你先等一等。小北京的手立刻停下来,问怎么了。冯伯伸过头朝小北京的脸上很认真地看了看。小北京的脸立刻飞起一片红晕,看一眼冯伯问,你干吗这样看我?冯伯又盯住小北京看了一阵才说,你……先不要喝酒。
为什么?
你最近,身体不好?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你的气色,你的气色有些不对。
小北京张张嘴,却没说出话来。
冯伯说,我先给你摸一下脉,喝了酒脉象就不准了。他一边说着就示意让小北京伸过手来。小北京迟疑了一下,还是把手放到冯伯面前的桌上。冯伯将三根指尖按在小北京的脉口摸了一阵,又换了一只手摸了一阵,然后问,你的……月事不太好?小北京涨红脸,低下头沉了一下才说,已经快一年了,总是……不太正常。
腹痛?
嗯。
有血块?
是。
血色是黑的?
是……是啊。
小北京抬起头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冯伯就不再说话了,只是埋下头去一口一口地喝酒。
冯伯第二天上午就去菜市场买了几只甲鱼回来。这些甲鱼都是灰绿色的,很大,用草绳拴住头,把脖子坠得很长。当时我正在街上,看到冯伯的手里拎了几只这样的东西就有些奇怪,不知他要干什么。但我知道,冯伯是绝不会自己吃的。冯伯平时一向很节俭。他虽然独自生活,每月的收入足够花销,却从不肯为自己多花一分钱。冯伯在这个上午将这几只甲鱼径直拎到小北京的家里去,并叮嘱她要清炖,一定要炖得很烂,每天半只,连吃十天。当时我在一旁看着,立刻断定冯伯给小北京送去这几只甲鱼不会是只让她做菜吃的,应该还有别的用途,而且很可能又是药用。那时我还不懂女人的月事,因此心里就很奇怪,这样几只甲鱼能治什么病呢?小北京按着冯伯的叮嘱将这几只甲鱼用清水炖了,连吃十天,接下来的月事果然就正常了。后来我知道了此事曾问过冯伯,清炖甲鱼究竟有什么功效。冯伯想了一下只告诉我,能治气滞血淤,还可以疏肝理气,如果再加几味中药调气活血的话效果就会更好,只是……他沉了一下,又说,药补终归不如食补,所以如果能不动药还是尽量不要动药。我又问他,女人的月事是怎么回事?冯伯笑笑说,这你以后自然会知道的。
这以后没过多久就出了一件事。
一天上午,冯伯上班时突然和一个患者家属争吵起来。这在以往是从没有过的事情。冯伯一向对患者和家属的态度很好,在传达室值班室时还经常帮着抬一抬病人或拎一拎东西。他曾经对我说,来这里的都是病人,他们已经很不容易,所以如果能照顾他们一下就尽量照顾。其实在这个上午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一个患者家属蹬来一辆三轮车准备接病人回去,在经过医院门口时不小心将立在那里的一块写有“出入下车,注意安全”的木牌子碰倒了。要在平时,冯伯将这块木牌扶起来也就没事了,但这一次不知为什么,冯伯的火气却很大,当即上前拦住那个患者家属,一定要他自己过去扶起来。这个蹬三轮车的患者家属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脾气很愣,加上正急着要去接病人,就没有理睬冯伯,继续蹬着三轮车朝里走。这一下冯伯更生气了,立刻追上去拉住三轮车就跟那个年轻人吵起来。那年轻人也不肯示弱,于是两人越吵越凶,几乎惊动了整个小医院。后来医院的领导闻声出来,才将两个人劝住了。医院领导也感到奇怪,搞不清冯伯为什么只为这一点小事就发这样大的火。
事后我才知道,冯伯的情绪这样坏是与小北京有关。
冯伯自从给小北京送去那几只甲鱼,就对小北京更加关心,似乎因为他给她治过这种女人特有的疾病,跟小北京的关系也就更进了一步。小北京原想将那几只甲鱼的钱还给冯伯,但冯伯执意不肯收,于是心里很感激,每次再见了冯伯也就越发热情,甚至还去冯伯的家里帮他洗过几次衣服。但渐渐地小北京就感觉出有些不对了。小北京毕竟是一个孀居的女人,对男女的事比较敏感,她发现冯伯跟自己说话时越来越局促,连眼睛都不敢正视自己。终于有一天,冯伯就对小北京把心里话说出来。冯伯是在一天早晨下夜班回来去小北京家的。冯伯为此一定很认真地考虑了一夜。他去到小北京的家里时,小北京已经起床,正在忙着为小医院浆洗床单。冯伯也不说话,挽起衣袖就和她一起干起来。小北京起初过意不去,不让冯伯动手,但看一看他脸上的表情心里就有些明白了,于是也就不再说话。两人就这样默默地将所有的床单和被单洗完,又在院子里晾晒起来,冯伯才吭吭哧哧地说,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说几句话。小北京的心里已经有了准备,就点点头说,有话去屋里说吧。于是冯伯就跟着小北京一起去到屋里。冯伯在这个早晨究竟对小北京说了些什么,没有人知道,但一定是关于他们两人之间关系的事情,而且应该是被小北京以什么方式拒绝了。有人看见说,冯伯从小北京的家里出来时脸色很难看,走路也有些跌跌撞撞。
冯伯这样做显然有些愚蠢。但是,我敢断定,他在当时一定不知道小北京跟罗平主任的关系,甚至连听也没有听说过,否则他绝不会这样冒冒失失地去找小北京的。我想,冯伯一定是因为这件事心情不好,所以才跟那个患者家属吵起来。
如果冯伯就此收手,也许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事了。
但冯伯却似乎把自己绕住了,无论怎样也放不下这件事。当然,这也可以理解,冯伯虽然已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但对于他,小北京毕竟是他在感情意义上接触的第一个女人,也就相当于初恋,初恋一旦受到挫折对于人的打击是很大的,况且冯伯的脾气很执拗,是那种一条道跑到黑的人。冯伯又闷闷不乐地想了几天,就决定最后再去跟小北京谈一次。他认为小北京没有理由拒绝自己。虽然自己的年龄比她稍大一些,但自己从没结过婚,而她又是一个孀居的女人,所以他们两人到一起应该是顺理成章的,至少应该很合适。于是冯伯就在一天晚上又去了小北京的家里。冯伯选择在晚上去找小北京一定是经过考虑的,他不想让街上的人看见自己。冯伯是一个很好面子的人,上一次自己被小北京拒绝,街上的人们已经有些传闻,因此他不想再让人家看自己的笑话。冯伯在这天晚上来到小北京的家里。他敲了好一阵门,小北京才走出来。就在小北京开门的一瞬,冯伯从她的肩膀朝屋里望去,一眼就看到了罗平主任。罗平主任正坐在小桌的跟前吃饭,面前摆放着两只高脚的玻璃杯,显然正和小北京一起对饮。冯伯从罗平主任坐在那里的姿势和脸上的神态,立刻就明白了一切,罗平主任就像是在自己的家里,看上去很随意,也很惬意。冯伯突然有些茫然,面对着小北京竟然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小北京的表情也有些不自然,迟疑了一下才说,你……进来吧。冯伯慢慢地朝后退了一步,又退了一步,没有说话就转身匆匆地走了。这时罗平主任从后面追上来,叫住冯伯说,你这样急着走干什么?冯伯犹豫一下还是站住了,慢慢回过头,看着罗平主任。罗平主任就像这家里的主人似的说,既然来了,就进去吧。
冯伯说不了,我……还有事。
你是不是要找晓燕?
不……我谁都不找。
冯伯这样说着就转身朝院子外面走去。罗平主任又在他身后说,虽然你只是个看大门的,但咱们毕竟在同一间医院工作,说起来也算同事,我今天再劝你一句,以后不要再给人治病了,这对你没好处。冯伯似乎没听见,继续朝前走。罗平主任又冲着他的背影说,我这样劝你也是为你好,你再这样下去,迟早会给自己带来大麻烦的。
罗平主任这样说着,冯伯已经走远了。
罗平主任还是说错了。冯伯并没有因为给街上的人治病出什么事,倒是罗平主任自己,没过多久就有了大麻烦。这时街上已经乱起来,到处贴的都是用白纸写的大标语。这些标语上的字不知为什么都是歪歪扭扭的,用的笔也很不讲究,字迹粗粗拉拉像用刷子刷上去的。
那好像是一个上午,我们这条街上突然来了一群拎着糨糊桶挟着标语纸的人,他们每人的胳膊上都戴着一块鲜红的大袖章。这些人来到罗平主任家的门口,先将那些大字报和大标语铺天盖地地糊在墙上,然后就开始大声呼口号,口号声和各种吆喊声响彻整条街。人们起初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都跑出来看热闹,待来到近前才发现,原来罗平主任这时就站在这些人的中间。这时的罗平主任已经有些让人认不出,他浑身是土,头发也乱蓬蓬的,黑框眼镜斜歪在脸上,好像随时都会掉下来。当时我也挤在人群里。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那些人为什么会这样对待罗平主任。后来那些人逼迫着让罗平主任交待问题,还用木棒和木枪打他的头。罗平主任似乎有些站立不稳,晃了几晃才吭哧着说,自从他父亲去了台湾,他真的从没跟他联系过,他甚至都不知道他现在究竟在哪里。立刻有人用木枪捅了他一下,说交待你自己的问题,你是怎样充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罗平主任的身体又晃了一下,但想了想却没说出话来。接着周围的口号声就又响起来。这时我站在人群里看着罗平主任,心里不免有些难过。罗平主任平时是一个很注意外表的人,头发总梳得一丝不苟,衣服也都要经过精心熨烫。但这时他低着头站在那里,简直就像一个落泊的乞丐。我突然发现,其实他的身材并不高大,而且还有一些水蛇腰,这就使他看上去像一根弯曲的树杈。罗平主任在我心目中一向是个很帅气的男人,这时我看着他,不免有些失望。
罗平主任接下来做了一件让谁都意想不到的事情。
这时已将近中午,那些贴大字报的人已经走了,街上围观的人们也都已散去。突然,从他的家里传出一阵乒乒乓乓的声音,这声音大得有些夸张,其中还夹杂着刺耳的破碎声。原来罗平主任正在用一根木棒砸自己的家。罗平主任在生活上一向是一个很讲究的人,在他的家里有很多非常考究的玻璃制品,雕花玻璃茶杯,雕花玻璃烟缸,水印玻璃衣镜,还有很多的玻璃工艺品,这也正是那些贴大字报的人说他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原因。罗平主任在这个中午将这些东西统统砸烂了,他砸得很坚决,也很彻底,甚至将每一只玻璃杯都要砸成很小的碎片,最后索性连门窗上的玻璃也都砸下来,从外面看去屋里一片狼藉。街上的人们都很吃惊,搞不清罗平主任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家砸成这样。罗平主任砸完之后,又将一些东西装进一个纸袋就拎着走了。事后人们才知道,原来罗平主任装进纸袋的是他父亲当年留下的一些旧照片。他把这些东西全都交到上面去,并郑重声明,自己已将家里砸烂,从此要跟这个资产阶级家庭彻底决裂。然后,他还检举揭发了他的一个叔叔。他的这个叔叔也是医生,在外地的一间血液病医院工作。罗平主任检举说,他这个叔叔曾不止一次地打听过他父亲在台湾的地址,后来他们还通过一个在香港的老朋友有过很多书信往来。上级对罗平主任的这个检举非常重视,立刻让他把这些情况写成一份详细材料,并写出他叔叔所在单位的地址。
罗平主任对自己采取的这次革命行动受到充分的肯定。他得到的评价是,革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这时小医院里已经没有什么医务人员,平时本来医生就少,再这样一闹就几乎连门诊也无法再开,于是医院经过研究,就决定暂时让罗平主任继续工作。罗平主任的头发从此又整齐起来,身上的衣服也又一如既往地一尘不染。但他在接诊时对患者的态度跟过去相比却有了很大改变,说话很和气,服务也很周到,甚至有些殷勤。一次我去小医院看病,发现他正在为一个蹬三轮车的工人看脚上的伤,他竟然蹲下身去亲手为这个工人小心翼翼地脱掉鞋,又扒去袜子,在仔细地查看过伤势之后还亲自涂抹药膏,缠裹纱布。
但是,罗平主任也并不是对所有的患者都如此热心周到。
一次小北京的父亲从乡下的亲戚家里回来,突然就病倒了。他的病来得很快,下午刚回到家,傍晚就躺在床上不能动了。如果在过去,小北京一定会把罗平主任叫到家里来为她父亲看病。但这时却不行了,小北京跟罗平主任已经不再是过去那样的关系了。据说小北京的家里也有很严重的历史问题,当年她爷爷曾在北京前门开过一爿木器厂,生意做得很大,尽管到她父亲这一辈已经家道中落,但她爷爷曾经当过资本家,这段历史却是无法抹掉的,而且据说她父亲在年轻时还曾参加过三青团之类的反动组织。幸好小北京的父亲这时已没有工作,平时在街上也很少说话,所以街道上才没有太难为他。起初小北京并没有察觉自己跟罗平主任的关系有了变化,只是每次去小医院,发现罗平主任总以工作忙为借口不肯再跟她多说话。去他的家里也总是找不到人。罗平主任自从将自己的家里砸得稀烂,门窗也就没再安装玻璃,只用一些厚厚的白纸将窗洞封起来。这样一来反而更加严实,屋里有没有人从外面都无法看到。小北京渐渐就感觉出有些不对劲了,于是在一天下午去到小医院,待罗平主任刚为一个患者看完了病,就过去一屁股坐到他的跟前。罗平主任以为又来了一位患者,一边趴在桌上写着什么,随口问了一句,哪里不好?小北京说,心里不好。罗平主任抬起头一看才发现是小北京,于是连忙朝诊室的外面看一眼,问她有什么事。小北京盯住罗平主任看了一阵才问,你现在就这样害怕跟我来往吗?罗平主任立刻说不……不是。小北京说你不要说了,我已经明白了,我的家庭出身是资本家,我父亲又有严重的历史问题,你现在好容易又坐回到这个医生的位子,你是怕我再连累你。小北京一边说着苦笑了一下,又说,我已经听说了,你现在又想去找过去的那个乡下女人了,你去吧,她家的出身是贫农,你又并没有跟她离婚,把她接过来吧,以后好好跟人家过日子。小北京这样说罢就站起身头也不回地走了。小北京没有说错。那段时间,罗平主任确实去过几次郊区农村看那个女人。那女人生了一种怪病,肚子里不知长了什么东西,像个瘤子似的越来越大。罗平主任想给这女人看一看。但这女人很有志气,一次也没有见他。后来罗平主任好容易找到她,她就当面对他说,你不要再来了,我无论得了什么病都跟你没有关系。这女人说,你如果是过去来找我还可以,但现在不行了,你是落到这步田地才来的,我知道你以后又会有啥变化呢?这女人对罗平主任说,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跟你离婚的,就是想离也不会在这个时候。罗平主任原本还想再说服一下这女人,但看一看人家的态度如此坚决,也就只好作罢回来了。
小北京在这个傍晚眼看着自己的父亲呕吐不止,渐渐已有些昏迷,就只好让街上的人帮着用平板车拉来小医院。这时罗平主任刚刚洗过手,正准备下班,一见小北京的父亲被抬进来,先皱一皱眉,然后才一边脱着白大褂问,这是怎么回事?小北京就把她父亲在这个下午的发病过程对罗平主任讲了一遍。罗平主任走到床前,只翻开小北京父亲的眼皮看了看,又听了一下心脏,就从耳朵上扯下听诊器说,心音这样弱,呼吸也已经衰竭,看来病人不行了。小北京一听就急得流下泪来,说下午回来时还好好的,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然后又问,他得的究竟是什么病?罗平主任摇摇头说,这就很难说了,很多疾病都有可能导致呼吸衰竭,你把病人弄回去,抓紧准备后事吧。小北京看出罗平主任并没有用心给自己的父亲看病,于是就流着泪对他说,我知道你不想给我父亲治,可是就算他有什么历史问题,他也是一个人啊,你作为医生怎么能见死不救呢?罗平主任立刻有些不耐烦起来,说我怎么见死不救了?我不是已经给他检查过了吗?小北京说你这样检查只是草草应付一下,又有什么用呢?罗平主任说我应付一下?这怎么能说是应付一下?医生也不是万能的,不可能将所有的危重病人都抢救过来,有的病能治,也有的病就不能治。小北京没再说什么,只好流着泪把她的父亲又拉回来。她走在路上时,刚好遇到从外面开会回来的冯伯。冯伯自从那一次的事以后,虽然再也没去找过小北京,但是对她家里的事仍很关心。他这时一看连忙问,这是怎么回事?小北京就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冯伯听了,先摸了一下小北京父亲的脉象,然后让小北京先回去,说自己刚刚开会回来,有些材料要放到医院去,随后就到。
冯伯这时已是小医院“临时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冯伯当上这个副组长很偶然,也很突然,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不久前的一天下午,一伙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突然闯来小医院,他们冲到院长办公室揪出院长和几个副院长狠狠批斗了一阵,又高呼了一阵革命口号,就将小医院的领导权从这些人的手里夺过来。但他们夺权之后却并没有多大兴趣,他们的兴趣是要去下一个什么单位继续夺权,于是站在院子里看了看,一眼发现了正在传达室值班的冯伯。这些人知道冯伯是小医院的院工,平时的口碑也一向很好,于是就将他拉过来,让他当了小医院“临时领导小组”的常务副组长。冯伯直到正式担任了这个常务副组长仍然感到有些懵懂,他知道所谓的“常务副组长”也就相当于过去的常务副院长,却不知这个副组长具体应该怎样当法。于是就将自己的办公室设在传达室里,平时一边继续看大门一边办公。冯伯在这个下午是去上面开了一个什么紧急会议,但是直到散会,他也没搞清楚这个会议说的究竟是什么精神,只是领了一些材料和几本书就回来了。
冯伯在这个傍晚先去小医院放下东西,然后就赶来小北京的家里。
这时小北京的父亲两眼紧闭,气息也已经很微弱。但冯伯摸了一下脉象,感觉问题并不大,暂时还不会有生命危险。他又掰开小北京父亲的嘴看了看,让小北京把她父亲吐过的污物拿过来,先闻了闻,又拨着看了一下问,他下午吃过鱼?小北京说不清楚,他是在乡下亲戚的家里吃过午饭才坐长途汽车回来的。冯伯听了想一下,忽然又问,你去过这个亲戚那里么?小北京说去是去过,但已是几年前的事了。
冯伯问,他家的附近,是不是有河?
小北京想想说对,好像是有一条河。
冯伯点点头说,这就对了。
他又对小北京说,如果他分析得不错,病人现在应该还没有太大的事。然后让小北京去药店买一些白丁香来,又沏了很大一壶酽茶,将白丁香倒进去。这种白丁香一到茶里立刻就化成粉末状,而且很快被溶解开。冯伯让小北京帮着掰开她父亲的嘴,把茶灌进去。就这样灌了半壶,她父亲的肚子里先是咕噜咕噜地响了一阵,然后就开始呕吐起来。就这样吐过之后再灌,灌了再吐,直到将这一壶茶水全灌进去,小北京的父亲就将胃里的东西全吐出来。又过了一阵,小北京的父亲就渐渐苏醒过来。
冯伯问他,你中午是不是吃过鱼?
小北京的父亲想了想,说是。
吃的什么鱼?
是……鲤鱼。
冯伯点点头,轻轻嗯了一声。
事后冯伯给我讲,北方的河边一般都生有一种叫红荆的植物,学名也叫荆芥,这种植物春夏两季开花,花粉极容易飘散,一定是做熟的鲤鱼落上了花粉,而“荆花鲤鱼”是有很强毒性的,所以小北京的父亲吃了才会有这样的反应。冯伯说,他给病人用的是一种秘方,这个方子可以治疗很多种病。但是,我更感兴趣的还是这方子里的白丁香。我发现这味中药的形状很奇特,而且有一种怪怪的味道,不像是开在外面的那些丁香花朵。
直到很长时间以后,我才知道,原来白丁香就是麻雀屎。
在那个晚上,冯伯刚刚离开小北京的家,罗平主任就又去了那里。罗平主任下班回到家里,想一想觉得有些不对劲,小北京的父亲毕竟是在自己值班时来医院就诊的,倘若他回去之后又出了别的问题自己就有脱不开的责任,至少没有及时救治,这要追究起来可就说不清楚了。于是他吃过晚饭就又来到小北京的家里,想探一下虚实。罗平主任一进门就看到小北京的父亲竟然已经苏醒过来,正歪在床上喝米汤。他愣了一下,立刻上前问,怎么……醒过来了?小北京回头看他一眼,淡淡地说,不该醒过来吗?
哦,我是说……怎么醒过来的?
刚才吃了一服药,就醒过来了。
罗平主任的心里立刻一沉,就不再说话了。他刚才来时看到冯伯刚刚离开这里。小北京说她父亲吃了一服药就苏醒过来,那么这服药自然是冯伯送来的。可是罗平主任想不出,冯伯能送来什么如此有效的药呢?罗平主任过去一直不把冯伯放在眼里,即使这段时间,尽管冯伯已不是过去的冯伯,他罗平主任也不再是过去的罗平主任,但他的心里仍不把冯伯当一回事。可是这一次就不同了,罗平主任下午在医院见到小北京的父亲时,虽然没有立刻判断出他得的是什么病症,但凭经验也知道绝非一般的时令病,他当时之所以没有给他治,一来是不想再沾小北京的事,二来也怕自己一旦染手真出了问题要承担责任。现在冯伯只用一服药就解决了问题,罗平主任意识到,看来冯伯这个人还真的不能小觑。罗平主任想到这里就又有些担忧,倘若冯伯的名气越来越大,那么在医院里直接受到威胁的应该就是自己。
罗平主任当然不能眼看着自己的处境受到威胁。
几天以后的一天早晨,罗平主任就找到冯伯。当时冯伯正用一把很大的扫帚在小医院的大门口扫地。冯伯一向认为医院应该是很干净的地方,所以扫地非常仔细,总要先在地上喷洒一些清水,待水把地面洇透,再用扫帚轻轻地扫,这样地上的尘土也就不会再飞扬起来。冯伯正在埋头扫地,罗平主任走到他的身后轻轻地咳嗽了一声。
冯伯停下手,慢慢回过头来看看罗平主任。
罗平主任面无表情地说,我想问你一件事。
冯伯没有说话,仍然用眼睛看着罗平主任。
我一直感到奇怪,你究竟是在哪学的中医?
我……不懂中医。
不懂?
不懂。
你不懂中医怎么会知道苍术绿矾?
那是常用药,随便谁都会知道的。
诊脉呢?也是随便谁都知道的吗?
冯伯就不再说话了,又埋下头去继续扫地。
罗平主任上前一步说,你还没有回答我呢。
冯伯用力抡一下扫帚,朝旁边扫过去。
罗平主任忽然说,有个人你还记得吗?
谁?
张全。
冯伯慢慢放下手里的扫帚,脸色立刻难看起来。
罗平主任歪起头,眯着眼一下一下地看着冯伯。
人家张全可还记得你啊,他还让我向你问好呢。
罗平主任这样说罢,不等冯伯再说什么就转身走了。
接下来没过多久,冯伯就被上面撤掉了小医院“临时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的职务。据说有人揭发了他,说他是混进革命队伍里来的,这些年一直隐瞒了自己很严重的历史问题。我们这条街上的人听了都很奇怪,冯伯解放前才不过二十来岁,这些年又一直为小医院看大门,平时也是安分守己,他能有什么严重的历史问题呢?
冯伯的问题很快就搞清楚了。原来冯伯解放前曾在一家叫济生堂的药店里做小伙计。那时的药店还有坐堂中医,在卖药的同时也为人看病,冯伯的诊脉就是那时跟店里的坐堂医生学会的。如果冯伯一直这样在药店里当伙计,也许就没有后来的事了。但解放那年却突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当时解放军已经攻打过来,城里的国民党军队兵员吃紧,就四处抓壮丁来充数。冯伯就这样也被抓了壮丁,而且当天就被迫穿上军服上了前线。国民党军队知道冯伯是在药店做过伙计的,懂一些医学知识,就让他当了卫生兵。但冯伯这时已在心里打定主意,于是他和另一个同伴扛着担架跑到前沿阵地,一见解放军已攻打过来,就没停脚地一直跑到了解放军这边来,两人一起脱掉国民党军服换上解放军的军装,就这样又当了解放军,而且一直跟着解放了这座城市。罗平主任提到的那个张全,就是当年和冯伯一起被抓壮丁,后来又一起跑到解放军阵地上来的那个同伴。我们这条街上的人知道了此事都不得不佩服罗平主任,据说张全解放后一直在一家药店里卖药,这样一个人罗平主任居然都能找到,而且还挖来如此详尽的情况,由此看来他一定是很下了一番工夫。
但是,尽管冯伯被撤掉副组长的职务,负责调查他问题的人在了解过这些情况之后却认为问题的性质很难认定,冯伯毕竟只当了不到一天的国民党兵,而且参加解放军后又曾经数次立过战功,这样将功抵过,应该还绰绰有余,于是最后就决定对冯伯不再追究,也不再使用,仍然让他在小医院的传达室看大门。与冯伯一起被检举出来的还有另一个人,这个人就没有这样幸运了。他是小医院原来的院长,姓常。常院长的问题原本已经说清楚,虽然这些年也干过一些错事,但还够不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上面就决定对他像罗平主任一样控制使用,一边接受革命群众的大批判,一边在医院里继续接诊。但是这一次常院长又有新的问题被揭发出来,据称他过去在当院长期间,为一位老工人接诊时曾经延误过病情。那一次那个老工人是突发心脏病,在拉来小医院时刚好是常院长值班。而常院长非但没有对他及时施行救治,还以小医院的治疗手段有限为由将病人推出门去,以致让病人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机。这件事看似普通,其实却非常严重,至少是不把劳动人民的疾病放在心上,对工人阶级缺乏起码的感情。当然,如果再上纲上线地认识这件事,问题就更严重了。常院长就这样又重新被揪出来,胸前挂上一块大牌子,每天站在小医院的门口示众。而罗平主任也因为表现突出,被上面停止审查,又正式恢复了门诊医生的工作。
但是,常院长只在小医院的门口站了几天,当年的那个老工人就闻讯找上门来。老工人对医院说,当时的情况并不像揭发常院长的人说的那样,事实是,他那一次突发心脏病被送来小医院时,常院长立刻对他做了一系列及时有效的处理,如果没有常院长他就真的会出危险了,后来常院长确实让他转院,但常院长的转院决定是正确的,事后连胸科医院的医生也承认,如果他再晚转来一会儿很可能后果就更严重了。这个老工人说,他以一个老工人的名义担保,常院长那一次是救了他的命的。老工人说罢还走过去,亲手为常院长摘掉胸前的木牌子。老工人对医院的人说,常院长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问题,如果真有问题他可以负完全的责任。老工人为此还联系了一些过去曾被常院长治过病的患者来医院证明,说常院长长期以来对工作认真负责,广大患者对他的评价也都很好。这样一来事情就发生了根本的逆转。常院长由于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肯定,不仅解除了一切问题,还很快被结合进医院的“临时领导小组”。
据说常院长被结合进领导小组以后,曾找过两个人谈话,一个是冯伯,另一个就是罗平主任。常院长是来传达室找冯伯的。他对冯伯说,你的事情上面已经彻底搞清楚,不存在什么问题,更何况你的家庭出身很好,所以不要有任何顾虑,更不要有思想包袱。常院长这样来找冯伯谈话,是想让冯伯继续出来工作。常院长对冯伯说,医院这些年对冯伯的为人还是很了解的,虽然是在传达室看大门,但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而且还懂一些中医,曾为不少人治过病,像这样的人才在小医院是很难找的。但冯伯听了却只是笑笑,说这段时间已经真正感觉到了,自己只能是看大门的料,或者胡乱给人家看一看病还可以,别的事就实在干不了了。常院长听了拍一拍冯伯的肩膀,说你再考虑一下吧,先不要把话说死。
常院长找罗平主任谈话就不是这样的态度了。
常院长在一天上午派人去把罗平主任找来自己的办公室,对他说,你以后不要再搞一些七七八八的事情了,还是多想一想自己的问题吧。常院长问罗平主任,你明白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吗?罗平主任点点头,又摇摇头,张了张嘴却没有说出话来。常院长冷冷一笑说,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再把心思放到别人的身上,这样不仅没什么好处,还会给你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常院长接着又说,这几天我把有关你的材料又仔细看了一遍,发现还有很多问题没搞清楚,比如你那个在台湾的父亲是通过香港的一个老朋友跟你叔叔联系的,那么你跟那个香港人有没有过联系?如果没有,你又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再有,你跟你那个叔叔有过很多书信往来,你们之间又是怎么回事呢?罗平主任听了立刻想说什么。常院长马上摆摆手说,你不用再说了,要我看你的事远没有这样简单,还须进一步审查,这样吧,你先写一份详细的交待材料,不过我警告你,不要避重就轻,最好把所有的事都如实交待出来。常院长这样对罗平主任说罢,做了一个手势,示意他可以走了。罗平主任就转身朝门外走去,走到门口时,常院长又在他身后说,你这段时间就不要再接门诊了,先在家里写交待材料吧。
罗平主任并没有在家里安心写交待材料。
罗平主任意识到,这时还有比写交待材料更重要的事情。好在这段时间不用去医院上班,于是他就又跑去郊区农村看那个乡下女人。这时那个女人的病情已经日益加重,肚子里的那块肿物不知发生了什么变化,经常会引起剧烈腹痛。罗平主任去过几次,那女人一直不肯见他,村里人也都对他很冷淡。那个村子叫西于庄,几乎一个村庄的人都有亲缘关系,大家知道罗平主任跟那个女人的事,所以就都对他充满敌意。后来罗平主任终于见到了那个女人,那女人就直截了当对他说,你以后不要来了。罗平主任立刻显得很惊讶,问为什么。那女人说不为什么。罗平主任说,可是,你是我的妻子呀!那女人淡淡一笑说,你现在才承认我是你的妻子吗?罗平主任说当然承认,这是事实我怎么能不承认呢。那女人沉了一下又对他说,你真的不要再来了,我这样说也是为你好。罗平主任听了这句话并没有真正明白,他以为那女人只是在警告自己,如果再来,西于庄的人可能会对自己动粗。事后罗平主任才知道,其实这女人对他说的只是半句话,那后半句因为是难言之隐,所以才没有说出来。但是,当时罗平主任还并不死心,坚持要让那女人跟他一起回去,他说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他都不在乎,他一定要把那女人带回城里去。他还耐心地劝她说,就算她不肯回去,到城里检查一下,看一看这肚子里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总可以吧?那女人对他说,你还是自己回去吧,我这样说真的是为你好。但罗平主任的态度却比这女人更坚决,他说如果你不跟我回去,我就不走了。这女人这些年虽然从没有跟罗平主任一起生活,却很了解他,她知道罗平主任这样坚持要接她回去,一定是又出了什么事,至少是处境又艰难起来,于是故意问,你非要我去你那里,究竟为什么?罗平主任说,就是为了给你彻底检查一下身体,你现在病成这样,怎么能再拖下去呢?只为这个吗?当然只为这个。可是,这女人问,我这病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过去为什么没有想起让我去检查呢?罗平主任说你过去的病情还没有这样严重。罗平主任又说,我不是吓唬你,根据我的经验,你肚子里的这个东西很可能是一个大问题。这女人一听就笑了,说你现在才告诉我有大问题,如果真有问题是不是晚了一点?
接着又问,我去城里看病,晚上住在哪呢?
罗平主任立刻睁大眼说,当然是住在家里。
住在你的家里吗?
不,是咱的家里。
你现在承认,那里也是我的家了?
那里本来就是你的家啊。
乡下女人又想了一下,摇头叹息一声说,还是算了吧。
罗平主任问为什么。
这女人说,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不,罗平主任立刻说,应该还不晚。
这女人苦笑一下说,有些事……你还不知道。
罗平主任说,你没有告诉我,我当然不知道。
这女人又想了一下,最后才点点头说,好吧。
罗平主任是在一天傍晚将那个乡下女人接回来的。
让罗平主任没想到的是,他们还没到家就出了事。
这时已是夏季,天气有些热起来,街上的人们吃过晚饭都出来坐在街边闲聊。罗平主任就是在这时带着那个乡下女人回来的。他来到人们面前指着这女人介绍说,这是他的妻子,姓于,叫于翠莲,平时由于工作忙一直住在郊区的西于庄。又说,她的家庭出身是正宗贫农,所以在村里担任贫协主席。那女人淡淡笑一下,为他纠正说,不是贫协主席,是妇女主任。罗平主任说总之是村干部,“红五类”家庭,当年她爷爷打过游击,她父亲还参加过土改呢。罗平主任在说这些话时声音很大,底气也很足,似乎是想让一条街的人都听到。他向人们做过介绍之后,就很恩爱地扶着这女人朝家里走去。这时人们才发现,这女人的气色很难看,走路的样子也有些迟缓,而且每走一步都要微微皱一下眉,好像很痛苦的样子。就在她走过街角时,突然伸手扶住一棵树站住了,头上的汗也滴滴答答地流下来。人们一见立刻围过来,问她怎么回事。这女人只是摇摇头,又摆摆手,却已经说不出话来。立刻有人搬来一个小木凳,让她坐。罗平主任扶着她慢慢坐稳,然后才说,老毛病了,已经两三年,这一次接她来城里就是看病的。有人在一旁说,你罗平主任的家里人有病还用去医院,自己在家里就可以看了。也有人说,医不治己么,真有了病还是得去医院。又有人建议说,街上的冯伯最能治这些疑难杂症,不如让他给看一看。罗平主任听了摇摇头,笑一笑,似乎想说什么,但话到嘴边又改口道,治病的事,还是应该……去正规的医院。这时忽然有人说,唉,那不是冯伯回来了?人们抬头一看,就见冯伯和小北京正远远地朝这边走过来。冯伯拉着一辆平板车,小北京跟在后面用力推着,看上去齐心合力的样子。
冯伯在这个下午是去帮小北京买煤。我们这条街上的人每到夏季都是在院子里做饭,要点煤球炉子,所以就要存储大量的煤球。但小北京一个人搬不动煤筐,平时就只能用篮子去煤店买,这样遇到阴天下雨不能出门,也就只好不开火做饭。冯伯知道了此事,就在这个下午利用休息时间去帮小北京买煤。这时小北京已经和冯伯很默契,所以也就不再客气,于是两个人找了一辆平板车,就一起去了煤店。冯伯虽然已是四十来岁的人,身上仍还很有气力,一百斤重的煤筐一个人就能很轻松地搬起来。小北京原想多买一些,冯伯说不用,买多了存放起来很占地方,又说,以后有我,买煤还用发愁么?小北京听了脸一红就低头笑了。冯伯在这个下午和小北京一起拉着煤车回到我们这条街上,远远地看到街边有一群人围着一个女人。这时小北京已经看清楚了,罗平主任也在那里,那个坐在小木凳上的显然是他在乡下的女人。于是就对冯伯说,你不要过去。冯伯这时也已看清了,就说,那女人好像有什么事,是不是病了?小北京说,别管什么事你也不要过去,你忘记罗平是怎样对待你了?如果不是他揭发检举,你会被撤职吗?冯伯说那件事已经过去了,再说跟这女人也没关系。冯伯说着就放下车,先去街边的水龙头洗了一下手,然后朝人群这边走过来。
人们一见冯伯过来,立刻都给他让开一条路。
冯伯走到这女人面前,问她哪里不舒服。
这女人皱着眉说,肚子痛。
多长时间了?
有,两年了。
一直痛?
一阵一阵的,痛起来就站不住。
冯伯朝站在旁边的罗平主任看一眼,发现他也正在看着自己,于是迟疑了一下,但还是伸出手,按住这女人的脉口摸了一阵,又摸了一阵,忽然,冯伯看看这女人,似乎想问什么,但只是张张嘴,没说话就站起来。这时站在一旁半天没有说话的罗平主任问冯伯,你看她是什么病?冯伯看一眼那女人,又看了看罗平主任说,说不好。冯伯这样说罢就转身准备走了。罗平主任却立刻上前拦住他说,你先不要走,你刚才那样认真地给她摸了脉象,怎么会摸不出她是什么病呢?接着又眨眨眼说,你还是仔细给她看一看吧,我这次接她来城里,也是想让你给诊断一下究竟是什么病呢。这时站在旁边的人们都已经看出来,罗平主任这样说是想故意难为冯伯。罗平主任这样做显然就有些不厚道了,不管怎样说,冯伯毕竟是一番好意,就算没有看出是什么病,罗平主任也不该用这样的态度刁难冯伯。但冯伯并没有说话,只是又很认真地看了看罗平主任。罗平主任微微一笑又说,街上的人刚才还在说,你平时看疑难杂症最有经验,你就再给她看一看吧。冯伯又沉了一下,然后说,你一定要我给她看吗?罗平主任说,你如果能看的话,当然,如果……那就算了。
好吧,冯伯点点头,说,你先把她送回家去吧。
罗平主任说,她现在不方便走,就在这里看吧。
冯伯又朝这女人看一眼,对罗平主任说,我劝你,最好还是让她回去。
罗平主任却似乎打定了主意,说没关系,就在街上吧,这里空气也好。
冯伯问,你,真的一定要在这里?
罗平主任说是啊,就在这里。
冯伯没再说话,又蹲下身去为这女人细细地摸了一下脉象,然后说,你肚子里有东西。
这女人点点头,艰难地说是,是个瘤子。
冯伯说,应该不是瘤子。
不是……瘤子?
你两年前,生过一场病?
这女人迟疑了一下,是……生过一场病。
冯伯又问,你当时,正有身孕?
这女人的脸色立刻变了,先是飞快地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罗平主任,然后死死盯住冯伯,沉默了一下才静静地说,没有,这怎么可能。
冯伯说,你可要说实话。
这女人说,是实话,没有。
冯伯说,你两年前不仅怀孕,后来还流产了。
这时罗平主任突然在一旁大笑起来。街上的人们都知道,这几年罗平主任一直没有跟这女人在一起,所以这女人也就不可能怀孕,更不可能流产。但是,罗平主任只笑了几声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突然就不再笑了,只是瞪大两眼看着这女人。
冯伯又对这女人说,你的肚子里不是瘤子,是一个死胎,两年前你怀的是双胞胎,后来流产你以为就没事了,但其实出来的只是一个,当时因为流血太多,那另一个才没有一起出来,于是也就一直留到了现在。这时那女人的脸色已经苍白起来,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冯伯又说,我给你开一剂方子,吃不吃在你。旁边立刻有人找来纸和笔。冯伯就蹲在地上写了一个方子交给这女人,然后又叮嘱说,药引是两种东西,一是早晨梳头时拢下的乱发一团,烧成灰,二是两头尖一钱半,先用酒泡了再用纱布包起来与药一起煎。他这样说罢又回过头去,才发现罗平主任已经拨开人群跌跌撞撞地走了。
事后我才知道,冯伯所说的药引两头尖,其实就是老鼠屎。
冯伯说,据古书上说,以至秽至浊之物,走下焦秽浊之处。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街上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据说那女人吃了冯伯开的药,几天以后竟然真的排出一个死胎。这死胎已经变黑,干硬,看上去就像是一块树根。这女人没向罗平主任做任何解释,当天下午就收拾好自己回乡下去了。
罗平主任是在那一年秋后死的。
在罗平主任临死的前几天,常院长曾代表院方找罗平主任谈过一次话。这时小医院已经成立起革命委员会,常院长担任革委会的副主任。常副主任对罗平主任说,最近上级决定,要将一批像罗平主任这样的人送去农村劳动改造,医院革委会考虑到罗平主任的妻子就在市郊的西于庄,就决定让他去那里,这样便于改造,生活也方便。医院革委会的这个决定对罗平主任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他的妻子自从那一次来城里看病,回去之后罗平主任就再也没去找过她。罗平主任直到这时才真正明白了那个女人当初对自己说那番话的含意。他很清楚,西于庄的人对自己充满敌意,甚至是仇视,如果自己去了那里一定不会有好结果的。
没有人注意到罗平主任一连几天没在街上露面。最先发现罗平主任尸体的是小北京。一天早晨小北京偶然从罗平主任家的门前经过,突然闻到一股很奇怪的气味。她扭头朝罗平主任家的门窗看去。罗平主任家的门窗上仍然没有安装玻璃,还糊着厚厚的白纸。这时她发现,那些白纸上已经落满一层苍蝇,那股难闻的气味也正是从屋里飘散出来的。于是她走上前去,用手指捅破一张窗纸朝屋里看了看,才发现罗平主任躺在床上,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了。据说罗平主任死前曾以胃不舒服为由,去医院的中药房拿过一些叫青藤香的药材。事后冯伯去现场看过。据冯伯说,从罗平主任吃剩下的药渣看,他拿回来的并不是青藤香,而是一种叫雪上一支蒿的中药。这种中药学名叫乌头碱,从表面看去,形状和颜色都与青藤香很难分辨,但却是外用药,专治风湿或迭瓦癣一类疾病,如果水煎内服有很强的毒性。
冯伯为此感到很内疚。他对我说,如果他事先发现,也就不会有这样的事了。
2008年3月15日写于天津木华榭
4月15日改毕
责任编辑 洪清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