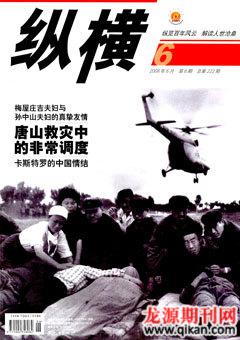一缕清香,从历史深处走来
张振群
报界名宿张友鸾与文学巨匠郁达夫,早在五四时期,就结成了文学友谊。他们富于戏剧性的相识和相互诚挚的友情,一直以来鲜为人知。
一个戏剧性镜头
张友鸾乃李大钊的学生,邵飘萍的高足,是我国新闻界出道很早的老报人。年轻时在邵飘萍主办的《京报》主编《文学周刊》,李大钊曾委任他为《国民晚报》社长。先后在14家报社工作,与张恨水、张慧剑并称“新闻界三张”,驰骋报坛,久负盛誉。
张友鸾1904年生于安庆一个书香门第,父亲张亮孝是安庆法政专门学校国文教师。1921年,革命风云激荡,张友鸾在安徽省立一中就读,受五四运动影响,思想十分活跃。当时他才17岁,就被安庆学联选为代表参与筹备成立省学联,并当选为宣传部部长。同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学运中的骨干,也是酷爱文学的青年,已在《申报·自由谈》、《时事新报·学灯》发表文章。
这年深秋,为配合新文化运动宣传,学生会宣传部办起贩书部,推销进步书籍,张友鸾为学联“头面人物”,自是带头推销。这天,和几个同学在工业专门学校门前卖书,却偏偏遇上了阴雨天。他正犯愁,迎面来了一位顾客,30来岁,上前问张友鸾:“有《觉悟》合订本吗?”张友鸾摇头。那人又问:“有郭沫若的《女神》吗?”张友鸾又摇头。但心里一阵欢喜,他知道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都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领袖,赫赫名家,当时著名的新文学团体“创造社”就是他们发起的。张友鸾读过《女神》,这是郭沫若刚出版并引起轰动的诗集。无疑,这是一位真正的读者!于是,他拿起一本《沉沦》,向这位推荐:“先生,郁达夫的《沉沦》也是刚出版的,我们都看过,非常好!”那人没有回答。张友鸾继续推荐:“先生,《沉沦》实在是好,郁达夫取材惊人,大胆描写,震撼心灵,先生应该买一本看看。而且他文笔优美……”不料这人打断他的话,畅然而笑:“我就是郁达夫。”
张友鸾呆了,一时竟说不出话来。不怪,郁达夫是新文学创始人之一,是大胆向封建道德挑战的勇士,是他仰慕以深的文学家,他刚读过《沉沦》,佩服得五体投地。万没想到他所崇拜的郁达夫,此刻竟站在面前和自己对话!
原来,郁达夫于这年10月刚到安庆,他是应安庆法政专门学校的邀请来教授英文的。张友鸾兴奋地说:“巧极了,先生和家父还是同事哩!”郁达夫也高兴起来,两人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张友鸾问道:“先生住哪里?”
“就住学生宿舍。”
酷爱文学的张友鸾又一阵欢喜,立即闪出登门求教之想。法政专门学校在安庆北郊的风景胜地菱湖旁边,离张友鸾家四方城不远。“菱湖夜月”久负盛名,此时正是“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季节,晚上月光绮丽,倩女们泛舟采菱,歌声阵阵。郁达夫住的校舍就在湖畔,常有“得天独厚开盈尺,与月同园到十分”的诗意。
张友鸾第一次登门求教,就受到郁达夫的热情接待,有问必答,可亲可敬。由是,张友鸾到菱湖亲炙,来得更勤了。
一段飘香的友情
作为教师和作家,郁达夫一直关爱青年学生,尤其关爱有思想有抱负的文学青年。他见张友鸾思想进步,又是学运骨干,热爱文学,非常乐意当他的“业余”老师。几次交谈请益,张友鸾得知郁达夫不过25岁,比自己只大8岁,心中赞叹写出惊世作品的文学名家,竟如此年轻!年龄相近,使得二人更加投合。张友鸾总是身迷心醉地怀情而来,得益而归。
当张友鸾发现郁达夫有“玉壶买春”的雅号之后,竟邀请郁达夫到家里做客浅饮。郁达夫知道他是真诚邀约,绝非俗气,欣然答应。
张友鸾高兴地告诉母亲:“我今天要请一位客人来家里喝酒……”
母亲诧异,埋怨道:“你正求学,怎好无端请人来家喝酒,岂不荒唐!”
“你晓得他是哪个啊!他是著名的文学家郁达夫先生,我的老师啊!”
母亲蒋汝娴,本是思想开放、知书达理的贤妻良母,听说是郁达夫先生,这是儿子难求的老师,难得的机遇!二话不说,高兴地下厨做菜。
张友鸾和郁达夫边饮酒、边聊天。郁达夫洋洋洒洒纵谈古今,张友鸾和老师畅谈当前文学、文坛作家。谈得较多的是郭沫若及其《女神》,张友鸾对《女神》体现出的“五四”精神和爱国热情,极为颂扬;郁达夫尤其赞赏那不是寂灭而是预示新中国新世界诞生的《凤凰涅柴》,竖起大拇指说:“沫若将有大的成就!”
张友鸾插话:“先生创作思想也了不起!”
“不不,我是—个庸人。”
两人越谈越投机,直到酒已满足,杯已见底,仍言犹未尽,难舍难分。此后,张友鸾时常请郁达夫到家中做客对饮,登城墙散步。这是他们一段诚挚快意的交往,一段飘香的友情。
一个“创造社”门口的伙计
1922年,张友鸾考入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此时郁达夫也离开安庆去了上海。张友鸾学新闻并未放弃对文学的追求,他与同学周灵钧、黄近青等组织了“星星文学社”,研究文学并发表文章。这年11月30日,适逢清废帝溥仪迎亲,人们涌到景山东街看热闹,引起张友鸾写小说的念头。酝酿构思,于年底写成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坟墓》。内容写两个青年大学生,因婚礼而引发“结婚是否为恋爱的坟墓”,的一场争论。写好后他就想到请郁达夫指教,将稿子寄到上海。寄出后一个多月不见回信,但翌年二月,竟出乎意料发表在《创造》季刊第一卷第四号上。
原来,郁达夫收到小说稿后,很认真地读了,并请郭沫若看过,都以为“这只有青年人才写得出来”。郁达夫有心提携这位文坛新秀,立即将稿子转给主编《创造》季刊的成仿吾,成收到此稿马上编发。《创造》季刊是当时一流的文学刊物:多是发表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名家作品。《坟墓》的发表,使张友鸾在文学殿堂崭露头角,受到极大鼓舞。
郁达夫、成仿吾在《中华新报》又办起一个副刊叫《创造日》。撰稿人除了创造社成员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郑伯奇等著名作家,还有一些文学青年,张友鸾即是其中突出者。此时的张友鸾目光敏锐,思想敏捷,不时激发强烈的创作冲动。
这是他勤奋写作的青春时期,作品大多发表在创造社的刊物上,且形式多样,--有杂文短评;有记叙散文,有抒情散文诗,还有寓言。他几乎包揽了《创造目》的“随感录”专栏。1927年3月出版的仅3月份一个月的《创造日汇刊》单行本,收入的张友鸾的“随感录”就有《吃饭》等5篇之多。
此时他与郁达夫的个人关系已发展成与创造社的关系了。他曾幽默地说他是“站在‘创造社门口的小伙计”。
一个骸骨迷恋的心愿
人生的巧合无时不有。这年秋天郁达夫到了北京。因他在日本留学时学的是经济学,应北大的邀请来做统计学教授,住在他哥哥曼陀先生的住所。这对张友鸾来说是特大的喜讯,他又能找郁达夫请益求教了。他对郁达夫早就有了的那种“骸骨的迷恋”越聚越浓,忽然闪出一个心愿:如果郁达夫能到平民大学来教课,那该多好啊!
这天,他找到平大一位姓徐的教务长,直接提出请
郁达夫来平大兼课的建议,教务长难以答复。可是不久,校方竟采纳了他的建议,其中原委,他后来才知道:因张友鸾在平大与左笑鸿、吴隼都是高才生,被称作“平大三鸟”(其名皆含鸟);他既是邵飘萍、李大钊器重的学生,又是学生会的成员之一,可谓“头面人物”。校方有时也向学生会征求意见,何况郁达夫是知名作家,所以校方很快就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他与郁达夫在平大开始了正式的师生关系。
一则滚烫的座右铭
1924年,张友鸾在邵飘萍办的《京报》开辟并主编了《文学周刊》,他向郁达夫求稿,郁达夫积极支持了他。郁达夫借用张友鸾那篇《吃饭》一文中“骸骨的迷恋”一词作标题,写了著名的散文《骸骨迷恋者的独语》,内容是讲新诗与旧诗、新文学与国故的关系,议论精辟,刊登在《文学周刊》第四期(后来郁达夫将它收入《奇零集》)。当时为《文学周刊》撰稿的也多是名家,如鲁迅、周作人、徐志摩、许地山等,张友鸾也成为文坛俊彦,声名鹊起。
1925年他在平大尚待结业,就被成舍我聘请到《世界日报》社,正式开始他立志献身的新闻生涯。一年后就当了该报总编辑,是同时期中最年轻的总编。两年后,接替刘半农主编《世界日报》副刊,他又想到了郁达夫,但郁达夫已离开北京到上海,与张友鸾两年多未通信。张友鸾写信给上海的同学周灵钧,托他持信找到郁达夫求稿。哪知此时的郁达夫很忙,一是忙于编务,《洪水》半月刊、《创造》月刊都由他一人编辑,一个月要做五六万字的稿子。二是正和王映霞热恋,无暇写稿。但是他对张友鸾的友谊仍没褪色,郑重地写了回信,开头就说:“友鸾同学弟:自从前年分别两年多,差不多信息不通,我也东南奔走,一无暇日,所以弄得来执笔的兴致都消失尽了……在信中他认真地对副刊说了三条意见,大意是:一、反对文坛的派系斗争,不要卷入这种争斗之中;二、要扶持新出现的青年作家;三、不要被恶势力吓倒、屈服,要登些富有革命精神的文学作品。”
这是一封非常珍贵的信。在《郁达夫书信集》里所收1927年全年的信件,给王映霞的信有50封之多,只有唯一的一封不是,那就是给张友鸾的这封信。
张友鸾似乎看到了郁达夫那颗滚烫的心,在关爱、支持着他。所以当他接手副刊的第二天,就将此信发表了,标题是《海大鱼——副刊编辑室座右铭》,在题下并作说明:“……他的意思很有道理,以后我们的方针差不多要依此而行。”
其实,这也是张友鸾的座右铭,它砥砺张友鸾从事新闻工作,伸张正义,坚持真理,敢为民众立言。因此,他被誉为“新闻奇才,办报全才”。
张友鸾晚年游故乡安庆,寻访四方城旧居,曾对我提及与郁达夫的真诚友谊。如今道来,宛如一缕清香,从历史深处走来。
责任编辑王文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