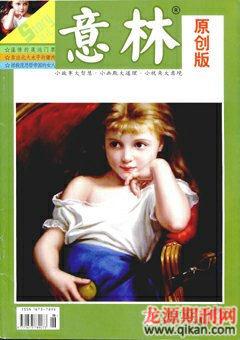魂归戈壁敦煌
末 茉
1938年,张大千在杨宛君的帮助下经历千难万险,逃离了日本人的魔掌,离开北京,由上海赴香港再转道重庆来到了成都灌县,坐滑竿到青城山,租下“上清宫”后院。隐身在参天古树、峰峦叠嶂之中,牵着杨宛君纤细白嫩的小手,面对滔滔东去的岷江,张大千感慨万千。
1935年,誉满京华画界的张大千在京城中山公园举办画展,邂逅活泼清纯的京韵大鼓艺人杨宛君,一见钟情。禀告父母获得同意后,那年的秋天张大千终于迎娶了这辈子唯一一位自己主动追求的女子。而正是这位美丽动人、温文尔雅的小女子,陪自己东渡日本回顾异国风情,也是这位女子机灵地与日本人周旋,镇定自若,东奔西走,把自己成功地营救了出来。虽然她的年龄比自己小了十七岁,却无时无刻不把自己宠得像个孩子。张大千将杨宛君视为上天赐予的厚礼,百般珍爱。
张大千提笔给远在上海沦陷区的红颜知己李秋君写信。诉述了牵挂和担忧,谈到了目前生活和计划,特别提到的是他有意去敦煌戈壁,寻找古文化的踪迹。
这个萦绕多年的梦想在得到了李秋君的鼓励和支持下,张大千雄心万丈,与杨宛君一起立刻为去敦煌着手详细周密的准备工作。
1941年,张大千一行经历了三个月跋涉八千里来到了敦煌莫高窟。杨宛君作为这队人马中的唯一一位女性伴随张大千登上了千佛洞。
她把家安顿在庙里,庙前有条小河,盐碱地上的每一滴水都是那样的珍贵,宛君忍痛剪去了一头长发。夏天,用几张席子在河床里围成“密室”洗澡。冬天,把河里的冰一块一块敲下来,化开备用。罐头吃完了,吃咸菜。为了让丈夫保证身体,补充营养,她从兰州买来菜种,种在碱地上,担河水一勺一勺浇灌,细心栽培,看到先生吃上了新鲜的萝卜白菜,杨宛君是如此的欣喜。
望着浑身上下沾满灰尘,夜以继日给每个洞逐一编号,架梯举灯,在高壁上奋笔摹画的先生,作为一个普通妇人,她不可能预见到这次敦煌之行对张大千的一生将起到什么样的影响,更想不到由此将奠定了他在中国绘画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她只知道毫无怨言地付出和别无选择地隐忍。
张大千先生自敦煌回到成都后,举办的《西行游记画展》,震动了整个画坛,整理出版的《敦煌临摹白描画》三集一直为世人视为收藏珍宝。他的画风由此逐渐接近敦煌壁画的风格。从此他的山水、花鸟、人物画,独具一格,出神入化,无与伦比,奠定了他成为一代绘画大师的基础。
然而,在这辉煌的背后,杨宛君却在张大千的身边悄然隐退了。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杨宛君没有决绝,没有毅然地离开,他们偶有简短的通信,张大千对她很客气,但缺少了曾经卿卿我我的甜蜜,往事如风,仿佛云淡风轻。
新中国成立后,杨宛君一边从报纸上收集张大千的消息,一边走出家门寻找工作的机会养活自己,身患多种疾病的她到了一贫如洗的晚年,也不肯用张大千的字画去换取钱财,而是与寡居的堂姐一道去绢花厂取来几千张纸,在残灯下绘出五颜六色的花朵谋取微薄的生活费。
而远在海湾那边的亲人,走时健壮潇洒,此时亦临暮迟迟,他闭口绝少提起“杨宛君”这个名字,或许是顾及身边的夫人,或许是不肯触痛心中的怀念。
台湾报纸在大千先生死后公布了他的亲笔遗嘱,遗嘱写道:“立遗嘱人张爱(字大千)缘余年届八十,深念渥承天麻,得毕生浸润于书画,勉有成就,感祷不已。惜余不治生产,积蓄甚微,光阴荏苒,宣立遗嘱以示后人……余自作之书画全部分为十六份……”其中十五份给他的妻子徐雯波及在海峡两岸的十四位子女。還有一份,这位在绘画艺术上被称为“五百年来一大千”的举世闻名的大画家,在遗赠部分的第一条特别注明:“上开余自作画之十六分之一”赠杨宛君。
所有时光淡尽,游子魂归戈壁敦煌,或许梦见了那位羸弱的女子在大漠里迎风向自己奔来?而杨宛君临死也梦想着与她的大千能够再见上一面。
世间有多少情感埋在心底,如尘封的琴,那弦不可触,一触就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