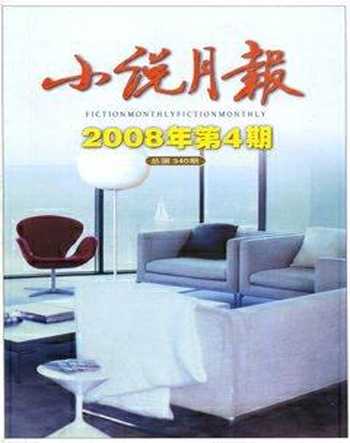冬闲时节
赵二憨醒来时天刚放亮,透过玻璃射入的光线有点灰蒙蒙的样子,身子在被窝里拱了拱没有任何回应,这才发现妻子早已下了床。赵二憨一转身,干脆把妻子原来占用的半拉被子也拖了过来,厚厚地盖在自己身上,然后又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等他再次醒来,屋里细小的灰尘在几束阳光的照射下急速地翻转,裹在被子里的他已经有了几分燥热。赵二憨一边伸出胳膊枕在头下,一边看着天花板上的菱形吊灯出神,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这大冬闲的,今天做些啥呢?
赵二憨终于想起来了,这天是冬至过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妻子昨晚对他说一大早就去邻村看望偷生二胎的表妹。赵二憨磨磨蹭蹭地起了床,然后走到房前一棵榆树旁洒了一通热尿,有些夸张地抖了抖手里的家伙,看看院里没动静,他一边费力地拉上了裤子拉链,一边走近儿子大宝的房门。门没关,可大宝也不在家。赵二憨也不知道儿子究竟野到哪里去了。赵二憨思忖着,这小子自打上了初一就渐渐迷恋上网,洙水镇中学附近新开了三家网吧,他如果去那鬼地方是不肯告诉老子的。
赵二憨草草地刷牙洗脸,用湿手往头发上随便捋了几下,照照镜子看起来倒也精神了许多,然后推出那辆破摩托,一溜烟似的来到了洙水镇。空腹出来,肚子里叽里咕噜地一个劲儿乱响,路过洙水镇酒家时就不假思索地走进店里。吧台里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身材匀称,前胸丰满,模样可人,赵二憨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赵二憨熟络劁猪骟羊的手艺,走乡串户时经常在洙水酒家歇息歇息,待到冬闲时活计少了,有时也在这里和一些熟人搓搓麻将,玩玩牌九。赵二憨不认识这位新来的姑娘,就怔怔地多看了几眼。姑娘正在用粉笔往黑板上写字,字体很工整,赵二憨凑近看去,写的是“今日菜谱”。
大厅里有一条茶几,两位镇计生办的工作人员正下象棋,两旁围了五六个观战的闲人。赵二憨仔细看了看,有熟悉的,也有不认识的,便掏出一包大鸡烟左右让了让。老板娘苗小凤从里间出来,朝赵二憨努了努嘴,说:“二憨,来啦!”
“来啦!”赵二憨打趣道,“这男人啊真是没出息,这不,人家一空下来就想来看看你!”
“你空了倒是好,一忙准没好事。”苗小凤笑了笑说,“不是劁猪,就是骟羊,这些牲灵碍你啥事啦?”
“你别冤枉好人啦,不是我谝能,我可是跟计生办的差事差不多呀!”赵二憨一下子来了精神气,“你想啊,我整天也忙着做男女扎,对不对?”
酒店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忍不住笑了。苗小凤更是笑得前仰后合,“男女扎——是是是——男女扎,真有意思!”酒店里只有一个人没笑,没笑的就是那个赵二憨不熟悉的姑娘,姑娘不但没笑,还红了脸。赵二憨可是很久没看到会脸红的女人了。
“别看了,再看眼珠子就要掉地下了。”苗小凤白了赵二憨一眼说。
“咋,我看人家一眼,你就吃醋啦?”
“熊样!你敢胡说,看我不抽你嘴巴子?”
“呦呵,屁大的工夫你竟然变成醋坛子了。”赵二憨压低声音说,“我看见脸红的姑娘就来劲!”
“别胡闹!瞧你……我闺女丽丽!”苗小凤脸上写满了愠色。
“我哪认识呀?”赵二憨说,“又不是咱俩的劳动成果。”
苗小凤就势在赵二憨的耳朵上拧了一把,疼得赵二憨一个劲儿直吸凉气,酒店里顿时又笑成一团。
苗小凤与赵二憨其实很熟悉,她的丈夫常年在东北的建筑工地上开吊车,几个不太安分的男人没少打她的主意,这其中就包括赵二憨,可大家却是过过嘴瘾,任何人沾不到一点便宜。
赵二憨说:“你就这法疼爱闺女?咋不让孩子上大学呀?”
“上大学?她是那块料?”苗小凤自我解嘲地说,“这不,今年技校毕业了,就先在我这里打个下手吧,反正没在城里找着个像样的男人。”
丽丽不乐意了,白了一眼苗小凤,说:“妈,你净瞎扯,人家是没找着个像样的工作。”
赵二憨学着某电视剧里的台词说:“一样的,一样的,一样一样一样的。”
“什么一样的?差大了,你们懂啥?”
“我不懂?我什么不懂呀?”赵二憨故意一撇嘴说,“这年头啊,可是有了好工作就有了好男人,有了好男人就有了好工作,对不对?”
酒店里又是笑声一片。一个端碗喝羊肉汤的中年人扑哧一笑,忍不住把含在嘴里的一口汤喷了出来,忙着四处找餐巾纸,丽丽满脸绯红,不敢再多说一句话。
“老样子,肉丝面、半份老醋花生、半份凉拌猪耳、二两半一瓶的洙水老窖。”赵二憨找了个位子坐下,对苗小凤说。
苗小凤就冲着里面喊:“一碗肉丝面、半份老醋花生米、半份凉拌猪耳、小瓶的洙水老窖酒。”
一位打工妹很快把酒、菜、饭端了上来,赵二憨叫住那姑娘:“哎哎,拿双卫生筷!”那个打工妹来了些时日,可赵二憨还是记不住她的名字,一直让他纳闷的是这姑娘虽说身材一般,但是一张好看的瓜子脸上镶嵌着两个浅浅的酒窝和一双美丽的大眼睛!
苗小凤看了看有点走神的赵二憨,故意岔开话题,问:“二憨,你家还剩几亩地?”
“三亩半,一季麦一季棉,吃穿够用剩点钱。”
“别整天恣得不行,怕是过不多久就给你开发了?”
“开发?开发个鸟!”赵二憨气不打一处来地说,“没听人说呀,乡镇干部瞎折腾,招商引资全是空。”
大眼睛给赵二憨递来一双卫生筷,赵二憨很有气派地撕开,一下插进盘子里,一阵风扫残云一般,不大会儿酒菜见了底,一碗肉丝面也进了肚,赵二憨顿时红光满面。
这时,外面响起了汽车喇叭声,计生办的人撂下那盘没有下完的棋转身就走。一个看棋的人说,不知他们又去逮哪村的超生户去了。大家也马上散了去,茶几上是凌乱的象棋残局,茶几下面是一地的烟头。苗小凤冲里面喊:“快收拾收拾盘子碗!”一会儿酒店里空了下来,苗小凤坐在赵二憨对面,数落着那个大眼睛,说这姑娘又馋又懒,还会使手段让男人们老惦记着。大眼睛似乎没有听到女老板的数落,闷不作声地收拾场面。
苗小凤尽管不停地吩咐大眼睛忙里忙外,但抛去的还是白眼珠子。赵二憨想,或许是她们没有缘分,无论如何这姑娘是不能讨老板娘喜欢的。于是,赵二憨对苗小凤说,“我听老婆说,他们那个厂子缺人,你要是真的不喜欢她,就干脆让她去那里好了,省得天天怄气。”
这时,丽丽却显得很有兴趣的样子,问:“哪里呀?我去行不?”可是,话音未落,苗小凤很快泼了冷水,说:“洙水人发厂,你干得了?白天夜里三班倒,你能吃这个苦?”
一席话说得丽丽很是无趣。苗小凤这才对赵二憨说:“闺女在县城技校毕业,一直没找到工作。”
赵二憨有些没话找话:“现在的年轻人啊……”话到这里并没有想出合适的下文,但是苗小凤似乎很懂的样子,点了点头接过话茬说:“就是就是,吃不了苦受不了罪,哪像你老婆啊,在那里干了七八年,已經习惯了。”
赵二憨打了一个饱嗝,很是坦然地舒了一口气说:“咱老婆现在也熬成小组长了,管着十几号人呢,就是还得跟着三班倒。”
“人发厂的效益不错吧,我记得去年春节的时候,它们还赞助了县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呢。”
“是有那么回事,今年利税六百万,全洙水镇排第一。”
“全镇第一的不是人发厂,是洙水养殖公司,光杜克、长白系列的商品猪就一万两千头呢。”
赵二憨说:“不管第一第二,人发厂不错。”
“那是那是,你老婆倒是也很能干,就是三班倒不好。”苗小凤说。
赵二憨凑近苗小凤的耳根说:“咋不好,等趁她再上夜班,我来找你,只要你给我开门……”
“去你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就你这天鹅肉,以为我真稀罕呀?”赵二憨故意逞能道,“还别说,老婆在厂里多少说话算数,你如果有熟人要到那里上班,找我帮忙就行。”
还没等苗小凤回应,酒店的电话就响了起来。苗小凤顺手拿起话筒“喂”了一声,然后对她闺女说:“丽丽,城关派出所的电话,找你的。”
丽丽一努嘴说:“就说我不在。”
苗小凤说:“你咋能这样,有啥事说啥事,还学会摆谱啦?”丽丽不太心甘地接过话筒。
赵二憨说:“你们娘俩咋啦?火气都不小。”
苗小凤叹了口气说:“这妮子心里真没数,她的一个同学追她追得很紧,他爸在县法院当执行局长,他妈做律师,这个男孩在城关派出所干合同警,你猜怎么着?人家愣说‘没电。”
“如今的孩子呀,谁的话也听不进去。”
“现在倒好,哪也没处去,整天拉着个脸,像是满世界的人都欠她钱。”
苗小凤的一个“钱”字刚脱口,赵二憨的魂儿就像被勾走一样,马上想找几个人玩玩牌九或麻将什么的。一个月前,在洙水镇屠宰场干保安的丁万能手气不好,玩牌九输了两千块,赵二憨一个人赢了八百多,丁万能早就扬言等二十五号发了工资要好好赌一把。今天刚好二十五号,丁万能该发工资了吧?不过,就他那张丧门星的脸,还能捞回来?
“二憨,想啥呢?”苗小凤看着赵二憨问。
赵二憨转过头来答道:“没想啥。看见丁万能了吗?”
“丁万能?你们不是一个村的吗?”苗小凤说,“人家都说,二憨不憨,万能不能,咋啦?你又想赢他钱了?”
赵二憨嘿嘿笑着,掏出手机对丁万能说:“万能,我有好几天看不到你啦,你忙啥呢?”
丁万能在电话里大声说:“没忙啥,可再想玩也凑不齐手啊,人家都去洙水养殖公司那儿看西洋景去了。”
“西洋景?啥西洋景?”赵二憨来了兴趣。
丁万能说:“你自己去看吧。”
赵二憨骑上摩托,一加油门就来到了洙水养殖公司门口,好几幅条幅随着氢气球的浮动迎风飘扬。赵二憨走近一看,呀!这个鬼地方什么时候搭起了五六个蒙古包似的帆布棚啊?他在那个顶大的大棚前停了下来,果然有一大群人围在出入口,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很拥挤。不远处,儿子大宝和他的几个同学也在,他们正朝另一个大棚的出入口张望,看表情是想看又不愿花钱的模样。
这时,一个把头发染得一绺黄一绺红的青年男子手持喇叭,在赵二憨靠近的大棚外大声吆喝着:“河南黑豹歌舞团的精彩演出啦——劲舞艳歌,绝对刺激,绝对开放,十块一位啦!”那个男子的一侧,一个年轻女子一边做着挑逗男人的动作,一边大声呼喊:“不看不知道,一看忘不掉!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赶快买票,赶快进场啦!”
大棚里则是急促的乐声,也不时传来众人的叫好声。一男一女一阵忽悠,十几个人连忙买票进场,进出口处开始人头攒动。
赵二憨侧目看了看进出口旁边的宣传栏,两块木板上贴着几张放大的照片,照片上有十多个穿着很暴露的女人,胸罩窄得连乳晕都没盖住,裤头小得不能完全遮住羞部,赵二憨俯下身子尽量把眼睛睁大细看,可还是觉得没有看清楚。大棚里骚动的乐声越来越大,赵二憨不禁心跳加速,这回也顾不得儿子大宝究竟在什么地方了,他在人群里挤了几下,从怀里掏出十元的钞票递给售票的。
“喂,就买一张?”
“就一张!”
赵二憨几步闯进大棚里,里面更是无序的声响,乱哄哄的震得耳朵一阵发蒙,偶尔几次粗嗓子声音倒很整齐:“脱!脱!”几个三十岁左右的中年妇女随着音乐的节奏摇晃着有些碍眼的丰乳肥臀。外面那个男人很响的声音也不时通过喇叭传来:“劲舞艳歌,绝对刺激,绝对开放,绝对超值享受,绝对精彩暴露!”原本很齐的“脱!脱!”的声音一会儿被掩盖了下去。
也就一棵烟的工夫,赵二憨感觉无趣,低着头走出了人群。他重又回到洙水酒家,倒了一杯茉莉花,和几个熟人大谈风气不好世道太差之类的话题。赵二憨也附和着别人说:“就是,女人脱衣裳有啥看头?看自家老婆不是一样吗?”另一个人骂了一句:“这帮人真缺德!大人无所谓啦,小孩看了不学坏才怪呢!”
一句话提醒了赵二憨,他二话没说骑着摩托又朝大棚那儿奔去。这会儿,各个大棚里里外外都是人。一个中不溜的大棚进出口最拥挤,喇叭里传出的声音是“脱啦,脱光啦!”赵二憨怎么也看不见儿子大宝,越是这样心里越着急,就摸出十块钱想买票进去。
售票的说:“全脱光的,二十块呢!”
“我不是为了自己看,我是找我儿子的,就十块!”
“那不行,只要进去就二十块。”售票的一点也不妥协。
“妈的,二十块就二十块!”
赵二憨进入大棚,左瞧瞧右看看,终于没有找到大宝,犹豫了一阵还是停在那里往表演台子上盯了几眼,与第一次进棚里看到的有所不同,原来的那个大棚里是几个年龄稍大的女人,这个棚子里的却是两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她们先是把横在前胸的乳罩往前拉了几下,让人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发育得不算太好的乳房的轮廓,稍后低下头把本来很小的裤头往下急急地扯下再提上,让人看了一眼女人的私处。大棚内顿时嘘声一片,两个姑娘趁势逃也似的跑向后台。看到这些,赵二憨的裆里硬了几次,弄得很不自在。待到赵二憨离开大棚时,差不多过了中午吃饭的时间,他骑着摩托想往家赶。在赵二憨经过洙水酒家时,有人叫了一声“二憨哥”,扭头看去原来是那个大眼睛。
这会儿饭店里吃饭的人大都离去,苗小凤和她女儿丽丽都不在,只有大眼睛一个人守空摊。大眼睛凑近赵二憨跟前,说:“二憨哥,你上午说的洙水人发厂的事儿,帮我问问好吗?”
“你想去?”赵二憨说。
“想去。在这里,就是累死一个月也只能挣个三百来块钱。”
“我帮你问问可以,事成了你咋谢我呀?”赵二憨有点不怀好意。
“咋谢都行。”大眼睛并没有露出一丝的胆怯。
赵二憨得寸进尺,盯着大眼睛的眼睛说:“事成了得让人家……”
大眼睛使劲瞪了赵二憨一眼,说:“你现在就好意思说三道四?事还没成呢,你猴急什么吗?”
赵二憨没再跟大眼睛过多纠缠,加大油门向家里奔去。
当天晚上,丁万能约赵二憨玩牌九,十几个人摆弄了三四个小时,赵二憨输了将近一千块。丁万能调侃道:“俗话说得好,情场得意,牌场失意。你一准去看女人光腚了?”
赵二憨说:“女人的光腚啥看头?自己家的女人还不一样?”赵二憨自认手气不好,身上的钱差不多输得精光,就抖抖衣裤回家了。他回到家里,老婆正看电视。看他回来,老婆问:“今天都干啥去啦?”赵二憨说:“跑了几个村,催了催欠账。”老婆说:“是该催催账啦,眼看春节快到了。”
赵二憨用谎话蒙混过关,心里慢慢地踏实了些,后来把大眼睛想要进厂的事跟老婆说了。老婆一听就烦:“咋了,你的相好?”
赵二憨一脸苦相,说:“哪能呢?我都这么大岁数啦。再说,谁能没难处呀,人家一个女孩子人生地不熟的,替人家帮个忙能碍多大事?”
老婆没好气地说:“我没这个能耐,帮不了。”
赵二憨说:“你好歹也算个组长,你就跟厂长说点好话嘛。”
“我们那里倒是真缺人手,可是我根本说不上话,你揽下的活你自己弄。”老婆嘟囔道,“如今当厂长的,不是贪财,就是好色,咋能说说就行?”
第二天,赵二憨应邀去外乡劁猪,路过洙水酒家吃飯的时候,看到了大眼睛,顿感无话可说。虽说吹牛不交税,但事儿八字没一撇呢,如何跟人交代呀?大眼睛并没有任何的言语,只是一脸笑模样走到赵二憨落座的地方,把他面前的桌子擦得锃亮。
赵二憨开始向别人打听洙水人发厂厂长的底细了。花了半天工夫终于弄清楚了,厂长姓徐,是一位副县长的小舅子,但他在青岛搞运输,平时并不多问厂里乱七八糟的事情,管事守摊的是徐厂长的高中同学阎在行,对外号称常务副厂长。赵二憨并不认识阎在行,不过毕竟是乡里乡亲的,转过来转过去原来也真有点沾亲带故,姓阎的是赵二憨姐夫的表哥的妹夫的战友的堂弟。赵二憨听他姐夫的表哥一说,马上有了很足的信心,决定当晚就去活动一下。赵二憨打听了阎在行的住处,原来就在洙水镇中学家属院。
妻子当值夜班,天不黑就得往人发厂里赶。赵二憨想离开家门时才想起要送点东西,但找来找去都觉得拿不出手,掏掏腰包瘪瘪的,自知已经把一张张百元大钞摔在了牌九桌上。正在他发愁的时候,兔笼里突然传来“吱”的一声叫唤。赵二憨急中生智,顺手抓了一只大个的兔子,塞在黑布包里出了家门。
赵二憨骑摩托车一会儿就到了洙水镇中学家属院,第三排第二家,很快找到了,伸手按了按门铃。一个小保姆把门打开后,直接引领他到客厅里。赵二憨这才看到,屋里烟雾腾腾,两男两女围坐在方桌旁打麻将。赵二憨去洙水人发厂找老婆时曾见过阎在行,只是没有说话的机会。赵二憨一脸笑模样,对手里正在举着“一条”的阎在行说:“阎厂长,我是……”
阎在行把一条重又放在牌桌上,说:“我认识你。你爱人不也在咱厂工作吗?”
赵二憨就说:“我不光是咱厂的男家属,我们还有点沾亲带故的关系呢,你是俺姐夫的表哥的妹夫的战友的堂弟……”
“你姐夫——你姐夫的表哥——你姐夫的表哥的……”阎在行拍拍脑瓜子说,“别这样费劲了,你干脆说啥事吧。”
“一个朋友的孩子想到咱厂上班,你看能不能……”
“进人的事要停一段时间。”阎在行扭头又问,“男孩?女孩?”
赵二憨说:“女孩,也就二十岁左右,瓜子脸,脸上有两个酒窝,眼睛大大的……”
阎在行说:“我考虑考虑再说吧,但如果进厂是要有试用期的。”
赵二憨一边应着“那是那是”,一边拿手拍拍黑提包里的兔子,说:“如今啥东西您都不稀罕了,给您带来了只活兔子,嘿嘿!”
阎在行摆摆手说:“不用不用,再说你看我这里也没法养活它,你拿回去吧。”
正在冷场的时候,坐在阎在行下手的一个中年女人说:“没法养活,干脆今晚吃了它。”另外两个人都附和着说:“不错不错。”
閻在行也认为是个好主意,就忙把保姆叫来,让她杀了兔做了吃。保姆为难地说:“我没杀过兔子,我害怕……”
赵二憨对众人说:“我来我来,我干这活最有经验。你们继续打牌就是了,一会儿就能吃上兔肉。”
阎在行一副皮笑肉不笑的模样,说:“这怎么好意思呀?”
赵二憨说:“阎厂长别见外,我又不是外人。”
阎在行说:“好吧,那就辛苦你啦!”
赵二憨拎着兔子走到屋外,这时听到屋里继续打麻将的声音——阎在行说:“幺鸡。”阎在行下手女人的声音:“你的幺鸡,哈哈,俺可是想了好久了——吃。”另一个说:“你敢吃阎厂长的幺鸡?他老婆来了打不扁你?还是等会儿吃兔肉吧。”阎在行说:“就是,我的幺鸡从不对外。”
赵二憨听了牌桌上传来的对话,也忍不住笑了。小保姆给他找来一把尖刀,赵二憨很麻利地把兔子给杀了,然后扒了皮,除去内脏,又清洗了一遍,就让保姆打开炉灶,把兔肉放进锅里。幸好阎在行厨房里葱、蒜、姜、花椒、茴香、酱油、黄酒等各种佐料一应俱全,赵二憨等水烧开了一股脑地把东西放到锅里。
客厅里不时传来大家的笑声,二憨听的是几个很有意思的下流笑话。
一个女人说:“老阎,你们洙水人发厂都是造假发的?”
阎在行说:“是啊,主要是给那些头上没毛的人盖盖顶。”
另一个男的说:“我昨天听了一个你们厂的笑话,很有意思。”
“快讲快讲。”还是阎在行下手那女人的声音。
那男的果真讲起来:“说是洙水西村有一个小女孩,因为家境困难十二三岁就到洙水人发厂上班。两周后,她突然发现自己的下体长了一撮黑色的细毛,她很害怕。她心想,这才十几天的时间,下面就长出像刷子一样的东西,再下去还了得。于是第二天就向阎厂长辞职。阎厂长一听,哈哈大笑道:‘原来这样,没什么嘛!每个人长大都会这样的,你看我也有啊!说完,当场脱了裤子给女孩看。小女孩吓得夺门而逃,她边跑边想,我才不会继续干呢,时间长了还不得像厂长一样,连刷柄都得长出来啊!”
赵二憨侧耳听着,不时也被逗得笑起来,就努力地在心里记了下来,有机会可以把这个笑话讲给牌友听。
小保姆看着炉灶,不时地加些开水。赵二憨一时无事可做,就走到了客厅里看他们打牌,还顺便从阎在行等人手里接过或三星将军或小熊猫牌子的高档香烟抽。
兔肉的香味很快溢满了整个院落。讲“刷毛”故事的男人对赵二憨说:“到底是兔肉,真香!”另一个女人接着说:“现在市场上的肉是真没法吃了,肉里打水鸡里填沙不说,里面还含激素。电视里说,为什么如今很多小男孩、小女孩嘴角上都长满了黑糊糊的胡须,就是因为食用的东西激素含量严重超标。”讲“刷毛”故事的男人说:“女孩长小胡子咋啦?你们真老土,那叫性感,懂吗?”赵二憨想笑,就很放松地笑出声来。
又隔了一会儿,赵二憨感觉兔肉炖得差不多了,就走进厨房在汤里放了些盐,然后对众人说:“你们慢慢玩儿吧,我得走了。”
阎在行说:“你忙活了半天,总该尝尝兔肉再走吧?”
赵二憨笑着说:“不了不了,你们白天上班,晚上才挤空玩会儿牌,挺辛苦的。”
阎在行没有强留,但也很客气地出门送客。两人走到大门外,阎厂长问:“你朋友的女孩子哪个村的?叫什么名字?”
赵二憨一时语塞,只好编了一个谎话:“你看我这人的记性……我只是跟这个女孩的舅舅在一起喝过几次酒,还真没问太清楚哩。”
“没关系没关系。”阎在行冲赵二憨颇为神秘地笑了笑,“我懂得我懂得,咱们男人嘛……”
赵二憨想解释一下,他和那个大眼睛之间并无干系,但是,这时阎在行打了个手势,那个手势看上去十分暧昧,所以赵二憨索性不再过多的解释。
阎厂长说:“既然这样,让她过了元旦找我报到吧。”
赵二憨连忙道谢,走了没两步阎在行拉灭了门灯,赵二憨跟前猛的一黑,差点跌了一跤。
第二天一早,老婆下夜班回来就发现少了一只兔子。她问赵二憨:“怎么少了一只兔子?”赵二憨说:“如今盗贼满天飞,少只兔子不是大不了的事,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
赵二憨洗漱罢了,就径直来到洙水酒家。因为时候尚早,苗小凤和闺女丽丽还没来到,一个瞎了一只眼的厨师在灶间点火,大眼睛在门口择一堆烂菜。赵二憨忍不住骂了一句:“妈的,怪不得吃了饭店的饭菜就拉肚子,就这烂菜叶子?”大眼睛当即表现出一脸无辜的样子。赵二憨心里当然明白,烂菜肯定与她无关,她又没得什么好处。
大眼睛说:“二憨哥,你这么早就来啦?”
赵二憨说:“早点来给你报个喜讯儿啊!”
“那事成啦?”大眼睛喜出望外。
“是啊,阎厂长主持工作,阎厂长跟我有亲戚哩,我去说一下,他还能不给面子?”
“二憨哥——不——二憨叔,真得谢谢你!”
“二憨叔?”赵二憨心里咯噔一愣。
大眼睛一副极为认真的模样。“您想啊,论年纪您是不是该叔叔的辈分?”
赵二憨心想:二憨哥眨眼工夫变成了“二憨叔”,这女孩的心眼儿活泛着呢。人家甘愿来做小字辈,自己也只好拿捏着硬充“叔叔”的样子啦。
“真是太谢谢您啦!”大眼睛再次道谢。
赵二憨说:“你也别客套了,小小年纪一个人出门在外很不容易的,帮帮忙应该的,可别忘了元旦后找阎厂长报到呀。”
赵二憨心里清楚,自己本是跟苗小凤吹牛,不过是想在苗小凤面前显摆一下能耐,好多一些进一步接近苗小凤的机会,没想到无意插柳柳成行,让大眼睛干地里拾鱼——白拣了个便宜。但是,尽管搭上了一只兔子,尽管费了一些周折,总算做成了一桩事情,从大眼睛后来又惊又喜的神情里,觉得自己很像个男人。
正当赵二憨遐想的时候,大眼睛已从操作间端来一份凉拌猪耳、一份老醋花生、两份热菜、一瓶洙水老窖,另有一包白将军香烟。大眼睛说:“谢你的,二憨叔,今天我请客!”
赵二憨顿时愣在那里:“就是你请客,我也吃不了那么多啊?”
“二憨叔,我陪你喝一点嘛!”大眼睛说着话,“啪”的一声往赵二憨脸上亲了一口。赵二憨慢慢地摸了摸被亲过的腮帮,兴奋无比地将一大杯白酒喝了个底朝天。
帮了大眼睛之后,赵二憨又回到了原本平静的日子里。因为在十冬腊月的天里,无论是养殖场,还是农户,都很少有劁猪骟羊的生意,他就早上睡懒觉,八九点钟起床,然后在家凑兑着吃点零食或者干脆空着肚子,中午到洙水镇吃点饭喝点酒,然后四下里溜达一番,再买菜买肉回家,下午约别人或被别人约去赌博。冬闲时节,镇里、村里晚上总是有很多打牌的人。要账顺利了,兜里的钱多了就玩牌九,手头上的钱少了就打麻将,有时输有时赢。村人们的日子每年冬天都是这样一天天打发掉的,赵二憨觉得这样反而挺忙活,每晚睡下都是昏昏沉沉,从来不会因为精力过剩而夜不能寐。
这天晚上十点多,赵二憨、丁万能等人正在村主任家玩牌九,外面突然响起嘭嘭嘭的敲门声,村主任的老婆不耐烦地跑出去开门,只听突然大叫一声,一时间院子里传来一阵乱糟糟的脚步声,村主任家的杂交狗也汪汪汪地叫了起来。几个下赌注的大都当场吓瘫,村主任几步跨进里屋然后从窗子里跳出来。赵二憨毕竟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也学着村主任的样子往外跳出去。谁想,待到赵二憨刚要跃上院墙,联防队员的三四只手电筒就同时照在了他的身上。
一个联防队员威胁道:“别动,动就开枪了。”
赵二憨心里说:狗屁!你们这帮人要是有枪,不比真警察还威风!赵二憨没有理会联防队员,急急地逃了出去,一个个吃得浑身横肉的联防队员哪里还能追得上。回到家里,妻子还没睡,赵二憨就给妻子说了联防队员抓赌的事。起初,妻子埋怨他说:“使劲赌呀,抓了活该!”
赵二憨并没跟妻子争吵,开导妻子说:“我是赢家,这几天少说赢了几千块,虽说没当场抓住,可是那几个没跑掉的都是没种的货色,等关进派出所,用电警棍一戳,马上就有人把我供出来。”
妻子说:“先躲出去,再想办法。”
谁也没想到,赵二憨刚想推摩托车往外逃,几个联防队员已经赶到他的近前,在他一愣神的时候就被人揪住了手臂。不大会儿,赵二憨和那几个参与赌博的,还有看热闹的统统被带到派出所。
七天过后,赵二憨才被从县公安局拘留所放出来。走出拘留所的大铁门,他乘上通往洙水镇的公交车。一个熟人看见了,跟他打招呼:“二憨,出来啦?”
赵二憨有气无力地说:“出来了。”
“这帮狗日的联防队员,不停地抓赌的抓嫖的,今年可是发大了!”
“唉,有什么办法?”
“他妈的,今年这帮小子一个人得分这个数。”那人竖起了三根手指头。
“三千?”赵二憨问。
那人摇了摇头说:“哼,三万!”
赵二憨恨恨地说:“这帮人整天办那些缺德事,迟早会遭报应的。”
“这话我信。”那人看看四周沒人,低声说道,“前天晚上,省电视台《焦点访谈》把镇上脱衣舞的事曝了光,里面还说派出所收了几千块钱的保护费呢!”
路过洙水酒家的时候,赵二憨摸了摸衣兜,只剩下二十块零五毛钱。苗小凤看见他落魄的样子,丢下手里的活计迎了过来。苗小凤问:“在拘留所里没挨打吧?”
“没有,哪像派出所里的这帮小子,动不动就往死里折腾你。”
“那就好,我去给你弄些吃的。”苗小凤说,“还是你常吃的那几样。”
赵二憨应了一声,说:“别麻烦了,就一碗肉丝面。”
“别跟自己过不去了。看在咱们老熟人的份上,今天为你免费,也算是给你压压惊。”
苗小凤就对厨房里的师傅说:“一碗肉丝面、半份老醋花生米、半份凉拌猪耳、二两半洙水老窖酒。”
赵二憨这才注意到,里面雅间里不时传来噼噼啪啪的麻将声。待到苗小凤再过来时,赵二憨小心地问:“怎么,你不怕抓赌?”
“抓赌?这几天谁顾得啊?这帮联防队员差不多都要卷铺盖回家,听说所长得判刑呢!”苗小凤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赵二憨问:“就是因为演脱衣舞的事?”
“说是也是,说不是也不是。”苗小凤说,“还有更缺德的事呢,所长不知是吃了豹子胆怎么的,竟然为一个强奸犯作伪证,让人给举报了。”
说话间,雅间里突然有了争吵声,一个打扮得十分妖艳的年轻女子随后骂骂咧咧地走出来:“不就是他妈的千把块钱的输赢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打啦,不打啦!”赵二憨听着声音很熟,仔细看时竟是大眼睛。才多长时间,赵二憨差点都认不出来了。
大眼睛看了看赵二憨,说:“二憨,是你啊?”
“啊——你,你怎么……”赵二憨支吾着,想着大眼睛对自己的不同称谓,不禁打了个寒战。
大眼睛并没有要与赵二憨多说话的意思,只是扭头看了看窗外。她穿着质地很好的软皮大衣,脸上浓妆艳抹,距离两米远就能闻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芳香。
大眼睛走了。赵二憨对吧台里的苗小凤说:“这个女孩变化不小啊!”
苗小凤说:“还不是多亏你的引荐,唉呀,你上过她没有?”
“上上上——上你个头!”赵二憨不好意思起来,“我是说,我都快不敢认她了。”
“当然了,她已经不是原来的她啦,青春饭多好吃啊。”
“青春饭?有人养?”
“你的好亲戚阎厂长啊,听说姓阎的马上就要跟老婆离了。”苗小凤有些鄙夷地说,“离了就要她罢,如今的男人还能有几个靠得住的?”
赵二憨开始默默地喝酒吃饭。填饱肚子后,赵二憨才问了一句苗小凤:“你闺女找工作了吧?”
“她爸老不在家,俺又没个做官的亲戚,去哪里找合适的工作?有时想开点就好了,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说得在理呢。”赵二憨说。
“人常说,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丢!就比如你吧,你蹲了七天拘留所不说,还被罚款五千块,有的人却皮毛无损。”
“啥?”
“听说你们的村长罚了八百块,丁万能只罚了五百多,财所所长的小舅子只花了一顿饭钱,镇长的一个八不沾的亲戚一分钱没罚。”
赵二憨看着苗小凤,好久没有说话。一开始,派出所让他交出两千五百块的赌资,再交两千块的治安罚款,赵二憨不情愿交足赌资,才愣是被关进拘留所。赵二憨起先觉得很合算,因为虽说在里面关起来不舒服,可能省掉四千五百块钱。日他亲娘的,他们这帮狗日的坏蛋!农民兄弟们不过是在冬闲时节赌个博玩个牌而已,而你们呢?你们却靠着一身“虎皮”吓唬老实人,却丧尽天良帮坏人开脱,你们还是人吗?你们被抓,被判刑,活该!
赵二憨在心里狠狠地骂骂咧咧,好似不讲情理的泼妇骂街,但很解恨很过瘾很舒坦。不知什么时候,赵二憨猛一抬头,发现自己已走在回家的路上。他踏着冬日里有些干燥的柏油路,尽量往家的方向远望,越望越近,越走越快。约摸过了十分钟,迎面遇到一干迎亲的人马,赵二憨突然豪气冲天,情不自禁地模仿起了早年电影故事片的经典台词:
别看今天闹得欢,小心日后拉清单!
原刊责编 许 晨
【作者简介】蔡高选,1965年生于山东巨野。曾在《山东文学》、《当代小说》、《青年文学家》等文学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现供职于菏泽电视台,菏泽市小说学会会长,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