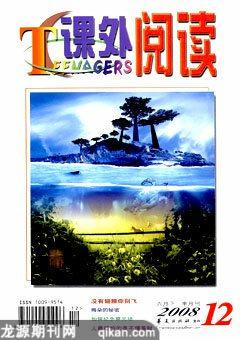没有翅膀你别飞
佚 名
一只灰褐色的麻雀从窗前飞过,“倏”的一声,远了。
他斜倚在窗前,看着窗外新芽初绽的梧桐,还有一掠而过的麻雀。他知道,只要轻轻抬一抬腿,他就可以飞出去,像鸟儿那样自由飞翔,所有的痛苦和折磨便随之烟消云散。
他真的这么做了,大脑一瞬间的空白,让他迈出了那一步。他以为他会像一只鸟儿那样,但一跨过那个矮矮的窗台,他就发现自己错了。他像一只笨重的熊,直朝地面砸去。
他再次睁开眼睛,是在五天以后。他听到了一声苍老的呼唤:“献儿,回来。”于是,他回来了。他慢慢睁开眼睛,看到了一片白:白的墙,白的衣,白的发。
“妈!”他想叫一声,但他叫不出来,一滴眼泪从眼角滚落,滚到一只骨节突出的手上。手像被开水烫了似的,哆嗦了一下,然后急促地抚着他的脸:“献儿,献儿,你可回来了。”
两个月后,他被母亲从医院里用轮椅推了出来,除了大脑还能继续思维,从胳膊往下,他的身体变得软塌塌的,像一把面条。
“妈,让我去死吧,你别管我。”他扭头哀求母亲。
母亲不理他,赌气似的把车推得更快。
回到家,确切说是母亲和父亲的家。他的家早在和妻子离婚后成了一片冰冷的地狱,女儿被妻子带走了,他什么都没有了,选择从楼上飞下去,是他做出的最残酷最无奈的选择。
父亲拄着拐杖从屋里出来,铁青着脸,一言不发,一只手帮妈妈把他推进一楼的屋里。从家门口到楼外的4层台阶已经用水泥砌成了斜坡,防盗门拆了,没有了门槛,他被稳稳地放在窄小的客厅当中。
父亲点燃了一支烟,母亲拿过毛巾不停地在脸上擦。
他突然低下头,把头窝在胸前,脸埋在双手间,呜呜大哭起来。
以后大概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他被父母小心地照顾着,总有一个人寸步不离在他跟前。父亲和母亲把一张大床和一张小床并在一起,晚上睡觉,他睡最里边,父亲挨着他,母亲挨着父亲,一旦他有什么动静,父亲就推推母亲。两个人一起起来给他翻身、换尿垫。每当父母花白的头低下来,为他收拾衣裤时,他就感觉有千万把刀子在割他的心,他恨不得自己立刻消失,像一缕烟,被风吹散了,不留一丝痕迹。
那天母亲出去买菜,父亲在家陪他,父亲看他情绪比较稳定,就很放心地把他放在客厅,第一次没有推他到卫生间,自己去解手了。
他等父亲一进卫生间,就快速转动轮椅,一把拉住卫生间的门,把门扣扣上,然后用一小截铁丝插在扣鼻儿里。任凭父亲在里面叫喊,把那扇薄薄的木门拍得山响。
他把轮椅摇到厨房,那里有可以让他消失的工具:刀。
他拿起一把刀,放在腕上,喃喃道:“爸,妈,对不起,再不能让你们为我受累了。”然后,对准腕上蜿蜒的青色凸起,割了下去。
感觉不到疼,他露出了一丝微笑。
突然,他的脸上热辣辣地烧了一下!那是父亲的巴掌,实实在在地扇在他脸上。父亲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一样,瞪着他,双手发抖,嘴巴很难看地歪着:“你个孬种!除了死你还会干什么?”
腕上的血还在滴,父亲一拐一拐颠进卧室拿来一根布条,狠狠地把滴血的地方捆住,继续瞪着他。
“养了你几十年,你就这样报答我和你妈?媳妇没了,可以重娶,孩子走了,还可以再要回来,你以为一死就啥都解脱了?你叫我和你妈咋活?”
这时,母亲回来了。一进家门看到他和父亲对峙的样子,看到他胳膊上缠着的血布条。她扔掉手里的菜,坐在沙发上仰着脸号啕大哭。
他转动轮椅,从父亲身边挤过去,转到母亲跟前,轻声叫:“妈。”母亲没有一点儿反应,仍旧放声大哭。他伸出双手,抱住母亲的脸:“妈,对不起。”
母亲没有理他,突然停住了哭泣,“呼”地站起来,快步走进厨房。等母亲从厨房出来,他看到母亲手里掂着那把明晃晃的切菜刀,“要死是不是?大家一起死,自杀,我也会。”
母亲说完拿着刀毫不犹豫地向自己的胳膊割去,鲜血冒了出来。“妈——”他感到撕心裂肺般的痛,他大喊一声,和父亲同时扑向母亲。
他整个人重重地从轮椅上摔了下去,扑倒在母亲脚下。他此刻才体味到了死的痛苦,那是死者留给生者的痛苦,是失去的痛苦。
当又一个春天到来时,12岁的女儿推着他在门前的小花园里散步。春风轻拂,杨柳依依,小鸟在枝頭唱着轻快的歌。他慢慢给女儿讲他想飞的过去,想被风吹散的过去,讲从卫生间破门而出的爷爷和号啕大哭的奶奶,他似乎很平静。
他说:“孩子,生命不仅仅属于个人。人根本不能像鸟儿那样,没有翅膀,千万别飞。”
(司志政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