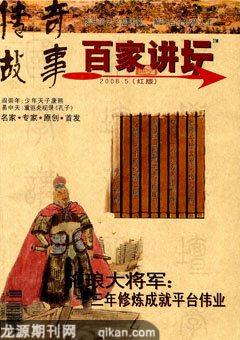海客谈瀛洲:帝制时代中国的西方印象
周 宁
广东肇庆教堂接待室的正面墙壁上挂着一幅欧洲绘制的世界地图。从图上可以看出,世界有五大洲,中国是亚细亚洲的一部分,而并非中国人想象的那样,是世界的全部或“天下”。
利玛窦神父用心良苦,他想用地图改变中国人心中那种无知的自大与莫名的恐惧。“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的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变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则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另有一个结果也同样重要。他们在地图上看到欧洲和中国之间隔着几乎无数的海洋陆地,这种认识减轻了我们到来所造成的恐惧。为什么要害怕一个天生离他们那样遥远的民族呢……”(利玛窦、金尼阁著《利玛窦中国札记》)
对外部世界的轻蔑与恐惧交织在一起,是一种复杂的民族心理,根本原因还在于无知。万历年间,利玛窦来到中国的时候,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中国海岸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不久荷兰人也来了。这些长身高鼻、猫眼鹰嘴、鬈发赤须、诡服异行的“佛郎机”或“红毛夷”,不论对沿海的百姓,还是帝国的官吏、皇帝来说,都是一个谜。
1517年,由舰长费尔南·皮雷斯;德·安德拉德(Peres de Andrade)与大使拖默·皮雷斯(TomePires)率领的葡萄牙使团到达广州。《广州通志·夷情上》中记载:“佛郎机素不通中国,正德十三年,驾大舶突至广州澳口,铳声如雷,以进贡请封为名。”在大明皇朝的眼里,他们是来朝贡的番使,只是此前从未听说过有这么一个“番邦”,也从未见识过那么野蛮的习俗,贡船驶入珠江口后,竟用杀人攻城的火炮来表示友好与尊重。札炮让怀远驿的守备吃惊恼怒,于是佛郎机贡使被扣押在光孝寺学习了三天的天朝礼仪,然后才定好日子引他们去见总督陈西轩公。
葡萄牙、西班牙在大明,被统称为“佛郎机”,这个称呼并无恶意。按照利玛窦神父的解释,穆斯林将欧洲人称为“法兰克”(Frank),中国人随他们称呼,但因为发不出“r”这个音,就成为“佛郎机”。但在马来半岛、苏门答腊或爪哇岛信奉回教的商人们眼中,佛郎机人绝非善类,毕竟葡萄牙人占领了他们的城市,烧毁过他们的船只与房屋,屠杀过他们的父兄妻女。
1511年,葡萄牙阿尔布克尔克总督攻陷马六甲,洗劫9天,满剌加国王派使者向大明帝国求援。迟迟10年以后,明世宗才想起让兵部议一议这件事,并下了一纸诏书:责令佛郎机退还满剌加,并谕遏罗等国前去援救。
诏书下得荒唐可笑,生长在内宫太监和女眷身边的年轻皇帝,还真以为四夷慕化宾服,帝国抚有天下,佛郎机不过是满剌加旁边苍茫大海中的一个蕞尔小番邦!还以为真的像郑和船队远航回来后宣传的那样:“天书到处多欢声,蛮魁首长争相迎。南金异宝远驰贡,怀恩慕义摅忠诚:”(马欢《纪行诗》,见《瀛涯胜览》)
当时,在广州做佥事的顾应祥详细记述了第一支葡萄牙使团在中国的遭遇:“正德丁丑(十二年)……蓦有大海船二只,直至广城怀远驿,称系佛郎机国进贡。其船主名加必丹。其人皆深目高鼻;以白布缠头,如回回打扮……以其人不知札,令于光孝寺习仪三日,而后引见。查《大明会典》并无此国入贡,具本参奏,朝廷许之,起送赴部。时武宗南巡,留会同馆者将一年。今上登极,以其不恭,将通事明正典刑,其人押回广东,驱之出境,去讫。其人在广东久,好读佛书。”(《筹海图编》)
大明皇朝的官员百姓,似乎弄不清葡萄牙与满剌加究竟有多远,分不清阿拉伯人与葡萄牙人,并将天主教与佛教混同一谈,看到葡萄牙人读《圣经》、听布道、做祷告,就想当然地判断其“好读佛书”。
广州素来是五方杂处的商港,明朝以来禁海,外番贡使从海路来,限走广州。人们见怪不怪,如今多了个回回打扮的佛郎机,似乎也不足为奇。若不是他们过分剽悍凶险,经常如海寇般犯边扰民、劫财掠物,天朝似乎也不会特别注意他们。但是,由于他们在中国海岸的暴行,天朝民间出现了一些关于他们的恐怖传说:“番国佛郎机者,前代不通中国……其人好食小儿……法以巨镬煎水成沸汤,以铁笼盏小儿置之镬上,蒸之出汗。汗尽,乃取出,用铁刷刷去苦皮。其儿犹活。乃杀而剖其腹,去肠胃,蒸食之。”
这段吃人故事,见于1574年阎从简的《殊域周咨录》。记载此事的远不仅这一部书,从中我们可知,佛郎机在明朝的印象早已被涂抹得一团漆黑,这里不仅有外夷的暴行,也有国人的想象。
利玛窦知道,佛郎机侵暴边疆、杀戮人民、劫掠财物,番鬼形象恶劣到极端,所以他才极力避免大明人将自己与那些海上暴徒混为一谈。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和他的同道们都来自那个香山澳,大明帝国边境上的一个“番鬼城”。这是让国朝人士感到极不舒服的一件事,总督张鸣就曾上书比喻说:“粤之有澳夷,犹疽之在背也。”(《明史·佛郎机传》)这个比喻还真是细微妥帖:疽疥虽无大碍,但总让人难受,何况还长在背上,痒痛难挠,让人痛苦无奈。
佛郎机干扰了大明朝一个世纪,商人海盗在边境,传教士在内地京城,但国朝中人,连最饱学者也说不清他们是谁,来自何处。朝廷不准其朝贡,但佛郎机人凶险,武器也最精良,海外诸番无敢与之对抗,大明边防也无法将其制止,于是坊间议论纷纷。
连佛郎机与满剌加都分辨不清,就更难分辨葡萄牙与西班牙了。绕道美洲征服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晚半个世纪来到中国海岸。大明官民把他们也称为佛郎机。于是,有澳门的佛郎机,还有吕宋岛的佛郎机。
西班牙人占据菲律宾后,一度窃想远征中国。他们开辟了从南美洲到菲律宾的大帆船贸易,于是,美洲的白银被源源不断地运抵中国购买中国货。国朝不知海外变故,盛传“海上有银山”。
当时,万历皇帝大建陵墓,耗资巨大,而朝鲜战争又劳民伤财,内府、宗藩、冗官势穷弊极,耗尽帝国财政。人们只知银元流入,却不知银元来自何方,闽南两位风水先生忽发奇想,上奏朝廷说,吕宋有座机易山,山中有树,盛产金豆,如果派人去采集,每年可获黄金10万两,白银30万两。
神宗皇帝将信将疑,派太监高窠前去勘察。高窠是福建税使,知道这是胡说,便派海澄丞王时和、百户于一成带着那位名叫张嶷的风水先生渡海前往吕宋。马尼拉的西班牙总督面对前来采金豆的中国官员大惑不解,质问道:“中国派你们来开山,山各有主,怎么能,随意开采?如果中国有金山,我们可以去开采吗?何况你们说山中树上产金豆,树是什么树?”王时和一时答不上来,而张嶷诡辩道;“山中遍地黄金,还要问什么树所生吗?”于是哄堂大笑。(《明史·吕宋传》)
天朝官民的糊涂给利玛窦委实带来许多麻烦。利玛窦把自己扮成和尚在肇庆传教,但总遮掩不了“长身高鼻、猫睛鹰嘴”。肇庆是个内陆城市,听到过一些关于佛郎机人剽劫行旅、掠食小
儿的传说,而好奇的小孩向教堂扔石头,教士的仆人就将其抓住,周围的百姓沸腾了。他们哭天抢地,说孩子被食人生番捉走了,要求官府惩治番鬼。对此利玛窦很不理解,不明白中国百姓为什么如此容易仇恨,容易激动。
其实问题还是出自那些传言。据说佛郎机国在狼徐鬼国对面,狼徐鬼国“分为二洲,皆能食人”。《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中还记载:“嘉靖初,佛郎机国遣使来贡,初至行者皆金钱,后乃觉之。其人好食小儿。云其圆惟国(口)得食之,臣僚以下,皆不能得也。至是潜市十余岁小儿食之。每一儿市金钱百文。广之恶少,掠小儿竞趋途,所食无算。”
与佛郎机人打了一个世纪的交道,朝野对佛郎机还是一无所知,这时荷兰人又到了。《辛丑年记事》中记载;“(1601年)九月间,有二夷舟至香山澳,通事者亦不知何国人。人呼之为红毛鬼。其人须发皆赤,目睛圆,长丈许。其舟甚巨,外以铜叶裹之。入水二丈,香山澳夷虑其以互市争澳,以兵逐之。其舟移入大洋后为飓风飘去,不知所适。”(王临亨《粤剑篇》卷三)
佛郎机凶狡不可名状,荷兰红夷又如飓风飘来,更残暴也更让人捉摸不透。1604年、1622年两次冲突之后,“红毛水怪”又占领了台湾。世界变得越来越让国良不能接受了,而难以接受的事必须得到一种“合理的解释”才能化解它对社会与传统观念带来的冲击。
万历时代中国人的世界知识与西方形象,不仅让利玛窦神父难堪,实际上也让国人自己难堪。
想当年,郑和七下西洋,汪大渊浮海万里,杜环经行西亚,法显玄奘西游,张骞“凿空之行”,国人不仅漫游世界,也将世界知识带回中国,胸怀眼界,何等开阔。至少此前一千年,中国人已经知道罗马帝国,知道那些通往“海西国”的道路,知道“大秦”的风土文明,而且颇有些羡慕。远的不说,就连本朝人郑和远航,200年后也变得荒渺蹊跷,远航的事迹与所历的国家似乎都半真半幻,若有若无。
利玛窦在北京的那些年里,坊间正流行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碧峰长老给永乐皇帝呈上一个“经折儿”,图中画着西洋十八国。长老说:“西洋是个总名,其中地理疆界,一圆是一国……第一国,金莲宝象国;第二国,爪哇国……第十八国,邦都鬼国。”
国朝人士不仅不知道大西洋国,甚至连200年前郑和远航所至的国家及地区也不清楚了。历史衰落到人已经无法想象人的事迹,就只好将人的事迹神魔化,《西游记》即问世于1580年前后,玄奘和尚乘危孤征、远徙万里去印度取经的历史变成了神魔夹道的传奇。
无法相信人的事迹,神魔化是一种解释,也是一种安慰。毕竟不可想象的伟大事业原不属于人的经历,衰落中的现实也就不会令人难堪。
200年前郑和下西洋(1405~1433),远至东非与阿拉伯半岛。300年前汪大渊(1311~?约逝于明初)附舶浮海,两下东西洋,游踪广远,甚于郑和。当年马欢随郑和出洋前就研读过《岛夷志略》,下洋经历亦证明了汪大渊“所著者不诬”(见《瀛涯胜览》序文)。
郑和时代不论航海知识还是世界知识,都不见比汪大渊时代有所进步。英国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史,发现1402年由朝鲜李荟和权近绘制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是在1330年左右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1370年左右僧清潜的《混一疆理图》的基础上合成的。遗憾的是,两幅中国的地图已经失传,但从留下来的朝鲜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看,汪大渊时代中国人所掌握的世界地理知识非常广博,不仅比同时代西方人掌握的中国周边地理知识多,而且有可能比-西方人掌握的西方地理知识还多。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图中的西方部分很值得注意,其中一共有将近一百个欧洲地名和三十五个非洲地名,非洲的形状很正确地画成三角形,而且三角形的尖端所指的方向也是正确的。图中非洲北部的撒哈拉,与许多中国地图(包括《广舆图》在内)上的戈壁沙漠一样,画成黑色。在亚历山大里亚所在的位置上绘上了一个塔状物,以代表亚历山大里亚的著名灯塔。地中海的轮廓画得很好,但绘图者没有把它画成黑色,这也许是因为绘图者不能肯定它是不是一个普通的海的缘故。德、法等国的国名均用音译(A-lel-man-ia和Fa-li-his-na),而且还绘上了亚速尔群岛。从所使用的符号来判断,朝鲜的平壤被认为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首府之一,而另一个被认为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城市则位于欧洲,从它所在的位置来看,大概是指布达佩斯。从这幅地图可以看出,绘图者所掌握的西方地理知识是相当广博的,比欧洲人当时所掌握的中国地理知识要明确得多。”
但万历朝国人的世界知识,已经收敛到爪哇,爪哇亦若有若无,半真半幻。书籍散佚是集体遗忘的证据,当年广博的世界地图已经不知去向,没有人关心甚至没有人相信。
国人祖上也曾胸怀宽广,例如,西方作为一个“有类中国”的文明国家的形象,最初出现在汉代中国的世界视野里。从中亚和西南亚来的商人与汉廷出使西域的使节,都可能带回大秦国(据考就是东罗马帝国)的消息。大秦、海西国、拂菻,可能指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可能指小亚细亚半岛、意大利半岛或巴尔干半岛,可能指托勒密、塞琉古王朝,也可能指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甚至塞尔柱克王朝。不管怎样,它们在地理与文化传统上都与我们今天所说的“西方”有关。
拂菻之名,最早出现在隋唐时代(见《隋·裴矩传》卷六、《铁勒传》卷八十四、《波斯传》卷八十三),以后直到佛朗机人出现在明代,中国文书中一直以拂菻与大秦并用,称拜占庭帝国。大唐天下,疆域辽阔,五方杂处,四夷称臣。《旧唐书》还记载贞观十七年、乾封二年、大足元年、开元七年,拂菻王波力多遣使来朝献贡。
在汉唐胸怀中,国朝人士强调的是西方“有类中国”的文明一面,甚至美好的一面。从汉到唐宋,大秦形象在中国,有些特征被遗忘了。有些情节则被添加进来,只是“有类中国”之说被一再重复。
怛罗斯战役中,杜环被黑衣大食俘虏,流离中亚、西亚十余年,才从海道乘大食商船取道广州回国。劫后余生,杜环著《经行记》,记述了自身遭遇与西亚风土人情。可惜这部书散佚了,只有、其中一些内容转述在唐代杜佑著的《通典》卷193中。提到大秦,它已不满足于“有类中国”之说,干脆成了中国人:“其人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或云,本中国人也。”
国朝祖上胸怀宽广,对世界、对西方也有好印象,但利玛窦神父却没有赶上那个好时代。
在中国人的眼界中,帝国膨胀,世界缩小,大明皇朝际天极地,帝国之外不是蛮荒大漠。就是凶险的海洋,几个鸡零狗碎的小岛,加起来不如帝国的一个省大。中国人的这种自我感觉,让利玛窦神父伤透脑筋。中国人不了解世界,怎么了解世界中的西方,不了解西方,怎么能了解西方
的基督教,还有他,这个泰西和尚……
利玛窦到京师后,自称大西洋人。而礼部上书称,《大明会典》记载到西洋琐里国,并无大西洋国,利玛窦其人可疑,其国也“真伪不可知”。
利玛窦和他的同道们继续传播他们的地图,介绍天下有五大洲(亚细亚、欧罗巴、利未亚、亚墨利加、墨瓦腊泥加),希望能够改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以及对欧洲人的看法。徐光启在南京见过赵可怀、吴中明进士刻印的《山海舆地图》,李之藻与友人造访利玛窦时,也见到他悬挂在堂前的《大地全图》。令神父感到欣慰的是,不仅一些有知识的中国人开始接受他的《山海舆地图》,对欧洲文教制度开始有好感,而且万历皇帝还传旨将他献的《万国全图》印在宫里的屏风上。
利玛窦1610年在北京过世,13年后,艾儒略神父在杨廷筠的协助下编成《职方外记》,卷首“五大洲总图界度解”之后分五卷,即亚细亚总说、欧罗巴总说、利未亚总说、亚墨利加总说和四海总说,其中欧罗巴总说对欧洲的介绍尤其详细。然而,艾儒略还是感觉书不尽言,1637年又出《西学问答》,进一步解答了有关西方风土人情的四十多个问题,对方域、列国、饮食、衣服、宫室、制度、立学、设官、宗教、政形、武备等方面都有生动的描绘。国朝总算有人明白,如谢肇涮《五杂俎》所言:“天主国,更在佛国之西,其人通文理,儒雅与中国无别。”
可喜的是,利玛窦、艾儒略、毕方济、南怀仁,由明入清,百年间编制了《坤舆万国全图》;金尼阁到中国,又带来了7000多部图书,大量介绍欧洲,从山川风俗到政教、军事、物产、技艺等各个方面,一应俱备。但国朝很少人知道,更少人相信。张维华指出:“明人于欧西地理始终不明,而于西士所言及其著述,亦始终疑为伪妄。”(《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
在《明史》中,《四国传》表述的欧洲国家观念,仍一片混乱: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被误当作南洋国家,近满剌加、吕宋或爪哇,虽然听说意大利在大西洋,但不相信利玛窦的《万国全图》与“五大洲”之说,评价“其说荒渺莫考”,“其所言风俗、物产多夸”。顾炎武可算当时饱学之士,但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写佛郎机也不外是流行套话:“佛郎机国在爪哇南,古无可考……素不通中国……略买食小儿,烹而食之。”
传教士们煞费苦心,国人们不是不闻不问,就是将信将疑。当然,将信将疑者还算是温和,激烈者已开始大加讨伐,认为“外夷”所传,不可尽信,甚至尽不可信。魏潜在《利说荒唐惑世》一文中说;“利玛窦以其邪说惑众,士大夫翕然信之……所著《坤舆万国全国》沈洋窗渺,直欺人以其目之所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按验也。真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中国当居正中,而图置稍西,全属无谓……焉得谓中国如此蕞尔,而居于图之近北?其肆无忌若此?!”由此看来,明清之际,中国并不是没有获得世界知识的条件,而是没有接受世界知识的心态。
往事已经忘却,大秦或拂菻早成为无稽之谈;新知依旧漠然:欧罗巴或大西洋国,妖妄怪诞,说了也没人相信。就连徐光启那一代人的西学知识,也很快被遗忘了。只有那些谜山蹈海、诡诈莫测、杀人掠物、烹食小儿的番鬼红夷形象,定格在中国人的记忆与想象中。
英国人1638年到中国海岸,1717年广东碣石总兵陈昂的奏折上才提到一个“英圭黎”,觉得与荷兰人难分别,都属于“红毛”。同时有台湾知县蓝鼎元在《粤夷论》中道:“红毛乃西岛番总名,中有荷兰、佛兰西、大西洋、小西洋、英圭黎、干丝腊诸国,皆凶狡异常……”有关西方的观念,还是那么乱七八糟。
知识变成荒渺莫考的传说时,真正荒渺莫考的传说也可能变成人们信奉的知识。荷兰、佛兰西、英圭黎、干丝腊诸国,尚有国可考,但大西洋、小西洋,又是何国何处?《大清一统志》于乾隆八年(1743年)成书,书中所论西洋,一塌糊涂,认定西洋国可在印度洋附近,也可在西南大海中,佛郎机、荷兰与苏门答腊、爪哇相邻。
45年后,即乾隆五十四年,和坤等奉旨编修的《钦定大清一统志》完成,外国都被列为朝贡国,西方国家就有荷兰、西洋、俄罗斯、西洋锁里、佛郎机等,地理方位、人文制度,一样地混乱模糊。利玛窦、艾儒略、徐光启、杨廷筠的努力真可谓全白费了。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纪晓岚等人在校订《清朝文献通考》、《四夷考》时还在批判《职方外记》“所言未免夸张”,“五洲之说语涉诞诳”。更有甚者,时人平步青忿忿不平,认为明人甘受利玛窦之流奸佞小人的侮慢蒙骗而不自觉,认为利玛窦将欧洲译为“欧罗巴”,用字就有夸大之嫌,而将亚洲译为“亚细亚”,用心更为险恶,“亚”者,有“次”、“丑”、“细”、“微”等意,这分明是在侮辱国人。
最大的侮辱还在将来。当凶狡奸诈的红毛打破国门,即鸦片战争失败了的时候,道光皇帝才想起让人打听清楚英国到底在什么地方。可在他的皇宫中,就有一百多年前传教士为他祖父康熙皇帝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其中就清楚地标明了英国的所在位置与远来中国的航线。
受道光皇帝旨意去询问鸦片战争中被俘的英国士兵有关中国与英国和俄罗斯距离远近的姚莹也发现,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所刻的《万国坤舆图》将海陆诸国何者接壤、孰为东西、相距远近等标示得已经非常清楚(见《康鞲纪行》卷五)。
中国并不是没有了解西方的机会与条件,而是没有了解西方的动机与心态。
明朝西方人大批来到中国之后,中国人也开始零星地到西方去了。1681年底,一位名叫周美爷的华人医生,随荷兰驻巴达维亚总督高恩(Rijklof van Goens)至荷兰,一年以后返回巴达维亚。1702年十月,福建莆田人黄嘉略随梁弘仁神父到欧洲,十月中旬到伦敦,月底到巴黎,又转赴罗马晋见教皇。
这些人去欧洲,在中国却没有任何影响。就现在所知,去西方的中国人最早留下记录的是山西人樊守义(1682~1735)。他从少年时代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1707年随艾若瑟(Jos AntlProvana,1692~1720)从澳门出发,到了欧洲和美洲。1719年从葡萄牙启程,1720年回到广州后写成了《身见录》一书,记述自己这十余年在欧美的见闻。遗憾的是,这部书并未刊行。又一百年过去了,杨炳南才根据谢清高遍游海外诸国的经历编成《海录》。
西方人越来越多地来到中国,国人了解西方的机会也越来越多,西方文明的种种优势也越来越明显,但在社会一般观念中,西方形象依旧是那般模糊怪诞。
国人心目中的西方想象,重要的往往不是表述一个异域文明,而是证明该异域在本土视野内的特定世界观念秩序中的意义与功能。自先秦“九州之说”开始,国人就形成了以内外文野来区别确立秩序的“世界观”。天下九州,中国只占一州,所谓赤县神州。神州为“海内”,其他为“海外”,海内以天子为中心,五服(甸服、侯服、绥
服、要服、荒服)依次向外延伸,由文明而野蛮、由高雅而低劣。
尽管中国历史上异族入侵与征服一再打破这种形象的秩序,但每一次现实的挫折,都更加强化国人关于这种世界秩序的想象与信仰的强度。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后,华夏中心主义优越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强,而被满族征服之后,国人的华夷之防心态越发敏感顽固。中国之外有四夷,中国恩威,四夷宾服。可西方出现在四夷之外,这对国人的现实与观念秩序,都是一种冲击。
在《国朝朝贡典录》中,没有这些国家,他们在知识之外,这些国家横行海上、威胁内陆,在帝国的权力之外。在观念上。我们发现,晚明清初的国人对西方的心理有拒绝与归纳两种倾向:拒绝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否认佛郎机,或红毛夷,或西洋国是现实中的国家,将其鬼化或妖魔化。归纳是试图将晚近出现的西方国家纳入南洋朝贡国家系列内,坚持佛郎机或红毛夷近满刺加或爪哇,西班牙与菲律宾是大吕宋与小吕宋。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问题,而是社会文化问题。塑造一个荒远、模糊、怪诞,诡异、危险、低劣、野蛮的西方形象,可以维护国朝人士的世界观念,更重要的是维持这种世界观念秩序中的自我身份认同,尤其是在这种认同出现危机的时刻。将日渐强大的西方妖魔化为一个诡异低劣的他者,不但可以证明天朝上国中正文雅,避免西方出现造成的天朝文化身份认同危机,还可以将这种危机的声音压制遮蔽起来,所谓“戒世人侈谈异域”。
国人心目中的西方想象,意义还在从文化上确认、缓解、超越国朝与西方紧张的现实关系。西方扩张势力到中国,犯边扰民。首先是他们的贸易与传教事业冲击中国原有的国家与世界秩序,然后是政治与军事势力和经济文化力量结合以来,冲跨中华帝国的内外防线。强调其荒远模糊,可以在无意识中远离威胁,使威胁变得似是而非,从而减少压力,渲染其怪诞诡异,既可以排斥异类,又可以从中获得一种优越感,使外来的威胁与自身对这种威胁无可奈何的尴尬都变得可以接受,毕竟是一些不通人伦、不通情理的番鬼红夷,不可一般见识,贬低其文化低劣野蛮,可以从失败与无奈中解脱出来,巩固或重获其文化自信。往往是西方的侵扰冲击越激烈,国人关于西方野蛮的想象与传说就越活跃。
所以,在国朝历史上,西方越是表露其强大,它在国人想象的文化秩序中,形象就越是野蛮低劣。
从汉唐到明清,中国的西方形象中,除了知识的退化之外,另一点最值得注意的特征就是:汉唐文化中的西方形象,强调的是其共同人性的一面,大秦“有类中国”,而明清文化中的西方形象,强调的是其不同于人性的一面,番夷甚至,鬼魔。
在中华帝国晚期的文化心态中,西方形象是一个被压抑置换表现的他者,有关西方的表述,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在不同文本中构筑同一种西方形象,它们的价值不是认识或再现西方的现实,而是构筑一种天朝文化的世界观念秩,序中必要的关于“外番”的意义,使得国朝文化、能从中既可以“把握”西方,又可以认同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