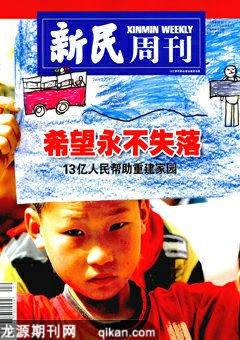心理援助:最困难的重建
黄 祺
中国首次大规模灾后心理救援行动,在灾区第一时间开展,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缺乏有效预案的缺陷,也在救援中凸显出来。

簡强的恶梦
这是简强在地震以后度过的第六个上午。5月12日的地震,好像把简强的生命剪成了两段,此前,是五彩的青春花季,现在,他的生活被完全改变。
简强是北川中学的一名初中生,“5•12”汶川大地震中,北川县是伤亡最严重的地区,而北川中学又是北川最大的伤痛——这所中学有1000多名师生被埋废墟之下,大多数已经死亡。幸存的未受重伤的学生,被暂时安置在绵阳市长虹虹苑剧场,跟其他班级一样,简强的班级已经残缺不全,他最好的朋友,也在灾难中永远离开。
长虹虹苑剧场墙上挂着几台大屏幕电视,画面永远是抗震救灾的内容,声音很大,门口喇叭不时有人用四川话喊“某某同学外面有人找”,安置点里非常嘈杂。同学们的地铺整齐排列,有人捐助了一些杂志发给同学们,剩下没有分到杂志的同学只能聊聊天打发时间。
看上去,大家都很好。简强也一样,他没有受伤,家人也都无恙。在安置点,他有时候跟两个好朋友聊天,有时候自己躺着发呆,吃的、穿的都有,还有老师管理,简强应该没有什么可烦恼的。不过,没有人知道,简强很不喜欢夜幕降临,夜晚到来意味着要睡觉了,睡着就会做梦,做梦,他好害怕。
在程文红医生到来之前,简强没有告诉别人他的这个烦恼,这些天,他每天晚上都做恶梦,梦的内容都是同一个:浑身鲜血的好朋友要杀死简强,叫简强去陪伴他。
“你们好,我是心理医生,我是到这里来帮助你们的。在我的医院,很多小朋友心里有一些烦恼,都会来找我,你们有什么烦恼吗?”程文红坐在电视机盒纸板上,这是学生们临时的“床”,几个男孩看着程文红,不说话,好半天,一个小个子的男孩回答:“没什么。”
“比如说,这几天你们晚上睡得好不好呀?”又是一阵沉默,几个男生回答:“还可以。”只有简强,始终嘴唇闭得紧紧的,双手抱着膝盖,脑袋枕在手臂上,表情严肃,歪着盯住程文红看,一直没有说话。程文红注意到这个男孩,在继续了几个问题和一阵谈话之后,她特意转向简强,问:“你有什么烦恼吗?”
“我做恶梦。”简强依旧把下巴支在手臂上,声音很小。
“什么样的梦呢?”
“有一个人,要杀死我,身上都是血,我就跑。”
梦里的人是简强最好的朋友,地震中遇难。地震已经过去6天,简强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但是,夜夜恶梦中,他都能见到这个满身鲜血的好朋友,睡觉变成了一种煎熬。
“哦。你的好朋友遇难了,你很伤心,你非常思念他,所以梦到他,这是很多人都会有的反应,很正常,随着时间慢慢过去,你会好起来。”程文红先安慰简强,这是心理治疗最常用的手段,首先让治疗对象相信自己的反应是正常和普遍存在的。
程文红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儿童青少年精神科副主任,17日赶赴四川绵阳参与灾后心理干预的工作。作为心理专家,程文红知道,虽然这些中学生表面上看上去很正常,但遭遇如此惨重的灾难,一部分学生心里一定有巨大的创伤。
简强出现了典型的心理应急反应,他突然失去了好朋友,他很思念他的好朋友,这种强烈的感情化作恶梦表现出来。受时间和场所的限制,程文红决定先实施一个简单的干预,希望能够帮助简强。
“你的朋友遇难了,你很思念他,对不对?你梦到他,说明你真的很想念他。他现在去世了,你相信他也很思念你吗?”
“相信。”
“你是他的好朋友,他也一样很思念你,那么,你认为他会伤害你吗?”
“不会。”
“好的。你梦到他,说明你很想念他,他是你的好朋友,所以他是不会伤害你的,梦里的情景都是假的,你相信这一点吗?”
“相信的。”
“好的。你现在做恶梦,只是一种正常的反应,但你要相信,做恶梦的这个现象,慢慢会减弱的。而且,你身边还有其他的好朋友,你也要多想想他们,对不对?”
“嗯。”
“你的好朋友已经去世了,你应该把脑子里这些不好的景象,慢慢缩小,然后把它放在心里一个角落,珍藏起来,用心里更大的空间,去想想身边这些朋友,他们也很需要你去关心,好不好?”
“嗯。”
简强还是没有抬起头,但表情看上去放松了一些。程文红很清楚,像简强这样的心理反应,并不是一次干预就能解决的,简强说这些天做恶梦的现象是越来越强,而不是越来越弱,这说明他的症状比普通的应急反应还要严重一些,他需要长期持续的心理干预。
可能是最艰巨的任务
这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灾后心理救援行动。
5月14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第二天,作为卫生部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的赵国秋,就从杭州出发抵达地震重灾区平武县,他是国内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的心理专家之一,在中国重大灾害救援历史上,这也是心理干预行动反应速度最快的一次。在赵国秋之后,像程文红这样的心理专家和精神科医生,陆续从全国各地到达四川,截止目前,已经有超过1000名专业人员在四川灾区参与心理干预工作。
当心理专家们到达灾区现场,他们立即发现,灾区心理干预工作将是一个复杂而浩大的工程,等待心理救援的人数太大,心理问题的种类太多,人群种类又如此不同,远远超出了之前的预料。
赵国秋最早看到的景象,是一片悲伤和绝望。在平武县南坝镇,随处有倒塌的楼房、遇难者的遗体、哭天抢地的亲人,医院里全是重伤员和他们惊恐的家人。事实上,这里每一个人都需要得到心理抚慰,但赵国秋和同事们只能寻找那些最急待干预的人群进行工作。
平武县人民医院从地震发生后,就成了当地重伤者的救命之地,根据赵国秋粗略的了解,在医院里,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已经存在符合诊断标准的心理疾病。伤者、痛失亲人的人当然最容易引起关注,但当一位护士闯入赵国秋的视野,他发现这些医务工作者,更让人担心。
一位女护士已经三天三夜没有休息,一刻不停地忙碌着,表情木然。赵国秋从其他人那里知道,这位护士原本失去父亲,与母亲相依为命。地震中,母亲也遇难,并且有10多名亲属都已经在地震中丧生。灾难对这名护士的打击可想而知,但她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痛哭流涕,却是每天为抢救伤者不停工作。
在赵国秋看来,这位护士的行为并不能仅仅用牺牲精神来解释,她是在用工作来回避现实,这样做,可能会给她自己带来危险。赵国秋特地找护士谈话,一开始,护士不愿意说话,在小心的疏导以后,她开始表达自己的悲伤。赵国秋说,让遭受打击的人面对现实而不是逃避,是心理干预的第一步。
在地震灾害发生十多天以后,赵国秋特别提醒,一定要重视救援人员的心理问题,包括医护人员、解放军官兵、消防人员。赵国秋说,从他接触到的救援人员看,最早参与救援的消防人员、解放军官兵体力透支到了极限,而且他们接触了太多死亡、伤残的景象,他们中出现严重心理问题的可能性很大。他的建议是,一部分已经非常疲惫的人员应该撤回,换新的队伍到灾区,而撤回当地的救援人员,应该马上安排心理干预。
实战演习
在汶川地震救援中,灾后心理干预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胡锦涛和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灾区时,多次嘱咐注意灾后心理疏导,邓亚萍等体育明星,也以“心理辅导员”的身份到灾区慰问。
事实上,在全国各地派往灾区的医疗队中,部分救援队里就已经加入了心理医生。积极组织抗震救援队伍的辽宁省卫生厅厅长姜潮,自己就是心理学专家,对灾后心理救援非常重视。在第一时间派出以外科医生为主的地震救援医疗队后,辽宁省第二批增援的医疗队里,就安排了30多名心理医生。

李晓白是这30多名医生中的一员,他是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的醫生。和其他医生一样,李晓白怀着满腔急切来到灾区,希望用自己的专业能力,为灾后心理受到重创的人们服务。当他到达绵阳市安置灾民人数最多的九洲体育馆内,他才真切地意识到,心理疏导的任务比他之前的想象要复杂和艰难。
九洲体育馆内的篮球馆,现在用来安置灾区学生,少部分北川中学的幸存学生也安置在这里。李晓白发现了一名初二的男生,他仰面躺在地铺上,双手把被子紧紧抓在胸前,目光直直地盯住天花板,一声不吭。李晓白得知,这名学生的父母至今没有消息,很可能已经遇难。李晓白说,这样的孩子急待心理干预,现在紧急的任务是把像这个孩子一样的人分辨出来。但是,绵阳市各个安置点,每一个都安置了几百或者几千灾民,怎样发现那些情况严重的人,是个艰难的工作。
来自同一家医院的汤艳清医生,同样靠自己的眼睛,从九洲体育馆上千灾民中发现了一位失去孩子的母亲。
“我刚看到她的时候,她正在翻孩子的照片,也不哭,没有表情,我觉得一定有问题。”这位母亲在失去儿子以后,根本就没有睡过觉,汤艳清问她是否需要一点安眠的药物帮助睡眠,她拒绝了。汤艳清知道这是一种自我惩罚的表现,这位母亲觉得儿子的死她有责任,深深的自责纠缠着她。汤艳清开始跟这位母亲交谈,引导她面对现实,慢慢地,母亲开始流下眼泪。
“她的情况比较严重,需要持续的干预,但我不知道明天是否还能到那里去。”晚上总结时,汤艳清忧心忡忡。作为专业医生,她知道持续的治疗非常重要,但他们的队伍在四川究竟怎样开展工作,还没有具体的计划,一切都还处于摸索的状态。
“对于中国的灾后心理救援,这次只能算是实战演习。”李晓白说。中国的临床心理学在最近几年中快速发展,但是,灾后心理救援尚没有成熟的应急预案,汶川地震以后,从最高级别的救灾指挥部到普通心理医生都意识到心理干预的重要,但具体怎样调配全国的专家资源、如何开展工作,却没有详细的计划,专家们只能互相协调,摸索工作模式。
赵国秋已经在重灾区平武县南坝镇坚守10多天,每天夜里在马路边休息,他最能体会一线心理干预的难处。“我们还缺乏全国性的、可操作的灾后心理干预预案,能派到一线工作的心理专家太少,很多资源难以调配,都浪费了。”
缺乏整体预案导致的后果不仅是灾区缺乏心理专家,无序的心理干预还可能带来负面的效果。程文红与心理专家们到北川中学安置点工作,校长一开始并不是太欢迎他们。校长并非不支持心理干预工作,灾后这些天,不断有心理干预工作者进入安置点与学生们接触,校长担心管理上的问题。
心理专家们同样担心,不同的人去干预,不能维持持续性,如果有不具备专业能力的人也加入这个工作,不仅起不到疏导的效果,反而带来负面的影响。
赵国秋认为,如此惨重的灾害以后,首先要区分各种程度的心理问题,按照不同程度的症状安排心理干预人员。“如果仅仅需要倾听,那么不是非常专业的人也可以做,但如果是比较重的心理问题,就必须让受过专业培训的有资质的医生来做。”但在本次地震救援中,由于灾害范围太大,缺乏操作预案,赵国秋所说的这种规范的干预,还未能实现。
在直接参与心理干预工作的同时,包括程文红在内的卫生部心理卫生专家,也在不断地总结灾后心理干预的经验,为下一步制订灾后心理干预预案做准备。
持久战
看过灾区的景象,每一位心理干预工作者都强烈地意识到,汶川地震灾后心理救援,将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
张行也是北川中学的幸存学生,他的教室在五楼,地震发生后他被压在水泥板下面,直到当天晚上9点多,他才被救援部队挖出来。地震中,他的左腿和胸部肋骨骨折,被抢救以后,在绵阳市第三医院接受治疗。张行躺在病床上,腿和胸部缠着绷带,身体的创伤已经开始慢慢恢复,但心理的创伤,却依然严重。
地震之前,张行是个电脑游戏迷,父亲经常因为张行通宵打游戏而教训他。但现在,就算打着手机上的游戏,张行脑中还是不时出现地震当时恐怖的画面,玩一会就不想玩了。
12日地震以后,绵阳市区经常能感觉到余震,住在医院七楼的病房里,能感觉到余震带来的轻微摇晃。每次摇晃,张行都极度惊恐。在一次稍微明显的余震发生时,张行大叫着要求父亲把他背下楼。还有一天,张行一觉醒来,正好同室的病友、护士和家人都不在病房,他吓得大叫,以为发生地震,大家把他遗忘在病房里了。
精神卫生博士李卫晖医生,开始针对张行的表现,进行疏导。经常想起地震时的景象,在心理学上叫做“闪回”,张行存在“闪回”、惊恐这样的急性应急反应,这些都是灾难经历者常见的心理问题。但随着谈话的深入,李卫晖发现,还有一个阴影留在张行的心里。
地震的瞬间,张行和同学摔倒在走廊上,一名老师从他们身边跑过,他们对着老师喊救命,但老师没有去拉他们。这位老师是张行平时最喜欢的老师,得救以后,张行感到很伤心。“我觉得,他很虚伪。”
在李卫晖看来,如果不进行干预,对老师的怨恨,可能比恐惧等等应急反应会更长久地给张行带来阴影。“你后来跟这位老师核实过吗?你知道他为什么没能救你吗?”张行并不知道这位老师现在在哪里,李卫晖建议他,尽可能找机会跟这位老师谈谈,在那样的情况下,也许他也没有办法救别人。
李卫晖很担心,如果老师没救他的阴影长期留在张行的心里,他会因此失去对别人的信任。像张行这样的情况,李卫晖认为同样需要长久的干预,帮助他解决心理的阴影。
在过往的重大灾害以后,一部分亲历者和幸存者,会出现严重的创伤后心理障碍(PTSD),“9•11”事件后,已经发现有很多幸存者和参与救援的人员,存在PTSD。而这种严重的创伤后心理障碍,有可能在灾害1个月甚至半年、一年后才表现出来,程文红表示,汶川地震心理干预,必须维持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必须建立起一个长期有效的心理干预部门,全国的专家要轮流到这里来工作。我们还必须依靠当地的力量,培训大量当地的心理干预专业人员,只有他们才有可能把心理干预工作坚持下去。”
汶川大地震,不仅震塌了房屋,也震碎了人们的心,太多的心灵,因为恐惧、悲伤而变得异常敏感,整个社会,还需要学习怎样保护这些脆弱的心灵。
5月20日深夜,成都和四川省的电视台,突然一遍又一遍播报余震预报通知,播音员表情肃穆、语调悲凉,听起来更像“讣告”。没有任何科学的解释,也没有指导市民躲避和疏散的知识,播音员单调冰冷的声音,把本来就深陷余震恐惧的成都市民,拉到更加恐慌的深渊,整个成都市的市民纷纷慌忙涌向室外。
“我当时听到收音机里通告的感觉,就好像在说:我们没办法了,自己逃吧,没有人能救我们了。我是精神科医生,我也感到这样无助和恐惧,更不要说普通人。”程文红当时正在绵阳,她说,灾后心理干预,并不仅仅是针对灾民,公众的心理反应也要重视。“媒体应该怎样播报信息,才能让大家既了解真相,又能对事实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不至于引起恐慌,这些都是今后应该注意的灾后心理问题。”(文中部分未成年采访对象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