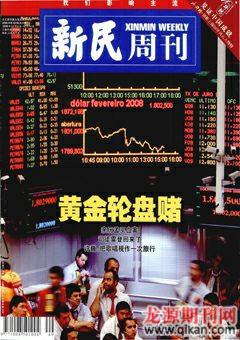故乡的墓碑
黄 平
作家内心的摇摆、犹疑与痛苦,注定了这部作品叙事的尴尬:一部为家乡立碑的史诗性作品,选择了由一个疯子来讲述。
贾平凹是本次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中最著名的一个。他的《秦腔》出版于2005年,距离前一部长篇小说《病相报告》,已经有三年的时间。某种程度上,进入新世纪的贾平凹,一直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写作资源的紧张。这几年,他很确信自己“怎么写”,反而不好把握“写什么”了。
毕竟,从70年代末初登文坛以来,贾平凹所创作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是面对家乡商州写作,叙述“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相遇。80年代的贾平凹,相对乐观地以《小月前本》、《浮躁》记录“改革开放”的乡村,“城市”扮演着“乡村”的拯救者,主人公困境中的选择往往是“到城里去”。90年代以后,自《废都》开始,贾平凹更在乎的是城乡之间的紧张关系,《废都》、《白夜》分别从社会上层、下层两个层面记录着“乡下人进城”的悲剧故事;《高老庄》、《怀念狼》反向地叙述了“城里人返乡”的失落与茫然;夹在二者中间的《土门》,更是直接地揭示城市对乡村的吞噬,由于土地改造,“西京”郊外的“仁厚村”化为乌有。
在这样的叙事谱系上,经历了《病相报告》转向革命历史与传奇爱情的失败后,《秦腔》注定是贾平凹三十年写作生涯集大成的作品——诚如贾平凹在作品后记中所说的,这部作品是故乡的墓碑。作为高度自传性的作品,《秦腔》的主要人物以贾氏家族为原型,而且,作家通过家族的命运,记录城市文明不断挤压下的棣花街,土崩瓦解的鄉情风俗与礼教世界。
一个大作家一生总要写这样一部作品,向被历史埋葬的童年与故乡致敬。不过,这一类作品容易沉溺于充满自恋的回忆中,任由软弱的抒情戕害作品的艺术价值。幸好,写作乡土命运三十年的贾平凹,对故乡的“真相”有深切的体味,“树一块碑子,并不是在修一座祠堂”.一方面,作家怀念着幼时“腐败的老街”与“湿草燃起熏蚊子的火”;另一方面,作家哀悼着当下故乡的塌陷,悲悯地注视着那些下煤窑、捡破烂的男人与打扮得花枝招展进城去的女人。贾平凹没有回避自我的分裂:“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与痛苦,我不知道该赞美现实还是诅咒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
作家内心的摇摆、犹疑与痛苦,注定了这部作品叙事的尴尬:一部为家乡立碑的史诗性作品,选择了由一个疯子来讲述。小说第一句话是直接干脆的表白:“要我说,我最喜欢的女人还是白雪。”不过我们随即得知,这个叫“引生”的“我”是个疯子,小说开始白雪就嫁给了当地望族夏家最出息的后代,大学毕业后留在省城从事创作的夏风。疯狂的引生偷来了白雪的红色胸罩,又在灵魂的谴责中出于惩罚阉割了自己。就是这样一个陷入无望的爱情中的痴汉,一边念念叨叨着内心的爱恋,一边絮絮叙述着清风街的历史,以及他所见到的荒唐混乱的现在。在引生的疯言胡语中,清风街家家户户的“生老病离死、吃喝拉撒睡”渐次展开。
在这个意义上,贾平凹有意将《秦腔》写成了“叙述人”不可信的“伪史诗”,或者说,以反讽的方式完成了当代文学的史诗写作。这种分裂同样制约着故事的编织,贾平凹始终怀疑那类结构清晰技巧娴熟的“故事”,能否呈现复杂的故乡生活?在《秦腔》中,贾平凹继续着《高老庄》开始的“无序而来,苍茫而去”的笔法,以“细密流年”的叙写,“尽量原生态地写出生活的流动”,纪念着“秦腔”所代表的传统与乡土的消亡。毕竟,面对日益荒芜的世界,除了勉力讲好故事以外,作家何为?故乡已死,不朽的是文学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