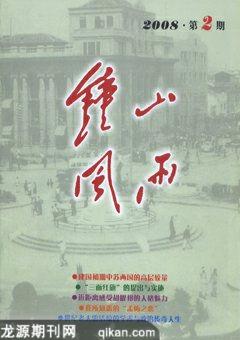鲁迅研究专家陈梦熊
周允中
陈梦熊,笔名熊融,1930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工人家庭。他是建国后上海滩较早研究鲁迅的专家之一。
受累胡风,退休才毕业
建国初期,陈梦熊由中华职业教育社转入上海诚明文学院,后入上海学院中文系读书。他晚间进修,白天在海燕书店当校对,后来该校并入复旦大学,他因为家中经济负担过重,就停止了学业。1951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成立,陈由于工作认真出色,升任为助理编辑。
1954年他响应国家号召,以调干生的身份考入厦门大学。离沪之前,他委托新文艺出版社副社长俞鸿模、编审耿庸写了几封介绍信给厦门大学的老朋友,请他们予以生活方面的照顾;还替总编辑王元化给福建省委的个别领导带了一些书籍。1955年全国展开反胡风集团的运动,厦大党委要求,凡持有胡风分子的信件,必须交出来。于是陈梦熊就将与耿庸来往的几封短信交给了学校的党委书记。不料,过了几天,全校召开大会,会上竟宣布陈是胡风集团反革命分子,当场由校警押出会场,隔离审查。后被厦门市公安局正式逮捕,关押在看守所将近一年之久,而且认定他是胡风集团安插在厦门大学的一枚钉子。后经调查没有实据,直到1956年的九十月间,才被释放,而且立即由校方送回上海了事。于是陈只得停止学业在家,后来经过上海市出版局党委的干涉,厦门大学才作了初步平反,并转入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工作。但是在他的档案材料上,作出了“受有胡风反动思想较深的落后群众”的结论,并受内部控制。
“文革”期间,陈的孩子去东北军垦农场工作,造反派又在他儿子的档案上,加上了“胡风思想影响分子”的结论。他儿子返沪探亲,问及此事,陈无以回答,只好找当时的工宣队了解,结果造反派在大会上宣布,这是经办人看错了档案。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他调到上海社科院,人事干部前来落实政策,此时胡风已经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陈梦熊被内控近30年的重负才算被解除了。1991年,他听说国务院有文件,凡是过去遭受冤假错案的大学生,平反以后,可以补发文凭。于是他去信给厦门大学学生科,终于盼来了迟到近40年的大学文凭。而此时,陈梦熊已经光荣退休。
文革受辱,求死跳粪坑
陈梦熊在文革期间,曾跳入奉贤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的粪坑自杀,这是当年轰动文艺界的一件大事。陈也成了干校名噪一时的新闻人物。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文革之中,大家都喜爱收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各种小报、传单和各种各样的毛主席讲话、文章、诗词,陈梦熊也不例外。他尤其喜爱收集各种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而且将各种不同的版本互相勘比,寻找其中的不同点,把文字和内容不同的地方抄录在当时通行的版本上。例如《纪念白求恩》,老版本上是《学习白求恩》,又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中,在对待优秀的文学遗产上,旧版本上只提继承,通行本上才改为批判继承,这本身属于编辑过程之中精益求精,不断完善的正确做法,也是从事编辑这个行业的人,从中学习,提高自己驾驭文字能力的途径之一。但在文化大革命之中,这就成了破坏《毛泽东选集》的滔天大罪了。当时陈梦熊发现《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这篇文章的注释里,曾经引用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的一段话:“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付诸实现。可是,这个希望失败了。”但是,在通行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收入的《论联合政府》的文章上,清清楚楚写的是:“这个希望落空了。”为此,他写信给中共中央毛选出版委员会,提出自己的意见,希望在文字上能够一致。今天来看无可非议,这是一个读者本着对毛选负责,对编辑工作精益求精提出来的正常意见。后来,这部《毛选》被他的侄子借去阅读,归还的时候,陈梦熊并未发现他的侄子已将自己用钢笔改动和添写的地方全部用墨涂掉了。
在出版社深挖“现行反革命”的时候,有人怀疑陈的藏书之中可能窝藏中央文革领导的黑材料,于是就用卡车将他的藏书全部抄走,在整理的过程之中,发现了这本被涂黑了的《毛泽东选集》,于是立即召开全社大会,公开宣布陈是破坏毛泽东著作的现行反革命,对陈的辩解,反驳说:“毛泽东的著作你有什么资格提意见。”这期间还对他进行了假审问、真隔离、强迫签字等违法行动。陈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终于跳进了所谓“远东第一大粪坑”中,寻求自尽。后来在奉贤县人民医院医生的及时抢救之下,陈的命是保住了,但给其所做的政治结论依然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三聚三散,藏书志不渝
来到陈先生在杨浦区的新居,抬头能看见的便是靠墙一架到顶的各种书刊杂志,和他的坎坷命运一样,他的藏书经历了三聚三散的悲惨历程。
早在初中读书的时候,陈梦熊就喜爱在马路上的书摊淘旧书,尤其喜欢新文艺的书刊,在读大学的时候,他的藏书就已经达到数千册之多。他被厦门大学强行退学返回上海时,父母告诉了他一件使他伤心欲绝的事情。原来他的一位冯姓朋友,当时正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念书,因为爱好文艺,喜好阅读,经常来他家聚谈,同时也经常到新文艺出版社来找他交游,在反胡风运动之中不知道什么原因受到株连,更殃及池鱼,将陈的全部藏书都抄走了。尤其是他收藏多年的一大批有关鲁迅研究的书信和资料作品,再也不知下落。
文革之中,由于怀疑他窝藏中央文革领导人的黑材料,将他的藏书全部抄走,后来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后,书刊却未能全部归还。一部分是被他人未经同意借用去了,或者说是窃拿走了。还有人自作主张、自说自话将他的藏书卖给了上海旧书店,只交给他一张收据凭单了事。这种藐视人权和法律的做法,陈一提起来就愤忿不已。所以当陈梦熊从出版社将书拉回家的时候,原先的藏书已经七零八落,损失不少,真是十分可惜。
第三次的损失是最具有传奇色彩的。藏书发回以后,由于常年在干校劳动,陈常常不在家。附近的几个初中生早就知道陈的家中藏书丰富。于是就打起了他的主意。这些学生多次聚首商议,绞尽脑汁,设想好了一套周密的计划,并做了精心的安排。当时陈居住的是老式公房,每个门洞上下两层10户,厨房、厕所设在楼下,大家公用,陈住在楼上9室。这些学生经过一番分工部署,决定采取行动。他们趁陈的妻子下楼去洗衣服的时候,几个人悄悄潜入陈的室内,将床底下的藏书先行取出,放在楼梯旁的公用储藏间里,并且指定一人上前去和陈妻搭话,分散她的注意力,当发现陈妻将要上楼的时候,这些孩子就以大声唱歌或者吹笛子作为暗号,招呼楼上的行窃者立即停止行动,等到陈妻进入房间,除留一人盯梢以外,其余的人马上将储藏室里的书籍抬下楼梯,迅速藏匿起来。一天,陈妻发现床沿遗落了一些书刊,移动纸盒的书箱,才发觉里面已经空了一大片,马上叫陈回家,经过分析研究,估计是附近的学生所为,后来找到他们的班主任,经过劝导和批评教育,这些学生才把偷窃的书刊陆陆续续地归还了。其中有部分书刊因为转借给了别人再也无法归还。后来陈先生在一篇文章之中表达了自己的豁达大度:“从窃书的过程看,尽管他们的手段不可取,但发生在文革的混乱时期,应该是可以谅解的,因为他们偷书并不是去卖钱,而是自己酷爱读书,却无法得到满足,通过读书消化成为自己的文化修养,增长了知识,这有什么不好呢?”这段话正反映了这位民间藏书家藏书著书的高远志向和宽广胸怀。
研究鲁迅,贡献真不小
陈梦熊最早开始研究鲁迅的生平和著作,大约在上世纪50年代初。那时,陈在纪念鲁迅的座谈会上,结识了王士菁先生,并且将自己编著的油印本《鲁迅书目著录》送赠给了王先生,赢得了王士菁先生的赞赏。
当时在虹口区的武进路上,由冯雪峰主持成立了鲁迅著作编译社,由于初创伊始,王士菁便委托陈帮助他们寻找一些有关现代文学的资料。陈梦熊有一位许姓的朋友,平时喜爱收藏新文艺作品和民国时期的期刊,于是陈就当起了义务跑腿,在许家和编译社之间来回运送书刊,直到编译社迁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止。然而,陈的热情与好学,对工作的踏实和任劳任怨,获得了编译社同仁的一致赞许和好评。经过王士菁先生不余遗力的推荐和介绍,终于使他当上了海燕书店的校对员。
从上世纪50年代起,陈梦熊就专门从事鲁迅和现代作家的史料挖掘和考证。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尤其是对鲁迅佚文的发掘共有十多篇,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功绩颇为显著。例如,他对鲁迅早年的译文《哀尘》的长篇考证,从过去人们认为鲁迅正式翻译外国作品始于1909年的《域外小说集》,提前到了1903年的《浙江潮》上;通过鲁迅与周作人的通信,揭示了当年鲁迅在文笔上推崇新民体(梁启超)和冷血体(陈冷血)的原因和实质。
陈梦熊认为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提到的王育和与王方仁,是两个政治背景完全不同的人,他的阐述使得许广平先生深为信服,并且在当时的《文汇报》上,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又从1914年10月4日出版的《教育周报》上,发现了鲁迅的《生理实验术要略》一文,该文不仅是鲁迅集外的佚文,而且是他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生理教员期间唯一正式发表的科学实验论文,这对研究鲁迅当时的教学和思想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陈梦熊考证和挖掘的上述的鲁迅佚文和佚信大约十余篇,全部被收入1981年再版的《鲁迅全集》之中。鲁迅编辑委员会还肯定和吸收了他的正确意见100多条,他还考证出《鲁迅日记》之中人所不知的,如翟永坤、陈昌标、韦杰之、熊文钧、黎仲丹等多人。
有的学者指出:陈梦熊在鲁迅研究中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就因为他在鲁迅研究之中引入了传统文学的考据学,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现在陈梦熊的著作《鲁迅全集中的人和事》,已经多次再版,迄今为止,有关鲁迅研究的文章已经有60多万字,他准备再加整理以后,予以补充和扩大。
文墓文幕,掘开又揭开
陈梦熊有一本新著《文墓与文幕》,这个书名取自钱钟书先生对他的评价,钱先生曾经幽默地称赞他“擅长发掘文墓和揭开文幕”;陈福康教授也表示,现代文学成为专门学科以后,好多作家将朽和已朽的作品,被陈梦熊发掘了出来,而他揭开文幕的史料上有很丰富的精神食粮,这对了解中国百年文学史,宏扬爱国主义,鉴赏文学名作,学习文坛前辈是大有好处的。
在这本《文墓与文幕》的著作中,他钩沉出杨村人是如何从中共领导人蜕变为第三种人的,鲁迅对柔石的关怀和栽培,陆蠡一些不为人知的往事,孙冶方是如何参与《鲁迅风》的争论的,使许多研究现代文学感到疑惑的学者洞悉其窍,豁然开朗。
陈梦熊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最近,他又在《太原日报》上连载《20世纪文化名人钩沉》的文章,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写出传主独特的个性,给读者以无穷的启迪和激励。
陈梦熊之所以对这项工作乐此不倦,孜孜矻矻,关键是他认为“史料工作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任何领域的学术研究,如无深厚的史料学做基础,是难于深入和提高的”。有的学者曾经替陈梦熊总结了三点:首先是眼勤,广泛涉猎,关注细节,善于思索;其次是口勤,趁当事人或者相关人还健在,多向他们询问,核实史料,解开疑难,寻找新的线索;最后是腿勤,查访资料要奔波于图书馆、档案馆、资料馆、藏书人家,还要实地走访故居、母校、师长、朋友,于不经意之中发现重大的内容和主题。
现在,陈先生已经是望八之年,腿脚多有不便,但是来他家寻访和求教的人川流不息,他自己也依然笔耕不辍。走笔至此,作者衷心祝愿他:凌云健笔探奥微,百尺竿头更上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