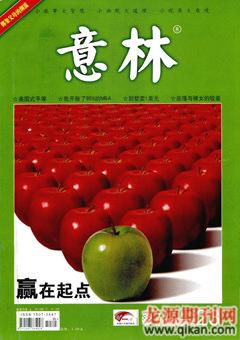海犁的故事
陈芸英
时序进入暮冬,冷风过境,一波波寒流来袭,伴随着倾盆大雨;这种天气对出狱刚半年的海犁,无疑是另一种折磨。
他瑟缩在大外套里,走几步路便气喘吁吁,一开口即咳个不停。好不容易走到三楼顶,他停下脚步,努力做深呼吸,清瘦的脸庞,更加憔悴。
这顶楼就是他的天地,占地一半的阳台种花养狗,另一半则是房间,地板上堆放着他编织中国结的材料,各种色彩的丝线穿梭交叉,宛如他的人生。
因为14年前的一场租船事件,扭转了他的一生。
海犁说,那年,他的一位朋友向他借船去大陆载运洋烟,给他20万台币当租金。但他回到高雄却被捕。原来船到大陆不是载洋烟,而是载毒品,他近乎吶喊地为自己辩护,但并未被检方所采信。法官最后认定他就是幕后主使者,判他无期徒刑。
踏进监狱,像是进入黑暗世界——阴森的高墙、冷漠的铁窗、灰色的囚服和一个编号。
他被分配到制作“中国结”的工厂服役。一开始,他只做些简单的编织,然而出于对中国结的天分,借着参考相关书籍和自己的创意,他竟做出许多别出心裁的中国结。监狱的日子,就在他的指掌间搓揉缠绕流逝。后来,他加入监狱写作班,过去跑船捕鱼近20年,航遍各大洋及到世界各国的阅历,都成了他创作的养分和灵感的源泉。
他试着把讨海人的生活化成篇篇文字,这些创作帮助他释放出心里的负面能量。他以“海犁”为笔名发表作品,多次刊登在台湾的报刊上。
牢狱岁月最痛苦的不是身心的煎熬,而是亲情的割舍。他记得妈妈第一次到监狱看他时,难过得说不出话来。他安慰她,“你就当我出海吧,我国中毕业就跑远洋,每次遇到台风天,你都很紧张,现在不用烦恼了,因为这里没有台风!”49岁的海犁一直未婚,母亲是他主要的精神支柱,后来他写信安慰她:“这十几年来,我的运气如果稍微差一点,早就死了;能活到现在,算命好。”
母亲仿佛得到了安慰,但父亲却始终把心事埋在心底。他是那种威严十足的职业军人,感情的表达含蓄不露白。海犁入狱后,两人的交流变得有限。不幸的是,父亲在他服刑期间身体每况愈下,最后因癌症过世。“他一辈子要面子,家人揣摩他的心意,不希望我系着手铐脚镣叮叮当当上香,所以当我知道消息时,已经天人永隔。”海犁无奈地说道。他在狱中强忍哀伤,但某夜就寝时,却忍不住悲从中来,捂住棉被放声大哭,“这种痛,没有经历过的人,永远无法了解。”
人生确实是难解的课题。原本他以为自己已走到谷底,不会再有更惨的事了,没想到就在服刑期满10年达到假释门槛之际,“有一天,我咳嗽咳出血丝,以为是重感冒,但咳了好一阵子都没好,我去照X光,医生发现我左肺部有肿瘤。”最后证实他患了肺癌。
“我万万没想到,在台中治病的日子,不但治疗了身体,也解开了我的心结。”这里有很多跟海犁同病相怜的人,跟他们相处一段时间后,海犁的心情竟有180度的大转变。
同房一个不到30岁罹患淋巴癌的狱友做骨髓移植时,需要家人为他“保外就医”,但他的母亲却拒绝,怕他一出狱又为家里带来麻烦。
“连我妈妈都不愿意保我,我只能猜想自己以前做得太过分了,这是我该得的惩罚吧!”这句不经意的话震撼了他。
“我反省自己,虽然我自认为是冤狱,但当初朋友为什么会借我的船从事不法勾当?难道不是因为自己过去曾有走私方面的不良纪录,只是没被抓到而已?”想到这里,纠缠十多年的心结终于解开了。
此外,同房两位对生命看法截然不同的狱友,也给了海犁深刻的感触:一位右手中风后自暴自弃,每天看起来奄奄一息,毫无生气,不到一年就死了;另一位被子弹击中下半身瘫痪,却坐在轮椅上行动自如,乐观进取,每天写字、画画,偶尔制造欢乐,激励大家。海犁说:“我看到一股残缺又旺盛且独特的生命力,给我的鼓舞,远超过我的想象。”此后,人家问他坐牢苦不苦,他都说:“坐牢苦不苦,需看心境!”从1994年到2006年中旬重获自由为止,他一共在牢里待了12年。
接他出狱的是住在桃园的弟弟和弟媳。再度拥抱对方,恍如隔世。他们按母亲的吩咐准备传统的“跨火炉”帮他去霉气,接着按规定赶回户籍地澎湖法院报到,同时回到老家与母亲团聚。由于得定期回诊看病,海犁多半时间都待在桃园。
不幸的是,他弟弟还在念小学的儿子也是癌症患者,整个家族有五人罹患癌症。海犁说:“没想到,疏离12年的亲情,却因此拉近距离。”他们彼此间打开心怀,讨论未来可能遇到的情形;他们了解对方的疼痛,给予意见,没有隐瞒;他们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天,知道感恩;更重要的是,他们也参考彼此的生命态度,携手共渡难关。
(田生摘自《读者文摘》图/孙红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