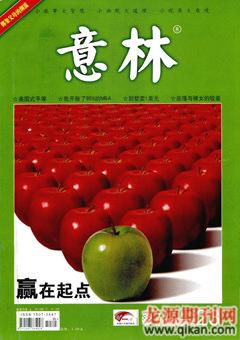被拒绝的死亡
鲁 娃
如果说,生命是一种美丽,那么死亡就是美的毁灭。但对于法国人尚达尔·赛比尔女士来说,生命已不成其为美丽,所以死亡就成了一种渴望。
6年前,赛比尔女士得知自己患了医学上称为“感觉神经细胞瘤演变性鼻腔鼻窦肿瘤”,这是很少见的不治之症,迄今为止,全球只有200例。随着病情加重,赛比尔女士备受身心双重煎熬,原本美丽的一张脸不可遏制地破相而变得惨不忍睹。她觉得自己就像活在暗无天日的地狱里,面对魔鬼的啃噬,怎么爬也爬不出去。
她不堪忍受,她想告别再挣扎也无奈的躯体。她希望在意识还清醒的最后时日里,把家人亲友都召集到家里来,举办一个温馨而美好的烛光告别晚会,然后在黎明到来的时候,静静死去。今年52岁、身为教师的赛比尔不乏法国人的浪漫,她愿意生命有最后的璀璨。今年3月份以来,她通过律师向所在的第戎市高级初审法院提请紧急诉求,要求破例允许主治医生对她采取“安乐死”。她还给萨科奇总统写了一封信。她说,她要表达的意愿在于,她热爱生命,所以不希望采取有悖生命尊严的自杀方式。萨科奇总统读信后被她深深打动,当即敦促总统医学研究事务顾问召集全国顶级专家对其病症重作诊断,以确认所有治疗手段是否穷尽。鉴于赛比尔女士已无力远行,总统府派出的一干人员专程赶赴第戎市她家里为她会诊。
于是,一位女性最私有的“内在自由”走入社会视野,吸引了舆论关注,成为公众话题中一个绕不开的漩涡。人们把她病前病后面貌美丽丑陋的两极照片贴到网上,对她直面苦难的勇气和有关生命的终极思考表示由衷的敬意。网上帖子雪花般飞扬,飞扬中重叠了一双双饱含热泪的眼睛。
然而,尽管医学专家同样作出了不治的确诊,尽管连法官也同情赛比尔女士万劫不复的境遇,依据现行法律,法院只能无可避免地驳回她的“安乐死”请求。事实上,法国不同于荷兰、瑞士、比利时,至今尚未通过有关“安乐死”条例。虽然法国人早在心理上认同了“安乐死”,多次民调赞同率都在70%以上,而且每年至少1000例至1500例非合法“安乐死”在暗地里悄然实施,受众不乏虔诚的宗教信仰者。可鉴于教会官方长久以来的阻力,法律意义的“主动安乐死”以及“协助自杀途径安乐死”仍同凶杀罪、见危难不救助罪如出一辙,最多可判30年刑事监禁。
法律就是铁律,来自总统或者平民的关爱体恤都无法超越。不过现行法律也留下了一道豁口,那就是所谓的“任其死亡权”,即用镇静药物辅助,置临终病人于半昏迷状态持续两周导致自然死亡。也就是说,选择这一终结方式的病人必须忍受缓慢的痛苦,在洞黑的时空深渊里踽踽独行,没有任何搀扶地走完生命最后一程。这是何其惨烈的临终惩罚,于生于死都是。赛比尔女士固然是勇敢的,即便勇敢,她也不敢窥视这么一条被死神一寸一寸吞噬的地狱走廊,她把这种懦弱理解为人性的另一面。所以,从一开始她就排斥这个豁口。就法律而言,这或许也算一种人道关怀,但之于人性,更多的舆论则认为是残酷与虚伪的。
无疑,这是一次被拒绝的死亡,其内涵象征着生命的尊严被无情抛弃。赛比尔女士支撑至今的柔韧意志崩溃了,理性再无法与绝望抗衡。她只能步向极端。虽然诉求驳回之后赛比尔女士获得了更多更多的声援,希望能在尴尬困境中寻找一种相对的人道途径。3月19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曾在“左派”政府担任过卫生及人道事务部长的现任外交与欧洲事务部长布希纳尔发表讲话,呼吁为赛比尔女士创设一个“法律例外”,并声称既人道,又必要。
但是,赛比尔女士听不到了。同天上午,她被发现死在第戎市的寓所里。门窗紧闭,窗帷低垂,赛比尔女士仰卧在自己干净整洁的床上,悄无声息地去了她想去的地方。亲人和孩子都不在身边。她遵循夙愿死在黎明,却无人送行,没有烛光,也没有温馨的告别晚会。她的脸容看起来平静,却藏匿了无边的憾恨。
自然,她被推上了尸体解剖台。她赤身裸体躺在冰凉毫无人性的金属板上,被手术刀肢解着需要肢解的部位,生命的尊严再一次被践踏。她是知道的,在吞服巴比妥酸剂之前,她就认定自己终将躺在这里。但她已然没有别的选择。结论当然是非自然死亡。致死的巴比妥酸剂在荷兰、瑞士以及比利时的药房里均有出售。
一个女性关于生命关于死亡的一页沉重合上了。赛比尔女士的悲剧就像春天湿漉漉的风,淅淅沥沥渗入到目睹并参与了这一事件的所有人心中,促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如何把属于私域的“内在自由”推进为社会法律公认的权利,从而进一步完善新的社会环境下新的人权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赛比尔女士无愧为殉道者的称号。
(青衫客摘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