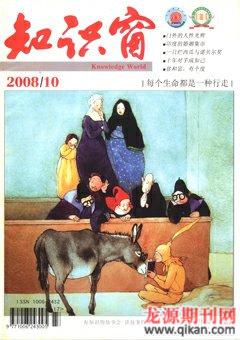月亮之下,无有忧烦
羽 毛
在家乡小镇,我度过了单薄惘然的少年时期。
那时小镇可谓“民风淳朴”。年轻男女当街都不说话。男人一律中山装,女人的衣服也中规中矩。唯独她,高挑娇艳,微微昂着下巴,像一只离群的鹤般,在灰扑扑的街上矜持行走。所以,她的每次出现,都让永远穿着改良旧衫的我,惊若天人。
夏天,她戴顶镶有精致绢花的宽檐帽,脸儿沉默,像位寂寞的贵族。每条裙子都颜色缤纷,包裹着她玲珑的身姿。摇曳生姿,是看了她的步态,我才明白确切的意思。
冬天,她裸露着修长的腿,呢子外套下是一条短得让人羞愧的皮裙。男人迎面走去,总要别过脸。走过了,又马上回头看,往往要撞到水泥柱子。女人则大声咳嗽,在她身后指指点点,骂她有伤风化,骂男人没出息。
她只是淡然微笑,若一枝花开在高树,若琴弦泠泠松寒音,飘逸脱俗。
那年她18岁,高中毕业后在小镇一家花店帮工。她的美滔滔不绝地流泻在陋镇,流泻进了少男少女的心里。来年,美悄然发出更多枝芽,有些女孩不顾父母的斥责,换上个性的衣衫,走在此起彼伏的男生口哨声里,俏丽欢悦。
后来,她去深圳打工,迅速晋升,并与一位身价不菲的金领相恋成婚,成了小镇的传奇。旁人不以为然,我却知道是这份刺破小镇沉闷空气的鲜活气度,才造就她的精彩。
大学时认识了另一位女孩,少言寡语,成绩极好。她说自己的理想是做学者,行事却颇有江湖气:和男生喝酒,一律用大碗,偶尔直接用瓶。男生哧溜倒在了酒桌下,她还不醉,拿起筷子敲打桌子,唱:“清风笑,人多寂寥……”很多男生暗恋她,她挑了一个,毕业后就嫁了。
再听到她的故事,仿佛小说般陡然转折。她嫁的人是独生子,有些被宠坏的脾气。她的婆婆总是看她不顺眼,觉得她根本不配进自己家门。她找了份工作,想博回一局,却遇上个苛刻的女上司,简直是命里克星。不巧,她的父亲罹患癌症,撒手西去,母亲成日以泪洗面,全靠她强打精神,温言相劝……祸不单行。
我们偶然在一次聚会中相见。见面之前,我担忧她会变成怨天尤人的祥林嫂,谁知,她更加风姿绰约,黑珍珠项链闪耀在白裙之上,笑意清甜。大家聊开了,喝多了,就有人说起她的近况,很是为她惋惜。她淡淡地说:“之前是很糟糕,我干脆辞职读书,刚考上北大经济学的研究生,继续学者梦。母亲现在早上练太极,晚上去跳舞,不让人操心。至于婆婆,日久见人心,她会喜欢我宽待我的,总有一天。”
众人叹服,举杯同饮。
工作中还采访过一个80后的新富。他高中毕业开始四处闯荡,曾经借高利贷开过一个书店,结果被冒名书商骗走了全部现金,颗粒无收。他三天没有吃东西,还被讨债的人找到,用脚踩住头,吃了一嘴的泥泞……他用清水洗尽脸,拍打身上的灰尘,找到附近一家面馆,要了两碗牛肉面,放上很多醋和辣椒,酣畅淋漓地吃完。然后,他请店主拿来纸笔,写下欠条,说等自己飞黄腾达之时,一定加倍偿还面钱。
店主瞪着他,突然笑了,撕掉欠条,说:“就凭你鼻青脸肿、分文没有还具有这份淡定的气度,我相信你。”
那晚,他就发誓,有生之年绝不让自己再饿肚子,也绝不辜负面馆老板的信任。
如今,他在当地开了连锁的家具经营店,每年利润丰厚。在他巨大的办公室里,摆放着一台三开门的冰箱。他给记者拉开,里面摆得满满当当,一桶殷红的樱桃,一排蒙牛牛奶,一打可口可乐,一堆花样繁多的巧克力……
有些让人可笑。他自己也笑着说:“这些吃的让人心里踏实。也是勉励自己小心行事,不要重蹈覆辙。”他神情认真,让人肃然。
有时候,遇到生活、工作或者思想上的难题,我就想想他们,一个美女,一个学者和一个商人。
无论是挑战小镇的陈年陋习、消除家庭的隔膜,还是对抗摔至谷底的命运,始终相信月亮之下,无有忧烦,岁月之上,无有壁垒——这种豁然气度,管他战役结局,已然所向披靡,提前取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