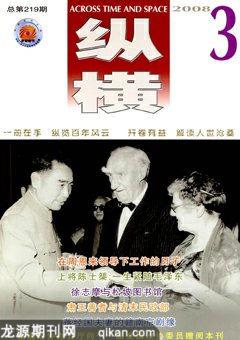肃王善耆与清末民政部
爱新觉罗·连绅
1907年,清政府任命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主管民政部。到1911年,善耆任民政部尚书(后改称民政部大臣)共计4年4个月。当时的民政部职责范围很广,相当于现在的内务部、民政部、公安部等部门。除此之外,善耆还分管诸如重建海军及推行宪政等事宜。在短短几年之间,善耆为挽救行将就木的清王朝,做了一些工作,接连创出了几个“中国第一次”。
革新和巩固警察制度
善耆任工巡总局管理事务大臣时学习欧洲及日本的警察制度,开始时在工巡总局属下设立警务处,在北京东、西城工巡分局设警巡、巡捕,并设巡捕处160余处,另设立了警务学堂培训巡警。调至民政部后,善耆继续改革和完善警察制度。
从来,清朝京城的警务由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捕盗营等担任,缺少统一的警务机关。他们多半只知欺压百姓,不知守护之责。自从善耆采取近代化的警察制度并设立了相应机构,大力培训巡警,扩大高等警官学堂等措施,经过数年努力,中国警察制度得到创立,京师的治安得到很大的改善。京城内第一次出现了派出所。巡警被派到各个街区负责日常警务,第一批木制的“巡警阁子”开始布置在繁华的街道、路口。1908年光绪和慈禧相继去世,市面人心惶惶。经过善耆的安抚及加强警戒,北京没有发生任何治安事件,致使光绪的殡葬大典和慈禧的葬仪得以顺利举办。参加这两次大葬礼的外国使节感叹说,“在此复杂的形势下得以保全社会安宁,完全是肃亲王指挥调度有方的结果”。

善耆自幼爱好习武,因此常常亲自带领巡捕去捕盗、抓赌局、禁鸦片烟馆及暗娼等,并设立习艺所来收容患病及老年娼妓,给予治病及学习生活技艺,使她们有生活出路。还有时穿着奇服怪装故意到街上行走,如果巡警能盘查寻问,善耆便褒赞该巡警尽责。
当时清朝统治者惧怕革命,已成惊弓之鸟。而一些官员则以抓革命党为由,胡乱逮捕民众,以求升官发财。有一日侍郎赵秉钧拿着一口刀见善耆说:“这是今天在前门外某妓院搜到的,刀上刻有尚文程三字,恐怕是革命党人之物。”善耆说:“此刀恐怕不是革命党人的,如果是革命党人,没必要非把名字刻在刀上不可。”赵说:“恐怕不是真名。”善耆笑着说:“即使是假名,革命党人也不会刻名留在刀上。令巡捕队三日内查出这个叫尚文程的人,可辨明真伪。”命令下达后很快查到了名叫尚文程的人。经审问,他不是革命党,只是逛妓院时把刀遗忘在那里。
关于“地方自治”的第一个具体方案
1909年后,善耆亲自起草的长达1500余字的奏折,是按照“九年立宪”而制定的地方自治规划。地方自治规划是按照日本及欧洲国家立法和执法两权分立的原则制定和执行的,内容涉及自治章程的制定,议事会、董事会的筹建,户籍法的施行以及警政、人口普查等诸多事宜,并包括每一年对前一年工作的考核与审定。此规划得到摄政王载沣的采纳。按此规划已完成了宣统元年及宣统二年的规划,宣统三年五月善耆与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勖不和,被调任理藩部大臣,但是宣统三年的规划也基本完成了。此后清朝灭亡,该规划中途停止。
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
善耆在推行地方自治工作中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安排了人口普查工作。虽然此项工作也因清王朝倒台而中止,但是留下了中国人口发展的宝贵的参考数据。因为中国人多地广,历史上很难提出准确的人口及户数的数据。过去说中国人口大致有4亿人口,是根据1838年(道光十八年)颁布的全国人口数字40900万人而来,而此数字是按照大清国18个省上报的数字,并不包括内外蒙古及西藏地区人口,各省上报的人数也是当时地方在册的户数的估计数,并不是有计划有组织的统计数。20世纪初当时驻清朝的美国公使对中国人口进行过分析研究而提出的人口总数不超过27500万人,此数也是根据一些历史资料分析而来,也不是进行人口普查而得出的。
善耆任民政部尚书不久,研究各国进行人口调查的方法及配合推行地方自治工作的需要,专门制订了人口普查计划,并由光绪三十四年(1909)开始至宣统二年(1910)十月完成户数登记。计划宣统四年(1912)十月完成人口调查。但因清王朝灭亡,善耆的人口普查工作也中途而废,黑龙江、山西、甘肃、四川各省及乌里雅苏台、伊犁、绥远城、福州、广州、汉口、杭州、凉州等地驻防军管辖户数尚未报来,西藏等西部边远地区尚未施行地方自治未进行登记。但是就以上统计户数有23400809户。按当时一般大户算一户人,因此每一户平均十口人计也有23500余万多人。如果全国都报来有可能达到4亿人口。此数字因只有人口普查工作开始一年的数字,远没有反映全部数据,只能作为参考数据。
甲午海战后的第一个重建海军方案
善耆任民政部尚书时期,对清廷海军现状进行了调查,并上书朝廷“筹办海军基础一折”,得到清廷重视和采纳。1909年,清廷降谕:“方今整顿海军实为经国要图。着派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尚书铁良、提督萨镇冰,按照所陈各节,妥慎筹划……”经过3个月的悉心考察,善耆对当时海军的教育情况、舰船情况及军港厂坞等情况作了详细报告,强调了培养海军人才的重要性,提出充分利用现存舰只,加强海军基地建设等主张,并对所需经费上报了预算。这一重建海军方案再次体现了善耆的务实和远见,尽管摄政王载沣对此很是欣赏,但是出自对善耆的猜忌,特别对其权欲的防范,始终不予善耆兵权。

海军重建案是善耆的建议,并由善耆任海军筹办委员之首来解决各项具体事务。因此中外人士都认为设立海军部时,必由肃亲王任海军部大臣之职,但是实际上海军部成立时任命了摄政王载沣之六弟载洵贝勒为海军部大臣,并任七弟载涛为禁卫军大臣掌管陆军。可是当时洵、涛兄弟皆为二十出头的青年,甚至老成谨慎的张之洞也认为二人难以承担如此大任。对海军大臣这个官职载涛、载洵争得厉害,善耆退让了,载沣后来把海军大臣的职位给了载洵。溥侗后来说“大哥(指善耆)真傻,就这么轻易地把海军大臣让给别人了,也不争争。”
着力开展卫生防疫,召开中国近代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
旧时广大民众缺乏卫生知识,很少公共卫生机构,尤其经过八国联军的破坏和地痞流氓的骚扰,造成垃圾脏物到处乱倒致使京城脏乱不堪,疾病流行及缺少医疗机构和相关医师药物。自善耆担任工巡总局管理大臣直至民政部大臣的十年多的时间,致力于改善城市及卫生面貌,做了几件事。
首先,善耆任期内,北京开始有了自来水供应。从1908年开
始,为了使自来水能送进朱门大院及饭店,在东直门外过桥迤北冰窖后身的香河园建了一座高40米的水塔,塔顶系一圈小铃,使风吹铃响,当时在北京也蔚为壮观,可算城外的一个西洋景。水塔全部用进口货,采用钢结构,不算大小铆钉,光各种钢材便达250多吨之多。水罐容积500吨,全是铆活。进塔内螺旋式楼梯直达顶部,站在塔顶内可凭窗俯瞰北京全景。
其次,善耆任职民政部大臣时期,开展防治鼠疫,并以此为契机,召开中国首届国际卫生防疫会议。1911年1月发生了鼠疫。疫情起初在东北某些地区出现,1月15日蔓延到天津,20日在北京也发现了感染患者。鼠疫在一般市民及外国驻京人员中引起了极大恐慌,石炭酸等药物价格暴涨,煤炭奇缺,大扫除用的扫帚都成为珍品。有的囤积粮食,市面流行着歹徒乘机进行暴乱等流言。善耆闻讯后,采取各种措施,对治安及卫生防疫方面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到了春天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也没有发生社会骚动。当时采取的措施有:
①下令收购老鼠集中焚烧,一只老鼠给一文钱,一天至少收购四五百只,多的时候可达几千只,这样短期内迅速消灭了鼠类;

②派医官对所有死者进行检查,如果怀疑死状有异,立即采取隔离消毒、火化等措施;
③发现鼠疫患者时采取文明国家的办法对尸体进行火化,对家人进行隔离观察,病家周围进行严密的消毒灭蚤工作;
④为了防止人心动摇,每天在官方报纸上发表城内死亡者姓名、住址、病状及负责医官姓名等,让老百姓随时了解疫情,起了安定民心的作用;
⑤向百姓教授消毒灭蚤法,同时号召全民防疫灭鼠及其他卫生事宜。
另外,在善耆的授权下,1911年4月3日至28日在沈阳召开了我国首届国际学术交流会,善耆通过外交使团邀请了日本著名细菌专家北里柴三郎及柴山五郎两位博士,以及其他11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这次会议的正式名称为“万国鼠疫研究会”,会期是1911年4月3日至28日。与会代表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会议共讨论了24次。
这是一次高水平的学术会议,日本代表北里柴三郎是一位细菌学权威,曾与德国细菌学家合作创制出破伤风和白喉病的抗毒素,后来又分离出鼠疫杆菌。
会议主席伍连德是广东新会人,先在英国剑桥大学和法国巴斯德学校学习,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天津陆军医院医官。由于他医术高明,学术渊博,在这次会议上被各国代表一致推举为会议主席,当时年仅32岁。
这次会议,也是一次维护我国主权的会议。北里柴三郎到达奉天后发表谈话说,日本方面早已将研究材料调集齐全,会议所要研究的问题“求诸日本可耳”,言意中国政府无提出议案的资格。此论一出立即遭到中国及各国代表的谴责和舆论的批评。会议在伍连德的主持下圆满结束,北里最后也不得不承认:此会为中国及万国之创举,实为医学史上光明之一页。最早的“城市现代化改造”
清朝民政部本来就由工巡局演化而来,因此修建道路、改变京城面貌是善耆从政十余年一直致力的工作。并且通道整修道路及城内布置,为今日著名的东华门大街、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等场所奠定了基础。善耆任民政部尚书期间继续修筑道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市交通,方便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北京修筑的道路虽然没有欧美文明国家的都市道路完备,但也不像日本东京修筑的道路那样,把砂石放在路面上由人脚踩实的原始方法,而是采用机器夯实,所以北京的道路比东京的道路宽阔,分为车行路和人行路。
不仅是京城道路修建工程,民政部还对各地区的山陵修建、河川维护及护堤等工程做了不少工作。尤其需要由中央政府拨款修建的大工程,都必须由善耆亲自审查批准。又如,修路工程费用,以往地方官吏由工程承包人处收取贿赂,因此工程造价很高,那桐任初期民政部尚书时,修筑北京市道路工程造价一清里需要4000两。善耆到职后虽然由于物价上涨致使工本费用增加,但是道路修筑加上水管管道埋设费等加上也不过一清里3000两,此举得到人们的称赞。
京张铁路的修建工程,虽然归邮传部管辖,但是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权势低微,而负责工程的詹天佑是一个技术官吏。修筑铁道用地需要通过很多王公大臣的祖坟。征用土地时,他们倚仗权势,极力抗征,使修筑铁道工程受到很大的阻挠,迟迟不能开工。善耆得知后,亲自到征用土地范围内的肃王祖坟地,向祖先磕头祈祭后把坟墓迁移到他处。由于善耆“从大处着眼”,带头迁了祖坟,其他王公大臣不好继续僵持,纷纷让出土地,保证了京张铁路的顺利完工。1909年9月,京张铁路通车典礼时,善耆又亲自试乘“洋玩意儿”火车往返于京张之间,以向保守派证明火车的安全性。

善耆看到当时交通工具木轮车,跑不快又压坏路面,为此开始从国外引进西洋马车。在大规模修路前善耆首先自费买了一辆西洋马车亲自试乘。此事结果被慈禧得知,以“肃王爷也学洋人了”为由予以责备,还把马车给没收了。后来颐和园也购进了西式马车,慈禧坐得舒服,就又把没收的马车还给了善耆,准许“学洋人”。
善耆结合防疫工作对北京市公共卫生进行了一番整治,建起了第一批公共厕所于市内主要地带。尽管这些公共厕所还很简陋,但毕竟是一次开拓性的工作。
善耆成功地进行了道路的改建,为改变卫生条件打下了基础,为此沿路设立了公共厕所来防止在市街上乱弃污物。北京城在明朝时修过较完整的地下水道渠可排放污水,但是由于年久失修已不能排污了,尤其当时民风对随意在马路上乱丢尿屎不以为耻,禁止在道路上乱放污物是一件移风易俗的难事,为此善耆决定建公共厕所,初步改变了北京的卫生面貌。
设立“国营禁毒设施”
1906年,在善耆的建议下,重新颁布禁止鸦片令,并且规划十年内完成禁止种植、买卖及吸食鸦片烟。但是起初禁令很难使地方政府接受和贯彻,于是1908年4月7日正式成立了禁烟总局,隶属民政部,主持全国禁止吸食鸦片烟及禁种罂粟等工作。
在此期间,善耆又建议朝廷任命他最信任的族弟恭亲王溥伟任禁烟大臣,以加强禁烟领导工作。至宣统二年,已在广东、广西、云南、直隶、四川等九省贯彻了禁烟令,民间也成立了以林则徐之孙林炳章为会长的“国民鸦片禁烟会”,配合官府贯彻禁烟工作。
善耆又令北京内外城警务厅派巡警去严查吸大烟者,还经常亲自带领巡捕查封大烟馆等处,另设立了戒烟局,把吸食鸦片烟者收容起来,配医官进行强制性戒烟工作。当时能够完全戒烟者称之为“戒净”,在京城三个月内得到“戒净570名”。
保护戏剧,改革戏院
在奕劻内阁时期,善耆屡受排挤,颇不得意,于是逐渐接近戏剧、棋艺。善耆嗓音不好,但很爱唱戏。他搭起了戏台,先是叫宫里的梨园戏班到府里唱(叫做王爷“传差”),以后通过“红豆馆主”溥侗(外面称侗五爷)的帮助,组成了肃王府自己的戏班。当时只有醇王和肃王两府才有自己的戏班,而肃王府差不多天天唱。府里唱的戏有两出外面没唱过,一出戏是《吴三桂请清兵》,戏中有睿亲王多尔衮的一段满文唱词,萧长华还带着徒弟到府里学过这段戏文;另一出戏是《郑成功收复台湾》,善耆亲自扮演郑成功。善耆还与当时名伶杨小楼合演“翠屏山”一戏,善耆扮石秀,杨小楼扮潘巧云。当演到巧云严词斥石秀时,石秀想过戏瘾,没完没了地抗辩。巧云一着急,来了一句:“就算你是王爷,也得给我滚出去!”当时四座皆相顾失色,以为杨小楼要遭飞来横祸。谁料,扮石秀的善耆意识到自己的没完没了,乐嘻嘻地“滚下去”了。善耆擅演武生,其武功之勇捷可与外号为“杨猴子”的杨月楼相媲美。常去肃王府演戏的名角除萧长华外,还有谭鑫培、杨小楼、钱金福、梅兰芳、丁永利等。

当时善耆在府里看戏时常有名角儿陪座,边看边探讨。在清末戏曲演员属“下九流”,社会地位很低,所以善耆的作风颇受议论,甚至有人借此弹劾善耆。但是戏剧界人士总是愿意到肃王府唱戏,那时候新加入梨园的新角及徒弟需要找有势力的后台来保护自己不受欺负。著名的戏剧大师梅兰芳在学徒时期,常常肩背着小王子看戏。1955年梅兰芳访问日本演出期间,由善耆的儿子宪立担任电视直播的日文解说,两人是老相识,配合默契,为在国外传播京剧艺术起了良好的作用。
善耆在民政部尚书任上,曾明令在西珠市口内,煤市街南口外设了名为“文明茶园”的戏院,它的规模与当时的广和楼相似。戏院楼上有女座,楼下设男座,以示男女分开,但取消了女人不能到戏院看戏的戒律。这一旧习的革除,在当年的北京,无疑是一件轰动全城的创举,善耆为此得到了“思想开化”、“伤风败俗”的两个名声。
默许党人办报
在中国首都北京自进入20世纪才有了报纸,早几年在外国租界发行外文报纸,后在上海、天津等地也有了中文报纸,但是在首都北京,庚子之乱前没有一家日报,只有叫做《时事采新》的周刊,发行量很小。慈禧曾下令不准官吏看报,除此外并没有别的限制。然而自庚子之乱后出现了一些报纸,却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一些“过激”的言论。后来随着报纸增多,各种的时评性报纸和报道也多起来,因此新闻管理规则就出现了。可是这些规则是参照外国新闻条例制定的。在善耆任民政部尚书期间,未曾发生过当局和新闻之间的冲突,也没有引起社会问题。当然有时会因违反规则而受到了处罚,但没有新闻界愤慨而与当局对抗的事。
1910年,谋炸清摄政王载沣未遂事件轰动了全国,善耆采取了缓和、争取、利用的策略,希望以立宪改良缓和国内矛盾,维护清朝统治。另外也有其个人希望——赢得支持,立宪后出任总理的野心。善耆通过其内亲崇铠与革命党人保持着一种微妙的联系,对革命党人给予了不少方便。当时同盟会在上海办的《民立报》几经查封,而京师朝廷眼皮底下的《国风日报》却从未遭此境遇,正是因为没有得到民政部尚书善耆批准的缘故。
虽然善耆做了几件关系民生之事,对革命党人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也使当时的一些革命党人对他抱有一定的好感,但是清王朝已经为历史所唾弃,他的“努力”不足以改变人民向往共和的心愿,更不足以延长大清的寿命。正如他自己所言:“革命思想之兴起,是由于政治不良基因所致,此类事为远在法国、近在葡萄牙等国的革命经历所证实。如果一国的政治得到民众的信任,则欲革命也无人呼应。由此如欲根绝革命运动唯有实行良政,别无他法。然而我大清上自亲贵下至小吏,并不解政治为何物,只知肥私。如此失去天下之人心,其趋势已接近亡国。”
责任编辑贾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