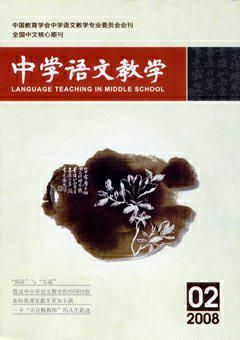一个“不合格教师”的人生轨迹
我是一名学历不合格的教师。1948年初中毕业,仅读了三个月的高中,就因故辍学;1949年参加教育工作后,也从未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学历培训,直至退休,我的“最后学历”仍是初中毕业。按如今教育人事部门的规定,“学历不合格教师”就是“不合格教师”,应在淘汰之列。但我居然不仅胜任了中学语文教学,还获得了好几个对我来说太过奢侈的称号和荣誉。我的人生之路究竟是怎样走过来的?不少关心我的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疑问。
我从小智力平平,加以顽皮贪玩,常常逃学, 在小学五年级之前累计创造了留级三次的“辉煌记录”。老师对我已丧失信心,我自己也以“差生”自居,不图上进,在自卑心理的支配下稀里糊涂地打发日子。要不是在小学五年级留级以后遇到了一位令我终身铭记的好老师,真不知道我现在会是一个怎样的人!
他姓武,在我小学五六年级时,教我班国语(语文)兼级任老师(班主任)。我现在虽然已经想不起他上课时许多生动的细节,但可以肯定地说,他绝对是一位优秀的语文老师。他之所以让我铭记终身,倒不完全因为他的课上得好,而是他教我做的一件事,整个儿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一天放晚学后,他把我留下,说是要教我“四角号码查字法”,看我能不能学会,来验证我是不是像人们所说的“聪明面孔笨肚肠”。经过他的指点,我居然很快就学会了这种查字法!他很高兴,于是交给了我一个任务:自备一本《四角号码小字典》,在教新课之前先把课文中生字新词的音义查出来,抄在黑板上供同学们学习。这件事对于我——一个长期被自卑感压得抬不起头的孩子来说,简直是一项无上光荣的神圣使命!一个学期下来,我不仅学会了熟练地使用工具书,而且养成了课前自学的兴趣和习惯,也不再逃学了,学习成绩有了明显的提高。到小学毕业的时候,武老师在我的成绩报告单上竟写下了“该生天资聪颖”这样的评语,他也许没有想到,这句评语对一个长期被自卑感困扰着的“差生”有多么重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逐渐萌发的求知欲的驱动下,我开始了读书自学的“兴趣之旅”。
确实,我读书全凭兴趣,既无计划,也谈不上下过什么苦功。进入初中以后,先是对古典诗词发生了兴趣,当时买到了一本《唐诗三百首》和《白香词谱》的合编本,于是先从读唐诗入手,凭着一本《诗韵合璧》,居然无师自通地弄懂了平仄,而且学会了按照平仄规律有板有眼地“吟哦”,一个学期下来,竟把三百多首唐诗全部背了出来,连《长恨歌》《琵琶行》这样的长诗,也能一背到底,不打“格楞”。接着又读《古文观止》,随后又扩展到读一些比较专门的集子,如仇兆鳌的《杜诗详注》,还做过一些札记。也爱读一些诗话词话,如《随园诗话》《白雨斋词话》等。傅庚生的《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俞陛云的《诗境浅说》是我接触最早的两本当代人写的文学启蒙读物。鲁迅的杂文和小说、林纾用“太史公笔法”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外国小说,都让我爱不释手。
读唐诗,读古文,遇到的生字、典故多了,小学时买的那本《四角号码小字典》已经被厚厚的《辞源》代替。这部《辞源》现在还在我的书架上,只是已经“老态龙钟”,原来的封面早就掉了,我为它用牛皮纸糊的第二个封面,也已经残破;书页全已发黄,书角书边由于手指常年的触摸、翻动,已呈灰黑色。它早就“退休”,但我在书架上仍给它留出一个应有的位置,像供奉一位长辈似的供奉着它。因为,它从我读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恪尽职守地为我服务,形影相随几十年,它给予我的知识和教益,超过了任何一位中学国文教师所能给予的;在我初中毕业后失学的日子里,又是它鼓励我选择了自学——在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里,它辅助我获得了一份不以文凭为标志的“学历”。它是我的老师,也是我读书自学的见证人,书边上那些灰黑色的指痕,就是它为我开具的“学历证明”。这些当然都是后话。
书读得多了,就不免“手痒”,便开始胡乱写些东西,尤其爱写旧体诗,在发表欲的驱使下,竟然还自作主张办了份名为《爝火》的壁报,至今我的“诗稿”中还保留着当年发表于《爝火》的好几首“少作”,虽然没有什么诗味,但多少可以看出我那时的精神状态。比如,初中二年级时学校组织学生到杭州旅游,我的诗稿里就留下了一首五律《登杭州南高峰北高峰》:“不见摩天岭,双峰自足奇。未穷最高处,已觉众山低。俗境随尘远,飞鸿与眼齐。还须凌绝顶,莫待夕阳西!”以登山为喻,表达了一个“少年读书郎”的志向,和小学读书时那个“差生钱梦龙”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除了课外读写,在课内国文学习上我也“发明”了一种独得之秘的学习策略,即在老师讲新课之前,先立足于自己消化课文,到听课时(当时的国文老师都是一讲到底的)就把自己的理解和老师的讲解比较、对照、印证;一般学生都忙于听和记,我则把听和记的过程变成了一个饶有兴趣的思考过程,既学活了知识,印入也特别深刻,到国文考试时,不必怎么复习,成绩也稳居第一。至于我的阅读和写作能力更远远高出于一般的初中学生,连不少高中生都是我的《爝火》的忠实读者。
综观我初中阶段的学习,尤其在国文学习上,呈现出一种明显的自学倾向。也许正因为有初中四年自学的“学历”垫底(我由于中途转学, 多读了一年初二,总共读了四年初中),毕业后我才能毫不沮丧地面对失学的现实,坦然选择了一条读书自学之路。
195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竟使我这个才初中毕业的20岁“大孩子”阴差阳错地成了一名中学美术教师,1952年以后又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成了专职语文教师。那时的我,对语文教学可谓一窍不通,语文知识的准备也远远不够。但我仗着自以为还有点国文“底子”,尽管身无“金钢钻”,却满怀信心地揽下了这桩“瓷器活”。我想,读书自学既然能使我学好国文,肯定也能帮助我的学生学好语文。于是,“怎样教会学生读书自学”成了我的语文教学的“主攻方向”。这实在是一次因为无知所以无畏的选择,绝不是因为有什么“超前意识”,只是凭我独特的“学历”,觉得语文只有这样教才不致误人子弟。
为了指导学生自己阅读课文,我备课首先考虑的不是怎样“讲”文章,而是自己怎样“读”文章。每教一篇课文之前,我总要反反复复地读,或朗诵,或默思,或圈点,或批注,直到确实“品”出了味儿,才决定教什么和怎样教。所谓“教”,也不是把自己已经认识了的东西全盘端给学生,而是着重介绍自己读文章的思路、方法和心得,然后鼓励学生自己到阅读中去理解、品味。我发现,任何一篇文章,只有自己读出了感觉,才能把学生读文章的热情也“鼓”起来。有时候自己在阅读中遇到了难点,估计学生也会在这些地方发生困难,就设计几个问题,让学生多想想;有时候讲一点自己阅读的“诀窍”,比如面对一篇文章从何入手、如何深入等等;自己爱朗读,有些文章读起来声情并茂,就指导学生在朗读中体会声情之美;自己读文章习惯于圈圈点点,读过的书页上朱墨纷呈,就要求学生凡读过的文章也必须留下阅读的痕迹;自己课外好舞文弄墨,还杂七杂八地看些书,学生在我的“言传身教”下,也喜欢写写东西,翻翻课外读物。总之,用传统的教学观念看,我的课上得有些随便,既没有环环相扣的严谨结构,也不追求“鸦雀无声”的课堂纪律。但学生学得倒也不觉得乏味,教学效果居然差强人意。1956年我被评为优秀教师,开始执教高中语文,并担任了学校语文教研组长,这更坚定了我“鼓励学生读书自学”的信念。那时自然不会想到,教学起步时认定的这个方向,会成为我语文教学上毕生的追求。
比较自觉地提炼自己的教学理念,则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
经过反思和总结,我开始明确:我的教学既然立足于学生自己的阅读实践,那么学生当然就是阅读的主体;但学生毕竟是不成熟的阅读者,因此在他们自主阅读的过程中离不开教师必要的指导。一方面是学生的阅读实践,一方面是教师的指导,师生之间自然形成一个教师“导”、学生“读”的互动过程,这一互动的过程就是阅读训练。于是,我把这种认识提炼为三句简明的话——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但“三主”作为语文教学的基本理念,其价值的体现,还有赖于在操作层面上得到落实和保证。于是我又提出了“三式”——自读式、教读式、复读式。“三主”与“三式”共同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语文教学体系,我把它命名为“语文导读法”。1989年出版的《心理学大词典》把“语文导读法”作为词条采录。著名心理学家朱智贤主编的这本《心理学大词典》,在第三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上被确定为国家级重点科研项目,被它收为词条,至少说明了学术界对“语文导读法”的认可。可以这样说:“语文导读法”的提出,是我读书自学历程的一个自然的归宿。
回视自己历时半个多世纪的人生轨迹,充满了戏剧性:少年时代是“差生”,从教后是“不合格教师”,中间又几经政治风雨,坎坷颠踬,但我竟然没有虚度此生,老来回忆,尚能差堪自慰。这靠的是什么?我的回答是:
认定了目标以后,就要以恋人般的痴情,宗教信徒般的虔诚,革命志士般百折不挠的意志,不离不弃、无怨无悔地紧追不舍。
是答案,也是我的人生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