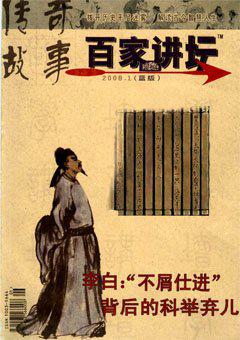解析的真实历史
芦 笛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上海,在黄浦江滚滚不息的浪涛及飘逝的流光碎影中,摇曳着的是上海滩那泛黄的记忆和虚幻的浪漫,是当年那个从十六铺的卑微和嘈杂中跌跌撞撞走出来的“水果月生”。
当他走进真实的历史篇章中时,他叫作杜月笙,那个曾经呼风唤雨叱咤风云于整个旧上海黑社会的黑帮老大杜月笙;而当他步入我们现实的假想中时,他叫宋子豪、小马哥或杀手小庄,当然。他还叫作冯敬尧、丁力以及许文强。
刀枪的血腥和世事的残酷构筑而成的是另一个畅快淋漓的江湖,只是,英雄所负载的所有侠义及传奇都被蒙上了一层黑色的面纱。于是,因这隔世的朦胧和沉醉的迷离,英雄的背影以及所有关于英雄的话题便多了一分神秘和探究中的遐想。
其实,所有的影子都只折射在了“海上闻人”杜月笙身上。从十六铺的铺子中间窜来窜去吆喝卖梨的小赤佬摇身一变,成为无限风光招摇过市的流氓老大,使得我们更愿意在一部部的黑帮电影中去重温那想像中的传奇与神话。
神话永远罩离在一圈模糊的光晕中,而传奇也永远只存在于渐行渐远的记忆中,无论你怎样努力去接近那个繁华飘摇的帮派江湖,你看得清英雄礼帽下遮盖着的潇洒俊朗的面孔,却读不懂他眼神中的迷离与忧郁,以及他转身时甩给你的无限的寂寥和伤痛。因此,从来就没有人可以复制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当年在上海滩那翻云覆雨一手遮天的豪气与精彩,即便他叫作宋子豪、小马哥,或是冯敬尧、丁力、许文强。
我们能借以满足好奇心和探究欲望的,也只是尽可能地去接近真实,接近这个亦真亦幻爱恨交织的上海滩,这个精致优雅甚至带着几分艳俗的上海滩;我们能做的也只是透过这些闻人枭雄脸上蒙着的那层面纱,去努力窥探他们的一个眼神、一个琢磨不透的表情以及一个寂寥伤痛的背影。
那些关于杜月笙的传奇
穷苦出身、前呼后拥的气派和玩弄于股掌之间的魄力,“义”字当先的豪爽,黑帮老人怒不形于色的意味深长,帮派争斗时的狠毒和老辣,黑道白道之间周旋的游刃有余,与法租界探长的权钱交易,和日本人利欲熏心祸国殃民的烟土生意,房地产公司背后不可告人的罪恶勾当,军阀、帮会、租界三位一体的鸦片走私联盟,法租界公董局华董的最高职位对其黑帮身份的洗白,渗透于政治、经济、金融,工商、新闻等全方位的势力范围——这是电视剧《上海滩》中冯敬尧的画像,也是杜月笙最真实的写照。
黑帮电影数十载,几度鼎盛,几度式微,江湖英雄代出,而最像当年那个驰骋于旧中国上海滩的闻人杜月笙的,不是宋子豪、小马哥,也不是许文强,而恰恰就是这个冯敬尧。
杜月笙是胜者,他胜在他始终是处在这个黑吃黑游戏的最高端,别人永远足他手中渺小的棋子,让他拿捏着摩挲着把玩着。黑帮分子跳梁小丑般的表演只有更加拙劣和蹩脚,方显出胜者如此大度与忍让的美德;倭寇异族的侵略与贪婪只有更加肆无忌惮和不知廉耻,才能彰显胜者不动声色的稳健,以及掩饰得更为深厚和隐秘的阴暗与老辣。
杜月笙原本只不过是旧上海浦东高桥臭河沟中苟活着的一只泥鳅,不甘于人下的他反而比那些遗老阔少们更为懂得用穷苦与艰辛作为修行的全部资本。于是,一干年之后,他化身为鲤;再一千年后,他终于可以跳龙门了。那一刻,在高桥杜氏祠堂盛大的宴会场所和权贵军阀的阿谀奉承中,他显得如此风光和招摇,然而他的心里却清楚地描画着另一种战战兢兢与虔诚执著的表情。躺在上海华格臬路216号杜公馆的这家主人意味深长地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杜月笙的成功是黑社会游戏规则的成功,是杜氏规则的成功。在那个秩序混乱是非颠倒的年代,杜月笙制定的规则就是上海滩的最高法令,租界的洋人就是他最亲密的帮凶,而警界和巡捕房也不过是一群披着执法外衣的帮会啰嗦而已。在这个规则体系之中,权力可以战胜正义,金钱可以打点良知,骁勇可以摔破辈分,赌博可以赢得前程。当规则制订的最高权力最终旁落到这个当年毕恭毕敬地给自己拎包的小赤佬手中时,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法租界华探督察长黄金荣或许永远都不明白,为什么被众人千叩万拜的这个“老头子”的座位,有一天会改姓杜?从高桥镇到十六铺,从十六铺到黄公馆,又从黄公馆到杜公馆,杜月笙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从一个水果小贩到一代闻人大亨的蜕变。
杜月笙能笑到最后,那是因为他比黄金荣更深刻地参透到了规则的最深要义,所以,他知道用豪爽和义气去笼络兄弟,用散金碎银来收买人心,以忍辱负重来铺通攀爬之路,以烟馆鸦片来独食经济暴利,靠官商勾结来巩固权钱地基,与异邦勾结来牵制帮会纷争。甚至在革命的风雷之声霹雳四起时,当已近80高龄的黄金荣仍抱着年迈之躯抖抖缩缩地居于上海滩时,杜月笙却能审时度势并义无反顾地跳出规则的诱惑之外,倾其财力改头换面成为一个抗日爱国的正义形象,以寻求新的规则及新的意识形态下的庇护。
所以,冯敬尧永远也活不出杜月笙的精彩,他只活到了杜老头子前半生的皮毛——那些在人们的遐想中永远前呼后拥一手遮天的皮毛。当许文强的枪指着他脑袋的时候,不管胸怀家仇国恨的许最终是否扣动扳机,冯敬尧的时代都已经结束了,或者留给他的后任丁力去收拾残局,或者从此宣告上海滩黑社会及帮会势力的全部终结。冯敬尧仅仅复原了杜月笙一生中“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尺五乏”的辉煌片段,而那些关于杜月笙充当“蒋介石的夜壶”的笑谈,充当国民党政府的打手疯狂镇压工人运动的残暴故事,还有关于他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用人力物力财力全面支持淞沪战场上的十九路军的爱国传奇,以及他振臂呐喊征募救国捐助的爱国壮举,终将隐身于一袭长袍里的黑社会老大的威严与流氓形象变成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而任由后人评说。
杜月笙,用自己的传奇与神话编织着上海滩的迷幻与奢靡。他是旧上海滩势力最大的黑帮头子,也是上海市各界抗敌委员会的负责人、上海党政统一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他是蒋介石北伐政府残酷镇压工人革命运动的最大帮凶,也是对蒋介石抗战政策最坚决的支持者,他是帮助日本人用鸦片政策打造中国东亚病夫屈辱形象的可耻卖国贼,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在上海和香港支援抗战的最重要的一个民间代表;他是蒋介石国民政府豢养的一只鹰犬,也是蒋介石用完了又嫌臭而被扔到床底下的“夜壶”;他是阴谋暗杀共产党工人领袖的流氓刽子手,也是保护潘汉年等中共地下党员的爱国志士……
杜月笙无疑是旧中国上海滩一个最富有争议的传奇人物,大半个世纪以来,历史给予他的评价和定论,总是因着种种价值评判体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以及他自身含混芜杂纷繁多变的行为性格所造成的解读隔阂,而将历史最真实的一面永远地阻隔在了我们的视野之外。他给后人留下了更多的悬疑和思考,让那些后来者在对历史情境一次次的蓄意模仿和天马行空的想像
中,试图引领我们走向那条漫漫的历史追溯之路,重温那个时代的梦想与传奇。
传奇的另一种写法
被严谨的制度和井然的秩序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我们,总是会以一种艳羡的同光去打量那些发生存我们生存规则以外的事物,而再也没有一样东西能像黑社会这样更能激起我们对历史的自由想像和对另类生存模式的向往。于是,我们便寄希望于在小说和影视作品以及其他所有可能的途径中去寻找那个另类江湖的踪迹,哪怕枭雄的传奇在不同的叙事模式中变幻着不同的色彩,哪怕英雄的影像早已被越来越晦涩的艺术想像肢解得体无完肤。
1972年,好莱坞导演弗朗西斯·科波拉执导的影片《教父》(The Godfather),标志着黑帮类型电影的诞生。从此,这种围绕着邪恶与正义争斗,罪恶与良知对抗的主题,包含着杀人、抢劫、偷盗、贩毒等犯罪内容的剧情片,便以其耳目一新的内容和怪异奇特的表现于法,将人们的视线从不痛不痒的平淡现实中抽离H来,成为人们在街头巷尾和茶余饭后最愿意去评说和谈论的影片类型。
《上海滩》,无疑是这种黑帮类型电视剧的一座高峰,冯敬尧、丁力、许文强的名字,在电视这种特殊传媒形式的传播下,经过冗长的剧集对爱恨情仇的充分演绎和对世态人性的细腻刻画,被赋予了更为鲜明的件格特征和更神秘更生动的传奇经历,让旧时代黑社会的另类江湖形态以及黑帮人物那富有传奇色彩的形象和经历,从此得以家喻户晓万人传唱。
在港版提供的故事框架基础上,著名导演高希希对大陆版本进行了全新的打造,还叫它“上海滩”,是因为故事还是那个故事,人物还是那些人物。但很显然,由于地域的差别、文化的差异以及在不同意识形态下主流话语权力的审视角度和人们的观影需求的不同,此《上海滩》已非彼《上海滩》。礼帽文明杖、帮会打斗、贩卖军火走私鸦片、内外勾结祸国殃民……高希希还原了旧版上海滩黑社会局部的场景风貌以及杜月笙发家奋斗史的某个章节,但他所编纂的江湖传奇,却已然是另一种写法,另一番风韵。
在《新上海滩》中,同那个杜姓祖师爷一样,冯敬尧是上海滩的一尊神,是人人敬仰着的上帝。以父辈名义投向后辈的永远是充满慈爱的目光,但也许只有他那个天真烂漫不谙世事的宝贝女儿,才可以过滤掉一切复杂深邃的杂质,看到他那温暖的疼爱与包容。丁力,这个再现了“水果月生”当年饱受饥饿与凌辱的不堪回首之流浪岁月的“水果阿力”,尊其为神,视其为父。当丁力欣喜地从冯敬尧的身上看到了他光明的末来,以及在想像中有可能会达到的那个权力与金钱的极限时,他便以一种自豪与崇拜的激动之情,让自己那过于简单的大脑接受了神与父的全部慈爱,以及慈爱中言说着的他看小清或虽然看清却执意要熟视无睹的所有美丽梦想与残酷现实。只是,当“水果阿力”终于有一天梦想成真变成了像冯先生那样的人之后,那个上海滩的游戏规则是否仍然坚不可摧?他是否还能安然地端坐于龙头人椅之上,以一个全新的黑帮老头子的身份来接受脚底下又一轮的跪拜?
历史永远站在了美好想像的对面,1951年,当逃往香港的杜月笙在某个清晨看到香港《大公报》转载的“黄金荣自白书”时,新中国水深火热的革命浪潮和解放运动已经将旧中国上海黑社会称霸一世的杜氏规则粉碎殆尽。所以,如果将荧屏中的这个江湖传奇继续演绎上去,丁力的权贵梦金钱梦,终将只是个虚无飘渺的梦想而已。当在剧情末尾他射杀了许文强之后,他就注定要在无尽的悔恨与自责中生不如死地聊度残生,连同那注定将要飘逝而去的婚姻与爱情之道,迷惘地面对着自己看似光鲜却又空空如也的未来。
所以,无论我们如何穷尽思考,无论我们如何在想像中尽情地演绎,杜月笙的精彩都只属于他自己,我们只能从街头巷尾流传着的关于他的众多神话与传奇中采撷一隅,以现代人的思维重构和影视艺术的夸张描摹来满足我们飨食的欲望;而杜月笙的失败,则更像是历史篇章中最普通最不起眼的那一页,他没有败在你死我活的黑帮争斗中,却败给了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败给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败给了中国历史新的时代及其新的运行规则。
于是,关于上海滩流氓大亨退隐前的那一笔尴尬,便根据人们的想像与期待,按照电影的叙事规律而改换成了另一种更具有传奇色彩的写法。冯敬尧在上海滩辉煌显赫‘世,最终却败在了这个叫作许文强的年轻后生手上。《新上海滩》中许文强并没有扣动指向冯敬尧的扳机,但在高希希所阐述的更深的意义层面上,冯敬尧即便活着,他的灵魂却早已经死了。
冯敬尧之于许文强的失败,并不同于黄金荣之于杜月笙的失败,也不同于杜月笙之于时代的失败。黄金荣的失败是黑帮规则中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之规律的最典型的注解,杜月笙的行事体系与江湖规则最终也是无奈地退让给了历史发展洪流中不可更改的必经阶段,而冯敬尧则是败在了“邪小压正”以及“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等这些中国最古老的道德定式对黑帮集团所有的强势因子的消解。冯敬尧其实是败给了许文强的坚持,那些被许文强内心涌动着的正义和良知的强大信念支撑着的坚持,那种即使是面对兄弟的背叛、爱人的分离和亲人的鲜血仍然义无反顺的坚持。
你死我活的黑帮争斗中从来都离不开利欲熏心的煽风点火,只是这一次,冯敬尧面对的却是视金钱为粪土、视权力如草芥的许文强,一个始终游离于黑社会游戏规则边缘的类黑帮分子。如果说许文强心中还存有一丝欲念的话,那么这个欲念就是“正义”,这个从黑社会的词典中根本就查不到的概念。位高权重的冯敬尧似乎是掌控了所有人的命运,但唯独裁在了许文强的信念之上,那些关于善良、正义、法律、有序以及爱国爱民的中国人最基本的信念之上。
正如杜月笙在国共两党之间左右逢源、并在时代更迭面前见风使舵的自保之举一样,冯敬尧到后来所追求的最高权力目标,也不过是为了还自己一个清白的名声而已。只是,当寻求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暴力行为与权钱交易越来越偏离自己身份和洗白的初衷时,永远都会有像许文强这样不被收买的良知和正义横亘在他的欲望面前,让他穷尽毕生精力也终究无法退去黑社会罪恶的外衣和虚假的灵魂。
这样一种出污泥而不染的坚毅性格,实际上离黑社会的行为规则及行事体系已相距很远很远。许文强总是从简单中解读出复杂保守的处事风格,以及他优柔寡断踯躅徘徊的性格及行为方式,显然还远不及丁力的鲁莽耿直及草莽气息更能融入黑社会的游戏规则。因此,与其说《新上海滩》描摹的是“海上闻人”杜月笙的蓝本,是一部关于穷苦小子混迹、发迹并最终叱咤风云一呼百应于黑社会江湖的黑帮片,倒不如说它是一个爱国青年与强大的黑势力进行坚持不懈的抗争并不惜流血牺牲的可歌可泣的年代剧。
在特定的意识形态的规制下,中国大陆不可能像美国、日本以及港台地区那样,将旧中国上海滩的黑色传奇大张旗鼓地搬入文化消费领
域,所以,中国大陆从来就不可能出现严格意义上的黑帮片、枭雄片。故而对于港版《上海滩》的翻拍,人们关于对“黑色戏谑正义”、“凶残战胜善良”的黑社会真实场景进行完全复制的任何新鲜的好奇与自由的想像,最终都将止步于主流的艺术道德规范和影视艺术本身所承载的教化意义之前。
这是一个妥协了之后的《上海滩》,对于熟请历史剧、年代剧叙事模式的高希希而言,他显然并不希望像众多的港式黑帮片那样,将《新上海滩》的着力点放置于黑社会的游戏规则之上,而是渴望通过跳出规则之外的视角,来讲述规则之内的无情与暴戾。于是,在许文强和冯敬尧这一正一邪的二元冲突中,我们便感受到了人性在两种截然相反的信念体系之间来回锯战时所形成的张力与残酷,感受到了许文强对黑帮游戏规则最深刻的质疑与思考,以及他在选择逃离还是归附这个规则体系时内心所承受的痛苦与煎熬。
高希希所营造的黑社会江湖,其实是一种被诗意化了的另类江湖传奇,许文强始终在黑与白之间徘徊,在民族大义和儿女情长之间伤感,在美好的想像与残酷的现实之间挣扎,直到最终他被兄弟的枪击中的那一刻,他的内心仍然在做着痛苦的斗争。这样一个悲剧性人物,实在算不上是一个黑帮人物,如果说丁力还算是一个枭雄,从他的身上还能觅得杜月笙当年黑帮老人的影子的话,那么悲剧的许文强甚至连英雄都做不了。
英雄需要果敢的行事手段,需要坚毅沉稳的性格,需要对社会和人生具有大足大非的清醒认识、坚定不移的信念以及积极向上的价值观,而许文强在思想感情上却存在着太多的羁绊,以至于他的优柔寡断最终葬送了他自己。第一次的火车站告别,本来是他逃离黑社会游戏规则的最好时机,而他却在兄弟的危机和爱人的眼泪中明知虎穴偏又行;尽管许文强在自己追求正义和爱国爱民的英雄壮举中付出了丧失兄弟、爱人以及亲人的惨痛代价,但在他举起手枪面对冯敬尧的那一刻,他却再一次因致命的善良和忧郁的情怀而背叛了自己的信念,背叛了正义对他作出的指示,背叛了亲人为他作出的牺牲。所以,如果非要将许文强看成是一个英雄人物的话,那么他也仅仅是个令人揪心垂泪扼腕叹息的悲剧英雄。
《新上海滩》看似是黑帮类型的电视剧,实则却更像是一部年代剧,它身上所流淌着的那种浓郁的伤感和淡淡的哀愁,依然是《历史的天空》或《真情年代》里属于高希希个人风格的一贯延续。至于片中的黑社会背景及人物事件,不过是高希希用来包装其叙事情境和结构背景,从而让其看上去更像是一部黑帮片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手段。
《新上海滩》由于对剧情氛围过度诗意的营造,对黑帮江杀的血雨腥风刻意的弱化,对人物性格定位的过度复杂和犹疑不定,以及对主人公身上所承载的历史使命的过度负荷,我们已看不到黑帮类型电影中所惯常使用的那种大胆跳转的叙事手法、变幻多端的镜头运用、精彩纷呈的画面构图、恣意爽快的制作剪辑以及行云流水的音画对接。
我们感受不到黑帮电影文本叙事本质上的那种虚无的游戏姿态,看到的却是略感沉重的历史文化和完美得近于失真的人格升华;我们甚至看不到其实最想享受的难得的黑帮暴力的刺激铺陈,感受不到快疾的叙事节奏中与枪战恶斗相辅相成的让人喘不过气米的紧凑与张力,而只能在苍白贫乏的剧情想像以及近乎历史陈述式的不慌不忙中再一次领略国内电视剧慢性子的固疾。当我们看到许文强存冯敬尧带着几分嘲弄的笑意中倒在兄弟枪口之下的时候,那些因他潇洒的扮相和帅气的身影所投射给我们的全部愉悦,都被驱逐于最深刻的记忆之外,而唯留下一腔的愤懑与不甘,让我们无处宣泄。这实在不是一个黑帮类型的电视剧应该带给我们的最后的感受与回味。
上海滩,为中国历史舞台上演绎着的众多的江湖传奇提供了最丰富的土壤,而在将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站在黄浦江边面对这浪奔浪流时,我们却只能无奈地欣赏从遥远的东海之外所传来的对于那段传奇的历史场景或真实或虚幻的重演。
以流氓大亨杜月笙那段独特的历史传奇的视角来看待《新上海滩》,这显然是一个善意的苛求。不过,如果它在无意中竟然帮助我们重新打开了思绪里对于旧中国上海滩那尘封已久的记忆,激起了我们对那段历史往事进行了解和探究的欲望,那么在观影过程中,我们就会多了一分对历史与现实进行相互对照和比较演绎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