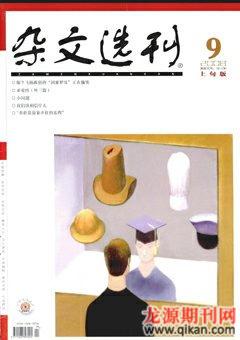狄马的发现
摩 罗
最近较为全面地拜读狄马的随笔集《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其中不少文章反反复复地读。狄马是一个有所发现的思想者。他的两个发现和三个关键词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第一个发现:我们是人盲。
一个农民深夜路过一个村庄,被村民当作小偷抓住并活活打死。这样草菅人命的事,我们的习惯是感叹生民不懂法,送一顶“法盲”的帽子了事。就是在这个地方,狄马发现,一些人之所以操刀舞剑、草菅人命,原因并不在于他们是法盲,而在于他们实际上是人盲。“他们的脑子中根本没有人的概念,他们不懂得只要是人,就是一具活脱脱的、有生命的独立实体,需要每一个别的人都善待和尊重。”
“我們对于权力、利益、观念、礼数、身份、功名等等都看得很重,惟独对人却视而不见。”人是一种很容易忘乎所以的动物,一不小心就忘记了自己是谁,这时不妨默诵一下狄马的发现。
第二个发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真正难度在于,对手也必须是一个讲究基本游戏规则的人。
狄马对非暴力的实质具有深刻的理解。他说:“说到底,‘非暴力是什么?它是一种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宗教运动,实质是以吃苦隐忍的精神、以道义的力量邀请对方共同遵守人类的文明准则。它的真正难度在于对手也必须是一个讲究基本游戏规则的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实际上是一场“非暴力合作运动”。在介绍甘地发起的反对当局食盐法运动及其胜利时,作者写道:“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典型的以灵魂的力量抵御暴力的感人尝试,它的意义在于施暴的一方由此认识到了弱者心灵的伟大,不仅放弃了食盐法,而且沮丧地认为,他们在这次事件中丢尽了英国人的脸。可对我来说,真正严重的问题是,假如他们压根儿就不要脸呢?”
狄马的提问充满了思想的力量和良知的痛苦。我沉重地认同和称赞他的这一发现,同时我绝望地抗议他启示我们怀疑这一伟大思想资源的险恶用心——尽管他在险恶的同时是如此痛苦。
狄马对他的时代提出的一些要求,对我们如何摆脱人盲状态,早日认识“人”,努力成为“人”的进一步的思考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关键词中。
一:怜悯。他反复强调做人就应该“懂得爱,懂得怜悯,懂得美和善良。”在谈论博物馆功能时,他批评那种通过展览突出英雄的功绩而漠视生民的生命的理念。“每一个人,一走进博物馆都不约而同地抚今伤昔、缅怀逝去的生命,不管他曾经是敌人还是朋友。”这才是具有人文价值的博物馆和纪念馆。如果我们“懂得爱和怜悯,敬畏和悲叹每一个短促而劳碌的生命,那么,寡廉鲜耻、丧尽天良的事一定会少得多。”
怜悯是人作为一种生命对待生命世界所应该具有的基本态度,是人之为人的情感底线。没有这种起码的情感本能,这种两脚动物就不是人而只能是人盲。
二:文明。和平、友爱、宽恕、协作的伦理思想和价值理想就是由人类世世代代建构起来的。这一理想就是所谓文明的核心,它已经不同程度地内化为人的基本素质。一个人无论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什么阶层,在利益纷争中处于什么位置,在政治冲突或者情感冲突中处于什么境地,只要他具备基本的人文素质,尊重基本的文明准则,他就必定会尊重他者的生命和权利。
狄马引述了一个材料,有人问那个制造假药的老妇人,你知道别人吃了这些假药会死掉,怎么还制造假药?老女人淡然地回答说:“他们又不是我的孩子。”这位老妇人只懂得珍爱自己的孩子的生命,而不懂得珍爱他者的生命,说明那些基本的文明准则还没有内化为她的素质,她像鳄鱼一样捕杀同伴的孩子来解决饥饿问题。狄马没有将这位老妇人看作个别现象,他所看到的是文明准则离我们还有若干距离。
三:信仰。有一个词语狄马没有动用,但是常常在他笔下呼之欲出。我指的是与人盲对应的“神盲”一词(他用的是另一个比较庄重的词:信仰)。人在精神上最终的归宿,不是泥土不是功勋不是后代,而是通过与最高存在的沟通而达成的生命意义。没有这种意义的建构和认定,我们就只是神盲。我们作为人盲的许多罪过,可能跟我们的神盲状态息息相关。
一个人要拥有狄马所说的那种大光明,才能让自己的生命跟宇宙存在建立最广泛最深刻的精神联系,这种联系可以命名为爱,也可以命名为神。上文所提到的那位老妇,那么勇敢地用假药伤害他人生命,竟然没有一点愧疚和忏悔。一个人没有神性的照耀,就很难有真正的人性觉醒。把动物本能当作人性,这是我们这些人盲最常犯的错误之一。
从怜悯到文明再到信仰,是我们解除人盲状态所需要遵循的内外兼具的途径。
【选自狄马著《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花城出
版社版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