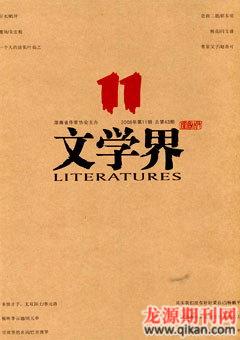桃花
闫文盛
一
来生叔去世的消息是母亲不久前告诉晓晨的,母亲的话语中带着怅然:“走的时候身边连个人都没有。屎尿糊了一裤子。”当时晓晨刚刚提拔,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代理主任,可大小有了点权,人也就变得牛逼起来,任何事情都不放在心上,所以,母亲的话从他的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可过不了几分钟,他却又想起这个话茬,就走到院子里追问了一句:“妈你刚才说什么?来生叔走了?”他的反应自然让母亲觉得很受伤,她高声大气地说:“你就日能吧你。”这句话让晓晨听了很不舒服。他有些悲哀地看了母亲一眼,这一眼很重,母亲似乎不堪承受。她又嘟囔了一句:“你就日能吧你。”但神情已经委顿了下来。
晓晨注意到母亲的脸色变得黯淡无光,像烧成灰烬的煤屑。
晓晨怎么也想不到母亲现在会那么在意他的目光。怎么会呢?他记得母亲并不是一个脸皮薄的人,以前自己多少次当着妻子方颖的面冲母亲发火,都没有见她有过一丁点儿不快。该说说,该笑笑,她甚至还冲着儿媳妇解释:“你瞧这孩子,硬是让我给惯坏了,以前他爸那死老鬼在的时候……”一听她提到父亲,晓晨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妈你还有脸提我爸!”母亲讪讪地笑着:“这孩子,这孩子……”
事后方颖总是说他过分了,他过分了吗?
这一天,妻子因为一件什么事情生气了,就在电话里骂他:“晓晨你不是东西,我早都应该瞧出来了。想想你怎么对待你娘的?”
晓晨当时没有反应过来,事后却一直在咀嚼妻子的话。他越想越气,当天晚上回家后就冲妻子发了一通无名火。这是破天荒的一次,妻子觉得他穷凶极恶的样子“有些恐怖”,她骂了他一句“神经病”,就径自离开了。
家里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
晓晨坐在阳台上,看着母亲的照片发呆。
年轻时候的母亲显然是一个美人,这张照片更加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不知道什么缘故,晓晨总是觉得方颖不知什么地方长得像自己的母亲,婚前婚后,他经常长时间地盯着她看,并且暗地里同自己记忆中的母亲做着对比。方颖发现了他的秘密,追问了他几次,他嬉笑着说:“我老婆长得好看呗。”她拿刚刚切过葱的手朝他脸上一抹,他顿时辣得睁不开眼。
照片上的母亲最突出的是眼睛,晓晨不知道怎么形容母亲的眼睛,作为儿子,他有些惧怕长着这样一双眼睛的母亲。有一次他半夜梦醒,突然看见方颖正含情脉脉地看着她。她的目光勾魂摄魄。晓晨惊奇得坐起来喊了声“妈”,他说:“我刚才怎么看见了我妈?”
方颖摸了摸他的额头说:“你是不是做梦了?”
晓晨摇了摇头。
他终于知道他们婆媳俩到底哪里长得像了。他憋了许多天,才把母亲年轻时的照片拿给方颖看。方颖不相信地盯着照片上的女人:“这个长着一双桃花眼的女人,难道,难道就是你妈?这个人,真是我的婆婆吗?”她边说着话,边在床上笑得打跌。晓晨有些失望地叹了口气:“你没有感觉到你们俩的眼睛长得很像吗?真像,简直像一只模子刻出来的。”
妻子从床上坐起来,夸张地摇头:“不,这不可能,你再让我看看。”她一下子把照片夺了过去,最后下结论说:“你的感觉太荒唐了,晓晨,我没想到你会有这么奇怪的想法。”
荒唐吗?他在心里说。其实一点儿都不荒唐,他私下琢磨着。
不过他记住了妻子的说法:桃花眼。他有些痛恨这个词。
妻子说:“这是你妈给你的?”
晓晨说:“不是。”
他没有对妻子明言,照片其实是他无意中在母亲的枕头底下发现的。那一年,他满了十八岁,给父亲做过了三周年祭日后,他郑重地询问母亲父亲是怎么死的。母亲擦着眼泪说是死于心脏病突发,他却隐隐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父亲的死或许同母亲有着很深的牵连,他甚至不止一次的猜想,母亲就是害死父亲的罪魁祸首。尽管没有质问同样处在悲伤中的母亲,但他的心里却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他把照片偷偷地收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母亲并没有向他询问这件事。有一个夜晚,他听到母亲在屋子里翻箱倒柜。昏暗的灯光下,母亲的身影像一个幽灵。
他忍了好久,终于还是没有张口叫住正在忙碌中的母亲。
后半夜,他听到母亲走到隔壁的屋子里去。母亲在他注视不到的地方嘤嘤哭泣。
晓晨冷静下来一想,自己确实挺对不起妻子的,可一时之下,又抹不开脸面。这样坚持了两天。这两天里他一直在回忆着妻子离去时的场景,可怎么也想不起来。因为心中有事,到了单位时情绪也都堆积在脸上,费了好大劲也没有变过来。这一天午间休息的时候在楼梯口碰到了总经理,这个发福的中年人关切地说:“晓晨啊,跟爱人吵架了吧?”他冲总经理尴尬地笑笑,然后就不打自招了:“我会处理好的。”总经理的手机恰在这时响起来了,他接起来说了一句话,就冲晓晨摆手,示意他离开。
第三天天刚麻麻亮,晓晨就起床了。他拿起手机给方颖发了条短信:老婆,我是混蛋,做了错事、蠢事,你能原谅我吗?
发完短信他就下楼到车库里取车,然后一溜烟地向丈母娘家驶去。晓晨根据经验判断,妻子这会儿肯定还在被窝里呼呼大睡呢。她向来比他起得晚。但是这一次,他想错了。
到丈母娘家楼下,晓晨拨了妻子的手机,手机开着,但没有人接。他觉得烦躁起来。他掏出烟盒,点燃了一枝烟。他强迫自己忍住这突如其来的怒火。在点烟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手有些抖。他暗暗骂了一声“臭婊子”,声音恶毒得像对待一个仇人。骂完后他发现了自己的病态和脆弱,他突然想哭。妻子却在这时出现了。她早已收拾妥当,连包都拿下来了。
晓晨的眼眶不由自主地红了。
妻子见他的神色古里古怪,拿手在他的眼前晃了晃:“臭小子,真有种,竟然整整两天连短信都不发!”
晓晨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地夺眶而出。
他猛地上前把她抱紧了。
妻子觉得他的力量好大,她使劲挣扎着抽出一只拳头砸他:“臭小子,你真是头倔驴。倔驴。”
他们默默地进了家门。他盯着她看了半晌,她被他盯得心里发毛。
她下意识地说:“你想做什么?”
晓晨嘿嘿地笑了笑:“你说我想做什么?”
他拦腰把她抱起来,从客厅里抱到卧室里去。他三下五除二,把她的衣服脱光了,她大声嘱咐他:“晓晨,你别急,先去洗洗。”他还是嘿嘿笑着,三下五除二地,早把该办的事情办完了,然后他就爬到床头,呼呼地喘气。妻子愤慨地冲他喊:“李晓晨,你是头猪吗?没想到你竟然是头猪。”
她骂他:“你简直禽兽不如。”
她指责他:“你这是在强奸我,李晓晨,你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晓晨看着她的嘴巴一张一合的,突然觉得滑稽。
他又点燃了一枝烟。他发现自己真的疯了。刚才和妻子做爱的时候,他突然感觉这个女人不是自己的妻子。他竟然觉得她那么像自己的母亲。竟然。
他扔掉了手中的烟。烟头的火星在地毯上发出了“哧”的一声,妻子俯近一看,已经烧出了一个小洞。他就在她的叫喊声中,跑到了卫生间,将水龙头开到最大,他用冷水哗啦哗啦地冲洗着自己的头。
妻子站在卫生间的门口,冷冷地看着他。
他知道她站在自己的身后,但他不想做出任何解释。他感到自己的内脏像被淘空了似的,胸口处一阵一阵地发慌。他知道那种可怕的感觉又来了。
还是在他六岁那年,父亲外出打工,撇下了他们母子俩。他记得那时候母亲很年轻,跟照片上的样子差不多,只是没有照片上那么鲜亮罢了。因为父亲长期不着家,母亲经常怨气冲冲的:“早知道你老子这么不负责任,我何苦生下你给自己找罪受。”
许多时候她也会怜爱地看着他,把他紧紧地抱在怀里。
晓晨童年最大的记忆就是母亲暖暖的怀抱。他甚至在母亲的被窝里一直睡到了七岁半,直到有一天一件奇怪的事情把这种温暖的感觉彻底击溃。
那天,他半夜里被尿憋醒,像往常一样。他喊了一声:“妈,我要尿尿。”但他的喊声没有立刻得到回应。然后,他就察觉到不对头。他发现自己单独睡到了一个被窝里。在母亲迟到的动作里,他还听到了一阵“呼哧呼哧”的喘气声。这声音让他害怕,他又喊了一声“妈”。
母亲催他:“尿完了赶紧睡吧。”
他迟疑地说:“我想跟妈睡。”
母亲不耐烦地吼:“都多大的人了还跟妈睡,说出去不怕人笑话。”
他不甘心地朝母亲的被窝里摸索,先是摸到了一条光光的腿,他以为是母亲的,但好像又不是。母亲察觉到他在犯傻,就伸出手来狠狠地揪了他一下。
他被弄疼了,“汪汪”地大哭起来。母亲说了句“你这个小冤家”,就钻到他的被窝里来了。
这一夜,他睡得很不踏实。屋子里总有一种奇怪的声音。天亮以后,这声音就消失了。他看到母亲的脸色泛红。母亲的眼睛也是红的。许多年以后,他才想到了一个词:桃花红。
晓晨觉得这个词里充满了让他恐惧的成分。尽管母亲一再地解释,那天晚上是父亲回来过了,但他凭着本能判断,那个人根本不是父亲。他冲母亲使白眼,不吃她做的饭,最后母亲生气了,拿笤帚把使劲地打他的屁股。他的屁股肿起来后,母亲又心疼地给他煮鸡蛋吃,甚至杀了惟一的一只公鸡,给他煨了鸡汤喝。
但他在鸡汤里喝出了一种奇怪的味道。他对母亲说:“我不喝你的汤。这汤是臭的。”
母亲气疯了。她坐在院子里号啕大哭了整整一个下午。整个人披头散发,像个魔鬼似的。
那一个下午,晓晨缩在屋子里看着母亲哭,他的身体里一阵阵地往外冒着冷汗。他甚至冲母亲喊了声:“妈,我冷。”但母亲显然没有听到。等到她的悲伤丧尽回屋的时候,她才看到了躺在炕上已经人事不省的孩子。
二
有不少人上了岁数以后,身体变坏了,失眠、多病,但脾气却变好了。晓晨娘就是这样。
最近一段时间,她暗暗注意到儿子儿媳的关系变得很微妙,有自己的前车之鉴,她觉得有必要提醒儿子要注意儿媳的新动向。可话还没有说出口,儿子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数落了她一顿。在儿子面前逆来顺受,她已经习惯了。不习惯的是儿媳妇。她当着婆婆的面就让晓晨下不来台。她说的话文绉绉的,但大意就是:你这样不孝,连我都看不下去了。你娘真是白养了你。
这话晓晨娘可是不爱听。
她觉得儿子应该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媳妇。即使儿子不愿意做,当娘的也有这样的责任。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婆婆毕竟不是从前的婆婆了,儿媳也不是从前的儿媳。晓晨娘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倒吸了一口凉气,她想起儿媳妇那得理不饶人的阵势,估计说了也是白说,弄不好,她会老大不客气地顶撞回来。儿媳不是亲养的,说到底还是个外人。
她急中生智,立马给儿子打电话说自己在家里闷得慌,准备到城里住一段,要儿子开车回来接她。晓晨在电话里支支吾吾、推三阻四的,她生气了:“怎么,做不了媳妇的主了?那是不是你的家?”儿子说:“当然是我的。”这么一说,他的底气就恢复了,他郑重地重复了一句:“当然是我的。妈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为了真正体现“是我的”,儿子没有跟媳妇商量就把母亲接过来了。
晓晨娘坐在儿子的车上来到省城的那天下午下着连绵不断的雨,整个城市被雨雾笼罩得严严实实,如同梦幻一般。儿子绷着一张脸不说话。她心里突然有些担忧,试探着问儿子:“方颖知道你把我接过来吧?”儿子哼了一声:“关她什么事!”她心里更加无法释然了。
儿媳的脸色果然不太好看,因为来得突兀,双方连起码的客套都忘了。晓晨进门后换了拖鞋,扔给母亲一双,然后就坐到沙发上看电视了。两个女人对视了一眼后都看晓晨。他不得不抬起头来看着她们。奇怪的是,这一次,他觉得两个人长相差距非常大,一个胖,一个瘦,一个高,一个矮,可谓泾渭分明。就是以前觉得异常相像的眼睛此刻看起来也不是一回事。妈的眼睛周围已经都是皱纹,媳妇的却是俏丽水嫩,他想从中找出桃花眼的迹象来,在刻板的环境中,却连一点儿踪影都没有了。
他突然高兴起来:“妈,方颖,你们都歇着吧,我给你们做饭去。”然后,他站起身来,似乎是迫不及待地逃离了现场。
母亲有些怯懦地坐下。方颖终于开口说第一句话:“妈你看,也不知道你要来,我得出去买点东西,家里什么都没有备下。”母亲连忙站起身来:“不用了,儿媳妇,家里有什么就吃什么,千万不要因为我来了再去破费,反正都是家里人。”
方颖笑了笑:“妈你说什么破费不破费,这跟你来不来也没什么关系,反正我们自己也得吃啊。”
晓晨从厨房里出来说:“方颖你去买点鱼和肉吧,妈喜欢吃荤。”他松松垮垮地系了一条白围裙,样子显得颇为古怪,一看就知道不是常下厨房的。
妻子还未答应,母亲就又来阻止了:“不要买,不要买,胡乱吃点就行,再说这阵子还不饿。”
妻子看了眼晓晨和婆婆,然后低了头去穿鞋。在晓晨娘看来,那一眼是不屑一顾,在晓晨看来,那一眼中含着不耐。他解掉围裙:“要不我出去吧?”妻子说“不用”,就开门出去了。
防盗门关上时发出巨大的声响,晓晨娘受惊似的看着儿子。
儿子愣了片刻后,一个人钻到厨房忙活去了。母亲在客厅里呆呆地站了半晌,有心想去厨房帮儿子,又看出孩子情绪不好。不知道怎么回事,到了省城,她发现自己又开始怕儿子了。
客厅里渐渐地暗下来了。
四十分钟后,防盗门被打开了,方颖提着一堆东西站在门口,喊晓晨出来帮忙。晓晨娘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
儿媳的脸上根本看不出喜怒哀乐。
晚饭的时候起了一阵风。晓晨匆匆地吃了晚饭,就出门了,说要去机场接一个北京的客人,晚上有可能不回来了。话是对方颖说的。母亲多了一句嘴:“都这么晚了……”
儿子说:“没办法,挣人家的钱呗。”
说到挣钱的时候,儿子的脸色是舒展的。儿媳却轻轻地“哼”了一声。
这一夜,儿子果真没有回来。方颖和婆婆在房间里说了半小时话,就一个人跑到客厅里去看韩剧了。婆婆百无聊赖地在房间里坐了会儿,有些憋得慌,想让儿媳陪着出去转一转,又不好意思开口。正犹豫中,忽然听到客厅里似乎有人说话,就屏息去听,声音却忽然没有了。过了几分钟,她轻轻开了门,看了看客厅,发现儿媳妇不见了。
她有些着急,就走到客厅里去,喊儿媳妇的名字。
方颖正在卫生间的马桶上蹲着,听到婆婆的声音后答应了一声。婆婆慌慌地说:“我没事,没事。”她想,刚才是儿媳在说话吗?
方颖出来后看见婆婆正在客厅里站着,眼睛盯着电视,就招呼说:“妈,你坐下看吧。”她没有坐下,而是犹豫着问她:“刚才,你在客厅里和谁说话了吗?”看着婆婆满脸的疑惑,方颖又好气又好笑:“是一个大学同学,我们通了个电话。”见她还是不放心的样子,又补充了一句:“和晓晨也是同学。对了,晓晨刚才说他不回来了,还嘱咐我安顿你早点睡。妈你跑了一路也累了吧?”
婆婆没有说累也没有说不累,只是神情萧瑟。方颖看见她闷闷不乐的样子,有些不明所以:“要不,我去放洗澡水,妈你洗个澡吧?”她说:“好”。
这下子她觉得心情好些了。但是等儿媳妇放洗澡水的空隙里,她突然想知道儿子在干什么,就鬼使神差地拨了儿子的手机。儿子的号码,她一直牢牢记着。
手机接通的时候,她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就把刚才方颖和人通电话的事和儿子讲了,还补充了一句:“她说是你们的同学。”儿子“嗯”了一声,听起来很不耐烦:“妈你还有别的事吗?”她说:“没了,就是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儿子说:“最早得明天了,妈你早些睡吧。”然后不由分说就把电话挂断了。
她拿着听筒,有些怅然若失。
方颖放好洗澡水出来时她没有敢看她的眼睛,而是扭头又看了一眼电话机。方颖说:“晓晨来电话了吗?”她答非所问:“不是。”
洗澡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好像被人监视了,又无来由地感到一丝委屈,就借着撩水声悄悄地哭了。
这一夜,晓晨娘睡得很不安稳。黎明五点,她就摸黑起床了。她没有到客厅里去,而是呆呆地坐到阳台上,一直坐到窗户里透进第一丝曙光。她突然动了返乡的念头。
吃早餐的时候,她装作随意地把这事对儿媳说了:“你们都忙,我待一两天就回去吧。”
方颖有些吃惊地看着她。
她错开了儿媳的目光,还是把想说的话说了出来:“媳妇啊,晓晨这孩子脾气不大好,大事小事你都得担待些。”见媳妇没有反应,她又说:“他的自尊心强,自从十五岁没了父亲,他就听不进我的话了。你的意见,我想他倒是能接受的。不过,不过,你不要总是数落他。他有逆反心理。其实,哪个男人又不是这样呢?”
方颖张了张嘴,想反驳她,可是终于没有。她缓缓地点了点头。
婆婆感激地冲她笑了笑。
晓晨在回家的路上感到眼皮子直跳,他摸出手机给家里去了电话,却久久没有人接。再打,还是如此。他气得把手机往旁边座位上一扔。手机却在这时响了。
是母亲打过来的。她在电话里说:“是你吗?儿子?”
晓晨说:“啊,妈。方颖呢?还没有回去?”
母亲说:“刚进门,又出去买菜了。你是不是到家门口了?”
晓晨说:“马上就到了。”
儿子和媳妇同时进的家门。这阵子看起来好多了。他们说说笑笑的。
儿子说:“妈,看我给你买了什么?”说着话,竟然像幼年时那样,把手捂在了背后。她说我哪里猜得出来。儿子说:“你就猜猜看。”母亲说:“不会是首饰吧,你知道娘最喜欢首饰了。”
儿子说:“知子莫如母,果然一猜一个准。”
晓晨果然给母亲买了一份珍贵的礼物,是一只金灿灿的手镯子。
媳妇说:“妈你戴上试试,不合适的话就去换。”她依言试了,大小还行。她高兴得连连夸奖自己的儿子。晓晨脸有得色:“妈,这比来生叔买给你的那只好吧?”
母亲和媳妇都愣了一下。方颖反应过来了,说:“李晓晨,你真不是东西。”
须臾之间,母亲脸上的泪水顺腮而下:“媳妇!不许你说他。这是我造的孽啊。”
方颖气得发抖:“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儿子。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母亲。”她说着话,仿佛比谁都气愤似的,摔门出去了。
母亲脸上的泪水汇成了一道道小溪,晓晨的心突然被母亲的泪水刺痛了。他抬起手来打自己的嘴巴:“妈,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
母亲摆摆手:“人老了老了,却越来越娇嫩了,这其实怨不得你。”
晓晨说:“方颖说得对,我是个禽兽不如的东西。”
母亲说:“胡说八道!以后她再骂你,你就大耳刮子扇她。”
送母亲回乡的路上,晓晨给方颖发了条短信:“颖,对不起,我陷入了深深的罪责之中。我可能已经病入膏肓了。”
十分钟后,他收到了一条粗俗的回信:“放你娘的狗臭屁。”
晓晨感觉十分疲惫,回头看看母亲,似乎已经睡着了。母亲的嘴角挂着一道口水,看起来丑陋无比,晓晨怎么也不能把她同二十年前那个艳如桃花的女人联系在一起。从母亲到“那个女人”,这是一个不小的转折。每每想到这一层,他就浑身冷汗淋漓。现在也是如此,晓晨握拳敲了一下自己的额头,他觉得自己的脑子里长了一颗坚硬的长钉,他无论如何都没法子把它彻底地清除出去。
三
然而年轻时的母亲的确是个长相不凡的女人。“回眸一笑百媚生”——这是来生叔扣在母亲身上的一顶大帽子。多少年里,村里许多上了年纪的男人说起当年的白玉兰姑娘,都会拿出这顶帽子来吓人。多少年来,他们对她垂涎三尺,但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近她。只有那个来生,他们一致认定,只有那个能说出“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来生,才是她除了丈夫之外的惟一的相好。
来生不是本地人,是县教育局派去教书的,本来说是教三年就可以调到城里去,哪知道三年头上,上面不再提调走的事,他也没有追问。过了好几年他才知道,就是那一句“回眸一笑百媚生”坏了事。有人跑到上面去告状,说是他作风不好,在村里搞女人,本来,教育局的头儿正在为他的事发愁呢——想进城的教师太多了,僧多粥少,可他又是他们专门到省城挖来的师范学院的高材生,他们当初的许诺不能不作数,这下好了,是他自己把好好的机会断送了。他们考虑过,万一他来质问此事,就把这个作风问题作为挡箭牌,但是他始终没有来,由此可见,“这个作风问题是真实的”。
当年的白玉兰姑娘并不懂得“回眸一笑百媚生”到底是个啥意思,他只是从男人们的坏笑里意识到这一定不是句好话。如今美人迟暮,她唯一记忆犹新的也是这句话。她只是已经判断不出自己当年的笑何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就是这一笑,导致丈夫与他情感上的彻底决裂,他先是狠了命地要她,然后才是彻底拒绝与她同床,之后就持续不断地外出,以此来回避那些经年不断的疯话——从这一点看来,他是懦弱的,这也是她最终能够狠下心来背叛他的最大原因。
晓晨记得来生叔第一次来他们家是在他六岁那年。他满手的粉笔灰弄得他很不舒服,偏偏他总喜欢摸他的头。晓晨拿拳头砸了一下那一只并不算太有力的手臂,但是母亲后来呵斥了他:“这是薛来生老师。”连名字都是如此拗口,晓晨本能地判断他不是一个好人。可一年之后,他就随着这个人走进了校园,同学们都叫他“杂种”。他听到了总是微微一笑,并不阻挡。因为这个原因,多少年后,晓晨都在憎恨他。他的默许助长了
那些坏小孩的气焰,小学几年,在他的心理上留下了很深的阴影。十二岁生日那天,他对着刚刚从外地赶回家为他庆贺生日的父亲说了句自己在学校里“备受欺凌”的话,父亲就恼羞成怒地叫来了母亲,骂他“贱人”,母亲回骂他“懦夫”。后来他们两个人大打出手。他看着殴打在一起的父亲母亲,异常绝望地拿菜刀切掉了自己的一小截指头。是他的尖叫声阻断了他们之间的互相伤害。
再后来,他就陷入经常性的头痛,一直持续了五六年的光景,父亲去世后病情日重,直到他考上大学后才不治而愈。
在父亲的葬礼上,他做出了平生最为忤逆的举动:他把一壶屎尿倒在了母亲的炕上。母亲大哭着要去上吊,被舅舅们拉住了。他因此受到了很严厉的惩罚:舅舅们把他吊到树上,用赶牲口的皮鞭抽了他三四十下,打得他皮开肉绽,直到母亲哭着为他求饶,他们才把他放了下来。
被打得奄奄一息的晓晨记住了舅舅们疯狂的脸,后来他再也没有去看望过他们。甚至在他结婚的时候,他都没有同意舅舅们前来参加他的婚礼。母亲为此跪在了父亲的灵位前祈祷:“孩子他爸,你在天有灵的话就让老天爷把我收了去吧,孩子没有错,一切都是我造的孽啊。”他烦躁地拉起了母亲,说:“他们可以来,但我不会叫他们一声舅舅的。”
来生叔也出现在他的婚礼上。这次不是他,而是他不请自来的六个脾气暴烈的舅舅出面,拿几根粗木棍把为人师表的薛老师一顿好打。可怜的薛来生老师由此落下了腿疾,后来就一蹶不振,听说连课都讲不好了,经常神情恍惚地对着学生们痛哭失声。婚后第二年,晓晨带着复杂的心情去看望了他。他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脸色灰暗无光,看样子将不久于人世。由于行动不便,他的屋子里充满了酸臭味。晓晨走的时候塞给他三千块钱,被他坚决地拒绝了:“你老子养子如虎。薛来生这一辈子终于败在了那个孬种手里,看样子只能等下辈子了。”他无畏无惧地说这句话,令晓晨脸上一阵难堪。
不过他还是很快就谅解了他。
母亲在回乡后的第二天去看了两个人的坟。
当时的情况是堂兄后来告诉晓晨的。那天下午,堂兄正在地里锄玉米,隐隐地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哭声,他悄悄地走过去,就看到了婶子正跪在叔父的坟前,已经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或许是因为悲伤过度,她始终没有发现身后有人。
母亲的哭诉非常漫长,大约有两个小时。堂兄觉得情况有异,就一直没敢离开。母亲的话语中充满了对父亲的不满。堂兄听得非常吃惊,他说没想到婶娘和叔父在生前的感情如此糟糕。
母亲历数父亲带给她的不幸,即使在他死后多年,这不幸都如影随形地伴随着她,如果她有选择来生的权利,她说自己一定不会再跟他了。他那么胆小怕事,一辈子都在躲避。躲避别人的冷眼冷语,躲避她对他的责问。甚至在她向他提出两个人分开过的时候,他都采取同样的方式。因为顾及家里人的感受,所以她才坚持到了他临终的那一天。她本来以为他死后自己就解脱了,万万没有想到,孩子却粗暴地截断了她的后路。她说,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老李啊,你怎么给我带来的是一场噩梦啊。
堂兄说:“婶娘离开叔父的坟后并没有回家,而是去看了另一个人。”讲述到这里,堂兄停顿了一下,晓晨的眼睛一挑:“是来生叔吧?”
堂兄说:“看来你都知道。薛老师的坟和你父亲的坟只隔着一条马路,五六分钟的时间就走到了,但是这段路,婶子却停了好几回。停一回,哭一回,我在后边看着都难受得不行,差一点就喊住了她。后来,她终于在坟前停下来了。你猜你娘头一句说什么?晓晨你打死想不出你娘说的是什么?”
晓晨说:“哥你有什么屁快放,别拐弯抹角的。”话一出口觉得不对,堂兄挑了挑眉:“你个狗日的!”
堂兄说:“婶娘说,早知道事情会变成后来那样,还不如在孩子不懂事的时候就送给你当儿。反正,那死老鬼早就在外面有人了。”
晓晨吃惊得打断了他的叙述:“鸡巴,你是不是瞎编排,你要是胡说半句,老子拧断你的脖颈。”
堂兄说:“日他妈,你不信,找你娘对证去。”
晓晨沉默了下来。堂兄所讲的一切使他心里的火越烧越旺,好几次,他都想跑到厨房里拿把菜刀把眼前的这个讲述者给宰了,像宰一只鸡那么容易。他觉得自己理智的防线已经崩溃。
……看来一切都不像他臆想中的。母亲果真有过同来生叔一起过活的愿望,这愿望的产生远比他想象的要早。难怪,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母亲也有过异常快乐的时光。晓晨记得最清晰的事是,母亲在那些年里经常去镇上赶集。母亲去赶集的时候,无一例外地都会把他寄放到姥姥家……原来,这些事情都是有因由的,原来,母亲早都同来生叔达成了默契。他们是借着赶集的机会躲避村人的耳目,到镇子上幽会去了。我的亲娘啊……晓晨痛苦得抓住了自己的头发使劲地揪。
堂兄又停了下来:“有些事你不知道也就罢了,反正我嘴皮子上贴了胶布,打死也不会说给外人听。”
晓晨说:“你讲,你全给我讲出来!”
……看起来,母亲并不只想过把自己送给来生叔当儿,而且在一计不成的时候还曾想过为他生一胎。只是,这个文弱的书生没有胆量这样做。母亲为此同他几乎决裂。那么这一切,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大概就是在“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典故出笼后至多一年吧。应该说,两个人把事情隐蔽得不错,因为家里的人尽管猜测,但谁都没有抓住把柄。年复一年的,父亲渐渐知道了所有的底细,但并没有非常彻底地把问题解决掉。母亲千方百计地打听,终于知道父亲在外面的不轨行为。因此才产生了同父亲分开的念头。但到底没有抗得过时间。十几年的光景,似乎一眨眼就过去了。母亲毁在了父亲手里,薛来生老师,同样毁在了母亲手里——
晓晨不能想像他们在一起也曾度过了好些年的快乐时光。他拒绝倾听堂兄在这个环节上的讲述:“你他娘的给我闭嘴吧,这些肮脏的东西,我不要听。”
然而他到底不能屏蔽自己的记忆。那些影象在他的心底里扎下根来,根深蒂固。它们形成了一个非常坏的作用力,就是他一旦想和妻子亲热了,就会想起母亲与来生叔。这种想像把他折磨得苦不堪言。
有一天,他刚从妻子身上下来,看见妻子做出一幅沉醉的样子,她桃花一般鲜艳的脸色对他构成了一种伤害,她目光中的风情更是对他构成了一种伤害,他就恶狠狠地骂了一句:“贱种。”
妻子终于被他神经质的情绪转换弄怕了。她向他提出离婚。他同意了。
与此同时,他的代理主任生涯也结束了。他的多项考核都没有通过。同事们用了很不友好的评价:“喜怒无常,类同小人。”如此一来,领导认为他难挑重担,就毫不客气地把他的小小官职撸掉了。连谈话的程序都略去了。
同前妻分离财产时,他慷慨地放弃了价值三十多万元的住房,而选择了八万元的定期存款。在收拾东西的时候却不见了母亲的那张照片。他怀疑母亲来的时候把它取走了,可又不好追问,只能揪住前妻的小辫子不放,他要她把属于他的私人物件都吐出来。方颖气愤了:“后悔了就早说,现在不用装慷慨了——说吧,你觉得我补给你多少钱合适?”
他骂她:“老子不稀罕。我是问你那张照片的事。你有没有看到我妈的那张照片?”
方颖仍旧气咻咻的:“你是说这个?你妈早把它烧了。那天下午,我在卫生间无意看到的。她可能以为我不在家。”
后来,她还补充了一句:“不过,你妈可能忘了收拾,烟灰缸里留下了一点灰烬。这些天里忙忙乱乱的,那东西应该还留在那里呢。”
他果真在客厅里找到了那只将近废弃的烟灰缸,缸底果真铺着一层浅浅的灰烬。
临出门的时候,他郑重地对前妻道了歉,然后自嘲似的说:“瞧这狗日的生活!”
责任编辑: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