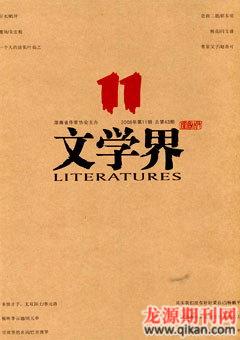一个人的迷雾
叶临之
1
我正在走廊上看报。一沓一沓的,是清洁工随手扔在那条乳兰色座椅上的《东京晨报》,纸面非常邋遢、脏污。捧在怀里,我弓着虾姿,而松在里面的小绿屋里接受检查。
我想时间一定会短,没有走开也并没有进去看。里面,张大夫正在规劝着松。
大声点,对,大声点,能告诉我你什么时候身体感觉不一样的吗?
不知道?你说不知道,没有吧,你肯定知道,你很害羞。能想象得出在张大夫面前松像个小孩,我把头掸了掸,瞟了一眼,张大夫正捏着松的手腕把脉。松的局促让我挺想发笑。其实,张大夫的口气挺像我。早晨,松一醒来就说肚子不舒服,接着迅速地奔出盥洗间,门忘记了关,就哗啦哗啦地开始吐。我跟上,悄悄地把门关上,靠在门槛上在听。所以,松一打开就看见了我。我有点像个做错了事的小学生。
重新回到床上,松说我挺像她隔壁家的小男孩,跟她抢过果冻。
就在早晨,我们决定来看医生。先是抛了一通色子,来决定。这星期日,我们有的是时间。但至于选择谁,中医还是西医,松到底是病了,还是其他怎么了,我们两都无定论,答案各异。这其实是两个问题,不能再靠抛色子决定了。松也不知道自己是否病了,有点作呕。我伏在她腹部去聆听,听了许久,万籁俱寂。我心里却高兴了,我说,那肯定怀孕了!
我说我都听到你肚里咕咕叫,松的脸彤红彤红的,腮边浮出些茄子紫。没有吧,有吗?我不相信。松去看台桌上那一堆一堆的书,愣愣地说,我怀疑是昨晚吃烤龙虾过敏。
对,我心里也相信是松吃虾过敏。那肯定是要看医生。至于医生的选择,她还是想去看中医。这些年她一直怕花钱,张大夫是我朋友,诊疗费会免的。但我立马提出反对,我说张大夫是我朋友,而你肯定怀孕了,怀孕检查,古人说是要宽衣的。松的眼皮吊了起来,懂不懂医啊?还亏你是人家医师的朋友,那是西医,只是照B超镜而已。最后,松懒得跟我说了,抛给我几个字,住嘴!别胡说八道。
我屈服,她是老师。我说,好,俺住嘴!俺们新新人类,丁克。
这是早上吵嘴。喝了豆奶,啃了几片汉堡,到九点就把床上商议的事忘了。我去树下的躺椅上坐下,正想看一本书,没想松还记得,松很生气地攥着我的胳膊,坐车到了张大夫的诊所。
其实,我有点恐慌,我这一生最怕两个职业了:医生,老师。我小时没被少批评过,再说现在我也算是一名老师,工作栏上写着“国际高等文学研修所讲师叶子诚”的名片,可我实在讨厌老师了,要不是松的执意,我恐怕早就回国了(不过,我发现我一直活在两为其难的困扰中),因此,我面对着世界上最讨厌的工作;而医生最接近于死亡,特别是当医生手上的针管扎进屁股,从骨子里放射的痛更让我发觉源自心灵的畏惧。
我发现我对恐惧与死亡的事联想特别多,前些日子,小区里我们这种背景的人家相继被偷。都是华人。日子总不太太平,偷车、爬楼抢劫,像蜘蛛侠,必须时时防盗、防劫。都与死亡、争执这些可怕的事相关。这一沓报纸又出现了,第一版是桩绑架谋杀案,一个小男孩非常优秀,被杀死在马路边,作案非常残忍,报纸连血肉模糊的遗照都被放大登出来了。
2
老师是松的职业,松非常优秀。我联想翩翩,我想肯定有她纵养的成分。按东方人的气质,其实,她非常漂亮,体型、面容、轮廓、嘴唇的线条都十分的迷人。我不清楚这是命运还是什么。相识是四月,时间2003年。后来在从东京北郊开来的车上,又经常碰面。事实上,一开始她就是我的老师。日语老师。
是在日语速成班上。
“a—i—u—e—o—!”
我总是不失时机地读成“a、e、u、e、o——!”偶尔挺像吹一支笛子,塞腔了似的。但我不是想捣蛋,方言而已,我从小生活在方言区。连汉语都不及格的。加之,从小我讨厌父亲的职业,讨厌他作为街上一名卖大饼鸡蛋、葱花大饼的无业人员颐长的吆喝声。父亲越是如此,我越发背道而驰,因此我小时的外号名小短笛。但松不放过,她一再地用嘴型示范,可越读我越像一只笨拙的鹦鹉,嘴里出来的竟都是“a、u、e——o——!”,到后来连“e”也没了,乱了套。十五遍不下,松也没了法子。她左手的那只松木杆(教鞭)当起了拐杖、在地上笃笃地敲,头抬起来。我看着她,表情像阿姨手里的糖果本应分给小朋友一样理所当然。
你说日语、很像松鸡叫。她突然说出来这么一句。完全、百分之百的汉语!我相信我们全体三十五名同学都傻了眼。他们集体看我,又看了看涨红了脸的松,以莫名的速度从口腔里爆发一阵哄堂大笑。那时我站起来了,我挥了挥手说,都三十来岁的老大爷们了,还笑,笑得像个猪猡。大家的笑被镇住了,但却开始窃窃私语:对了,她怎么会讲我们的话,怎么会中国话呢。
松也令我也相当惊讶。她的汉语很流利,但我的关注点并不在这里。当松抬起头,拿起木杆当拐杖的时候,我在看她脖子上那纤细平滑的颈圈。从小起我就敏感,养成了偷窥的习惯,我总被自认为美的东西所迷惑。但大家笑时,我当她是一位被嘲笑、而生性胆小的老师了,就像她的体型表征一样。我站起来只是为了帮她平息起哄。
没想她又说话了:“叶君,下课、请到我的办公室!”
又说的是汉语,她并不面怯。大家的表情扭成了奇形怪状的树根状。我看她是有点恼了,眼睁睁地看着我,直到我坐下。
大概以为我是成心捣乱,肯定把我当成了问题学生。但我不敢辩解也不敢不去,课后还真像小学生被老师找去谈话一样,去找她。
这次让我在松的印象里形成了始终是一个笨学生的形象,但是要说,如果没有这次谈话,我和松大概就不会真相识,就没有今天甚至远至2030、2040直至共约死亡的那一天的结局。因为过后不久,所里对日语速成班的举办没了信心,领导对我们这些老学生没了信心,三个月后速成班被解散,松回到了她的语言学校。
那天下午,太阳懒洋洋的,我抱着无所谓的心态。对学不学得好日语我不太感兴趣。况且,我的外语专长是英语,何况我又不想在这呆一辈子。
是在所里单独腾出来的一间小件办公室,我走到办公室门口,从窗子里可以看到松和另一个女人坐在一张大木桌前,松在批我们这些老学生的作业,另一个女人捧着一面小镜子在办公桌前整冠。我立在门口,叩了叩门:“良木松子小姐,我可以进来吗?”屋里传出来局促的一声“好”,我打开门时,松迎了出来。
松倒了两杯水,我对面坐着。我们的谈话就这么局促地开始了。
“你、大概多大?”
“二十九了吧。”
“哦,真对不起,比我还大、一岁,一岁。”
“我妹妹也是的。”
“那、你以前、来过吗?”
“第一次。”
“哦、那你觉得语言、很难吗?”
“不算吧,只是我有点大了,年龄到二十五岁记忆退化。老了。”
“老了?真幽默,其实其实,我叫你来是想纠正一下你,对,口型?你发音困难,我觉得是舌头短了。”
“我一直是如此,打小时。”
“别介意,我这完全是老师、老师学生间的对话、
没其它意思。”
“多谢,松子小姐。”
“能让我像医生一样看一下吗?对,舌头。我想不纠正不行,想对你提出具体方案,真的。非常非常想。”
“……”
“那请张开嘴,像我,鼓足勇气,紧腹收肋提气,对。”
“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
3
我刚看完报,在打盹,松在里面叫了起来,像刚刚发生了噩梦。
钟表时针已经整整走了一圈了。打盹前,那个孩子的谋杀案我已经滤过了三遍,除了血腥的情节,大概我也能把作者的叙事套路背下来。正要起身哈腰。松又在里面叫了起来。
松叫时,我扭头去看。松也在寻找我。(她一定以为我按她的吩咐去菜市场买菜去了)。但我和她的眼光很快对视上了,松的脸上透着风云莫测的光鲜。像熟透了的芒果。我进屋忙问怎么了怎么了。她和张大夫秘而不宣。张大夫在收拾仪什,他拍拍我的肩膀说,挺好,以后你要多加注意松的营养。这真是莫名其妙的。告别了张大夫,从医院出来,我一再追问松到底是怎么回事。直到车上,人员拥挤的时候,松才轻轻地把嘴凑近我的耳朵,说:你猜对了,我怀、孕、了。
我有点没听清,真的?
你早上的坚持哪去了,还要不要抛色子?
旁边的一个日本老太太扫了我们俩一眼,这时我们才没敢说话。
松她怀孕了!?现在的松在规划整个妊娠时期,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面容浮满臆想,再是感觉满足,像一块抹布整日坐在原处,全无了先前生活的快节奏,一天到晚,都在拿日历比划着休假计划。这可急坏了我,房产期付呀,旅游啊,现阶段这都是大问题。刚开始的几天,我心里磨蹭,这该怎么办?我打了电话给张大夫,觉得有必要确认真假性。张大夫说,不假,已经一个半月了。每月来检查一次,朋友嘛,我这照B超镜很便宜的。我嘴上虽说哦哦,但当时我差点忍不住想提一个可能伤害松的问题。
我们想想是哪一次?我和松都在猜测这次意外之祸。
每次都很安全的,我说。
没有吧,那一次,你还记得吗?在车上的那一次,樱花很漂亮的,松肘着半臂,眼巴巴地看我。
是那次你和你同学去送你的“潜水青蛙”,我去找你的那一次?你哭哭啼啼的那一次?
一说起这个隐身人,前男友子甘,我就不失时机地反讽她。
松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怯怯地说,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嘛。
事实上,自从那一次叫我去办公室,松就开始单独给我补课,先把“i”补回来,再接着补会话。我学完“谢谢”、“对不起”、“请多多关照”之类的寒暄,日语速成班就解散了。但此后相当一段时间,私下里她还是教我学日语。现在,我这本地语言倒成了班上最好的一个。2005年传统的“樱花祭”,松专门邀请过我去她老姆家新泻县赏过樱花。我才明白松为什么懂国语。松的老姆跟我说,松从小就喜欢汉语,她的邻居有一户“二战兵”,华裔,大连出生,四几年才从青岛随日本军队退回来,而“二战兵”的孙女是松的女友。“二战兵”被征做过汉语翻译,来新泻后,顺便把汉语传授给了邻居家的孩子包括松。“他不好战,可惜她却死了。”他孙女在女子学校学教育专业的时候,箱根的一次攀援中意外坠入温泉窒息身亡。
“良木松子就是她的名字,我原来的名字倒不用了,懂吗?纪念很重要!”松说。一次,我们还一起去新泻县给这个已经安眠了的女孩献过鲜花。
但松说“在车上的那一次”,我反而有点恼怒。那次她是去告别前男友,“潜水青蛙”,一个叫子甘的前歌手——甚至谁能保证他们两不会发生什么事?
这真的牵扯到太多的问题!来得这么快,这么急。有些话还只能藏心里头,例如对那个“潜水青蛙”的怨气。但事却很明摆,松和我在卡板上罗列了一通由于那天的呕吐带来的全部新的、崭新的事情:回去?呆在这?工作?还是陪松当“宅公”照顾她。这不止是松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作为同绑在一条线上的蚱蜢。你看着办吧。松噘着嘴看我,这让我反而不习惯,以前我一贯听她的,现在她倒愿意听我的。这或许是人脆弱时需要安全感的表现。
这些天,我脑海里一再纠缠着各种错象。上班如此。这是不是我们生活的一个不良预兆?
4
前几个月,松把一大堆彩礼贺信发出去了,按老家的习俗,雪花一样,家里还到处贴满“庆生薄”,和老鼠生子的卡通图片;还刻意要我去了好几趟婴儿用品市场,买了许多套宝宝服,并且松还装模作样地开始和贩子讨价还价。每次从婴儿市场回来,又去张大夫那磨蹭好一个下午,这可够消磨我的耐心。万事俱备,松还想安排一次去“大卧佛”求签,以便取个好名字。
很明显,松是想把怀孕的事昭告天下。包括我所有的同事朋友,张大夫呀、李小姐呀,刘所长呀,小郝司机呀。我说低调低调,你就不怕被绑架?松说谁敢绑架我?惶惶不可终日写在我的脸上。而在一华人出租车公司做无聊司机的小郝,当即接到贺信,就笑嘻嘻地给我煲来一个电话:“这么快?你们结婚才半年。”对他的质疑我觉得可恶。我说:“还有没结婚就生小孩的呢。”小郝马上回应:“那可不一样喽,这是外边,嫂是漂亮的有艺术感的女孩。”我说:“去你的。那你小周在航空还不漂亮?”
小郝说:“她是飞的老母鸡,安全,我觉得是有必要提醒你一点。”
小郝的这一通聊天搞得我心烦。下班回来,我再一次想起那个叫子甘的人。我甚至产生了和他联系的想法,只可惜他去了札幌。
一天,在所里我却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对方那混浊的比大提琴还低沉的口音,着实把我吓了一跳。电话一通,对方就问松子还好吧。我马上意识到这就是那个与我未曾谋面的松的前男友,子甘。他是一个颓废的前男低音,因吸毒而荒废,但他浑厚的嗓音还在。听说他已去了札幌,为何又出现在了东京?我第一反应想问他,你是谁呀。但出于对松的尊重,我说,你就是子甘吧,札幌过得还好吧?
电话那边又冷生生地抛过来一句,我要找良木松子。
是他!我腿上发凉。但我有理智,我笑着说,万万不行的。
他从鼻孔里震出一声,你们才认识多久?
我说,她已经怀孕了。
电话那边,他的回话倒吓了我一跳:我知道她怀孕了。
这时我生气了,说完“你知道她已经怀孕了,骚扰不犯罪吗?!”我就撂了电话。
回到家里,我又见到了懒洋洋的松,被宽实的孕服包裹的松站在客厅等待着我。但我一看到她,气又上来了,我质问,你是不是把啥贺信发给那个啥青蛙了,没事惹事!
说起青蛙,松反而高兴了,我第一个发贺信的就是给他!让他知道代价!我取得了重大胜利。我问,什么代价?松不肯说了。其实我在琢磨这之间的故事。
一个月后在所里,我又接到了子甘的电话。很奇怪,他竟然也懂汉语。但这次礼貌了许多,叫我“叶先生”。他想问松是什么时候怀孕的。我名正言顺地告诉他,我们已经结婚了。
到这时,电话里停顿了许久,我甚至对这个可怜的男人产生了同情。他不出声了,他肯定是在路上打的手机,甚至话筒里传来电车铃声,显然在车站,但电话
还没挂,一两分钟过去,我喂喂了好几声,还是没有回音。
直到半个月后一个下午,他才出现。那天,所里的人都出了差,我一个人留守,在桌上打盹,突然座机响,我抓起座机话筒,话筒里又传来那个下沉的低音:那我不想见她了,我想见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约个地点,我们尽快见个面,当面说说。
我的口气顿时硬了许多,我故意冷笑一声:也好!我正要找你,你自己说吧。
5
对于那个前歌手子甘,我的记忆基本上模糊。自从他2005年消失之后更是如此。
惟有一次,松带我去找过他一次,那还是2004年。他还是歌手。松的耳朵上挂着昭示青春的两个银亮的大耳环。我们从唐人街出发到音乐町去找他,接待我们的却是他幼小的学徒工弟弟。当初,他弟弟指着我问松,这是谁。松说,我男朋友。他弟弟马上反唇相讥,我哥不是你男朋友吗?那一次弄得相当尴尬,我本来是来听音乐会的,结果被这一闹搞得全无兴致。
但那小子还是把我和松带到他哥的工作室看了,都是一些很能弄出声响的乐器,例如钹,鼓,木琴、簧管,各自在高钠灯的照耀下闪光光的很是耀眼。子甘不在。他弟说是跑场子去了。我和松在工作室内坐了一下,松就向我说起子甘的历史。“他过得很苦,拉皮条,懂吗?童年他是孤儿。”到这松想哽噎一声,接着以怀疑的口吻问我,“你捡过破烂吗?”我当然只有摇头,松的眼神马上朝我鄙夷过来,我很想辩解:“我只是有一个父亲而已,但有父亲和没有父亲又有何区别呢?我父亲只是一个在街口卖大饼鸡蛋、随时可以被城管或者恶霸们驱赶的城市无业人员而已。”但我的耐心很好,我只听松说。松说完,蹲地上去打开一个小尼龙包的拉链,熟练地从中取出一沓东西,是相片,起身她指给我看,这就是子甘。
相片上的那个男人看不太清晰,因为他戴棕色大墨镜,大墨镜几乎遮住了整张脸。但我感觉他有点像黄家驹。那种孤傲,同时也适合在黄昏里游荡的人。
音乐会要开始了,正想从他的工作室出来,他的弟弟还在大胆地追问:“你准备嫁给这个丑八怪?”当时,我恨不得凑过去骂他几下。但松及时地扯住了我说:“走吧走吧,都过去的事了。”
似乎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才听说子甘准备消隐的。我和松去找过几次。都没有音信。这个男人一直只肯见松也不肯见我。直到2006年,松明明确确地告诉我,他在吸毒。
我们把相见的地点约在一个主题公园。依着那相片里模糊的记忆我去与他相见。
我还有些紧张,但开始是我多虑了。一进主题公园,我就看到一个男子坐一张石凳上弹吉他,周边站满了喝彩的小孩。我有些怀疑是他,但想一想肯定是他了。在这个吉他人面前站定,他就抬头看了看我,手指“噗”地一声扣弦,停止了弹奏,孩子们听不到吉他自然就散了,一个男孩给他一颗棒棒糖作为报酬,他也接受。今天的他没戴墨镜,我仔细观摩了一阵,脸型消瘦、五官精致、眼神黯淡无光,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可怕,但与那相片里的冷漠大致相同。
他一看到我站在他的面前也认定了我,打量了一番后,一声冷笑,走吧,换个地方。
我跟着他走,蹿过了条条巷巷、铁道、集市。恐慌感应时具有。进了一个被废弃的仓库,接着仄进一个铁房,里面到处透满了钢琴的烤漆味。屋内漆黑而冷静,估计是个琴房。天窗一炷的阳光打下来,屋里迷雾丛生。他坐了下来,也不说什么,直了下腰板,敲了一通琴键,指法优雅,那时从天窗来的光线正好打在他的面孔和手指上,体毛历历在目,那一刻,我感觉他是一个非常有艺术感的钢琴家。
弹了半刻,霍地,他的面部扭曲。可能是毒瘾发作。“啪”的他剧烈地阖上钢琴盖,十指蜷曲,反过身来看着我,这让我毛骨悚然。
我先开始说……你在外过得不是很好么?
我知道你们是结婚了。他不接我话,很泄气,但音色如D、C区那么浑厚。
这时,我倒慷慨,……我们可以成为朋友。我的脑子很灵活,我又想把话题扭转到有利于我的方面,一转锋问道,我想问一个问题,四月十九那天为什么松哭哭啼啼?
我惹她?我非常讨厌她!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喜欢你,她过来跟我说再也不能见我。
我的目的达到了,胆子也壮实了,我倒觉得他真是一个可怜人。我说你找我什么事?或许我可以帮你点什么?
他已从袋里抓出一支“烟”,抽了半刻,面部表情才缓和,神色讥讽,你帮我?
是的,即使是作为一个以前的朋友。我很诚恳。
他笑了,别逗了,松子还欠我钱。你俩只要还清就可以了。
我愕然,从没听说松还欠人钱。你能解释清楚吗?
他说,那好,我说清楚一点,我是歌手的时候,她在女子大学学费、生活费都是我赞助的,我连给弟弟都舍不得。后来她工作,我托人又找朋友,几乎花了一个小金人。她老姆的生活费也由我寄送,语言学校,你以为她家一个乡下人能到这种地步?那正是我最辉煌的时期,现在我后悔了,我想把以前花在她那的钱收回来,连本带利。
我吓了一跳,还从来没听松说过。再说,一个吸毒人我们也无法供得起。我说,我们都只是公务员,没什么富足的钱,这里也不好过,我知道你现在急需帮助,平时倒可以赞助你一些生活费,不过,你还得唱你的歌。
唱歌就那么好?都他妈的假东西。别装!你们没钱?你们怎么千里迢迢地能跑出来?我见到一个就他妈的一个比我有钱,什么唐人街呀,什么卖唐装茶叶的,没钱?骗鬼去吧。再说,我这么可怜?一点钱来打发我?他笑。
对他的偏见我眼神发怔,没有了谈下去的必要性。
突然,他嘴里哼哼的,掂起腿旁的吉他捏弦线,表情不屑,声音顿失地说,到底是打算出一次血呢,还是想证明松是不清白的?
看着他又掏出一支“烟”来抽,我说,这是误解,别说这么难听,看在以前松的份上。
这个男人很生气,你别跟我说她!我注意你很久了,这是两个男人的秘密,如果她知道,你能想象到结果!
6
我差点当场就答应了这个人。
诚如他所说,他关注我是在我跟松学日语时起,那天,她竟然拒绝了他的晚宴邀请,专门来陪我矫正口型“啊——”。可都是亲眼所见啊。接着,他又把恨深深地拉远,甚至远至那个“二战兵”身上,这个老人总是唠唠絮絮地教他学蹩脚的汉语。他总是不能理解。
我终于明白了这几个月、出海后,脑里为什么慌张。
这一次他显然是有备而来的。但又不能报警,否则他会否反咬一口?如果松知道,她是否会恨他。如果是的,松也答应,那我们偿还这个前歌手所谓的恩情也未尝不可。孩子可以不要,房子可以转让。他肯定是缺钱花了。但花了这笔巨资我们就可以一刀两断,再也不会牵扯到什么迷津了。
沙发上的松听我一说,她没有责问,反而大骂那个子甘。
说的是人话吗?以前我确实受过帮助,可是有代价的。青春就是代价。
到此,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我马上会心地笑了。因此,松怀孕也并不是一件坏事。我发现自从松怀孕后,几个月以来,她的立场完全就偏向了我,她不
再是老师的身份,而成了一个温顺的妻子。这就是东方人的优势。在一场战争中,我完全胜利,这是关于一个人的一场迷雾。如今,尘埃落定。
我说,那、该怎么办?
我要见他!我要问他,这些年我节省,他到底又花了我多少钱?
我更开心了,我说,好啊,只是他恐怕不想。
他留下了什么联系方式没有。松问。
我摇头,只记得他带我去一个琴房,在郊外。
松说她好像知道,叫“介之龙”对吧。果真如此。这次,和松坐车到达后,我把那个仓库打量了个通透。松说这里她也曾来过,从前很热闹的,是一个东京艺术联盟的所在地,那时子甘是里面的核心成员,只可惜前几年破产,老板也潜逃了。只剩下铁屋子和满房间的乐器。我们又蜇了进去,找那个琴房,来到这间绿铁皮的房子前,铁门紧锁,锁上面落满了灰层。又请人把锁砸开,如今这个所谓的琴房连那架废旧的钢琴也不见了,里面散落着一两只老鼠,松失望了,我们只好无功而返。
我们回来后又去了原来的音乐町找过。都是无果而终,实在没法子了,松说我们去乡下。他肯定在。冬十二月的那天,天气异常的火燥,松挺着大肚子和我往他神秘老家赶。他们是新泻同乡人。可还是令人失望:在乡下的老家,只见到他那已经回来当废品收费工的弟弟。而他的弟弟说起这个哥哥只有恨,对于他这个哥哥自从他离开东京后就什么也不知道。
回来时,都很泄气。正当失望,我突然想起,他每次都是打我们所里的座机电话和我联系的。而我们所里的座机电话对每一次呼叫号码都是有存储功能的,只需调出来,查对一遍即可。我一说,松当即又和我来到所里,调出我所在的座机近一季度所有的拨入号码,一查对,果真对出了他的联系号码,是手机号。
松兴奋,你去把他引出来。
引蛇出洞?我抚摸着她隆起的肚皮,轻轻地凑过去。说,这,你看,合适吗?
7
人,特别是男人一旦落魄就没意思,上帝有吗?他说。我也不打算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说,可以,经过考虑我答应你的要求。他说很好。同时他警惕地问我报警了没,松子知道了吗?乱糟了的话,我饶不了你们。我说你放心,这是我对你一个人的事。他才放心地提供了相见的时间和地点。
我决定去跟踪松。对于这样一个危险人物,太危险了。
但这事我想找小郝司机帮忙。小郝一听我说,就深恶痛绝,最恨这种敲诈我们的本地人。你不知道呀,坏事都是他们干的呀,特别是我们开出租的,老是受欺负,杀人啊劫车啊,歧视、这些人的素质哪去了呢?我说可能还没这么严重,到时你去给我盯梢就行。这是个熟人,他挺恨我们的。我的意思是破一点财没关系,但要监护好你嫂子保证她没事。跟紧点,随时保持联络。另外你不也要被松发现了。
小郝义愤填膺,都豪爽地应允。
这天星期六,阳光很好。按他提供的时间,一清早,我就把松送到指定地点的附近。接着离去,又很快给小郝打了个电话,小郝上午九点也赶到了。那时,他还没到的。而我坐在市立图书馆的阅览室,手机开着,随时恭候小郝的反馈。
但过了许久,时间约摸转移到了十点钟,也没有小郝传来的消息。这让我太难受。站在市立图书馆的五楼。恰好可以看见他指定地点的主体。那是一展览会馆。它表面巨大的玻璃反射着刺眼的冬日蓝光,看来琳琅满目的。但那一块地表车水马龙,就什么也看不清楚了。那一刻,我后悔没带望远镜。
我拨了好几次小郝的手机,都没有回音。时间到了十一点,我跑去饮料厅喝汽水,却突然接到了电话。小郝司机气喘吁吁地告诉我,糟了糟了。
我说,说清楚,你嫂子呢。
小郝说,不见了。
不见了?我说没听清,再说清楚一点!
小郝大概在边开车边打电话,车窗子是敞开的,话音里灌满呼呼的风哨,我连听带揣摩了老半天才弄明白他的大意。大概是松见到子甘后,两人还没说上几句话就离席而走,松就追上去。
我一听顿时心里一凉,想起这个男人带我去琴房的那天,这是不是又是他的伎俩。我说那你咋这时候才给我打电话,快把你嫂子找回来呀。小郝很委屈,我这不在找吗?等等,等等。
小郝的手机很快就盲音了。这让我连坐的信心都没了。我很快赶到那个展览会馆,又给小郝拨电话,手机依旧不通。正当我要离去,小郝电话来了,还是气喘吁吁,说找到了找到了。
我问在哪?
小郝没回答,他说,松子在追着那个男人跑,一个跑一个追。
这让我头都快晕了!
小郝还在继续说。他们从东平路追到四荒路了,很多人啊看热闹,他们俩一男一女在东京街上狂飙!
我不堪想象已经怀孕八个月了的松挺着大肚子去追赶她前男友的情景。我生气地跺脚,你傻呀,难道你不会阻止吗?
小郝很无辜。他说,我还得看车。几十万日元耶,再说,我在追呀,我开车追!他们俩跑人行道、小巷,他们跑,我都要拐弯抹角开上老长一段才能追上。还是你过来吧。
我又马上赶到小郝说的四荒路。我没有找到小郝,但有一段时间,我确信看到了松!一个挺像松的孕妇一手捂着肚子,一手伸向前呈奔跑状。只是不见那个在前面她追赶的男人。如果是松的话,那么不堪想象,她竟跑得这么快!脚踩风火轮似的,我相信以这样的速度那个子甘也一定会落荒而逃——这个女人一会儿出现在高架桥,又很快淹没在公园十字环路的人群里,就一两分钟的事。我隔远遥遥相望。路上人员熙攘,等我赶到十字环字路,人已没了踪影。
太阳已愈来愈烈。我很后悔出了馊主意。小郝那边又没了消息。我再次接到他的电话已将近十二点。还没等我问,小郝就说,你快来呀,到医院。张大夫这里,迟来半刻,大人小孩都没命了。我问你说清楚,我马上来。路上小郝说,松追那个男人昏倒了,他赶紧把她送到了张大夫这里。
我说,那那个男人呢?
小郝一听看似很生气,我已经报了警,我说是抢劫犯!警察一起上来,估计被抓了。
“华裔—赵子甘—歌手—孤儿—1973二战后新泻滞留义工家庭出生—2005—吸毒”。
很快,小郝在那边像报话机一样滴滴地一口口报出了子甘的所有来历。
我惊讶、诧异。我心里嘀咕。对于这个模糊的人,我翻山倒海地追忆,竟想不出。
心总算是悬下来了,只是胸腔里有层很薄的愧疚。我正要舒一口气敞开,那边小郝对着我喊:你快来张大夫这!她死活不答应,说等你来,你不来恐怕……
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张大夫所在荒川区医院。妇产科11号门口,小郝正无力地仰头躺在我坐过的那排椅子上,冬日里汗流浃背。冬日的甬道腾升着暖气宛若迷雾,而旁边的一扇门里,进进出出的护士当中,看到一个护士端着一块染满鲜血的白布匆匆走出,我正要往窗子里去探望,一声婴儿啼哭尖锐地喷薄而出……
责任编辑:易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