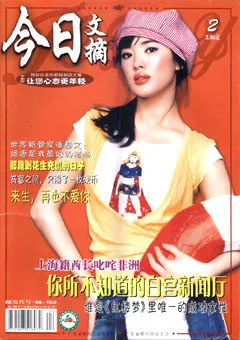那段剥花生充饥的日子
1938年,蒋经国被父亲蒋介石派往江西南昌。在那里,因为工作关系蒋经国结识了秀外慧中的章亚若,不久两人相恋。而当时的蒋经国已与蒋方良结婚3年。1942年1月,章亚若在桂林为蒋经国生下一对双胞胎。取名蒋孝严、蒋孝慈。但在孩子出生不久后,章亚若就离奇死亡了。为了这对双胞胎的安全,舅舅章浩若将他们改娃为章。1949年,在蒋经国的安排下,蒋孝慈一家由南昌来到台湾新竹。在外婆一家的关爱照顾下。这对双胞胎的童年生活过得快乐而单纯。
我与哥哥孝严,出生在广西桂林。不久我们被带回江西南昌的外婆家,直至民国三十八年迁到台湾定居新竹,皆由外婆及舅舅抚养。
由于母亲去世时我们才几个月大,可说对母亲我们没有任何记忆。根据外婆描述,母亲的字写得很好,人也长得娟秀,做事果断,能力强,同时对外婆十分孝顺。
外公家境非常好。印象中南昌的老家是一幢非常大的宅子,气派的正门上有两个铜环扣,门口一对石狮子,偌大的天井连接二层的楼房,规模宏伟。外公是典型的读书人,成天就是吟诗作对、读书写字。外婆则是个慈祥的女子,但个性很坚毅,对我们惜疼之中,自有其执著的原则。时局动荡,大人们讨论东渡的问题,外公因为舍不下庞大的家产以及孩子们,不肯离开大陆,外婆则和舅舅决定带着孝严和我来台湾。
外婆随身带了些现款和首饰,但因为考虑到短期内就要回去,数目并不多,足够我们一段时间的需用。没多久,我们的生活就捉襟见肘了。从当时整个社会来说,大家的物质条件几乎都同样差,在这种环境下长大,我并不觉得苦。
因为家贫,买不起鞋,外婆就亲自缝鞋面纳鞋底为我们做布鞋。不过我们平常上课多半打赤脚,同学也都这样!而且不穿鞋,跑得蛮快的。小孩子爱玩,地面再烫或再冰都满不在乎。偶尔碰到正式些的场合不得不穿鞋,反而有些不自在。
我们的房子十分简陋,甚至没有一间浴室。屋内堆了一些空的木箱子,便拿来在厨房一角隔个小间,勉强算做“浴室”。水壶烧点热水,再对冷水,倒在木盆里来洗澡,后来换成厚的铝制盆,用肥皂洗澡,那便是当时生活的最佳写照。
有时候我们穷得连米钱也付不出。欠了几次之后,米店再也不肯让我们赊账了。这时我们只好改用便宜的面粉,由舅舅自己做馒头或加点青菜煮面疙瘩。十分困难的时候,连面粉也买不起了,就只好吃带壳的煮花生。我们放学回家,见舅舅在揉面,就知道要吃馒头;见报纸包的一大包东西,便知道是吃花生的日子,一颗一颗把壳剥开,总得吃个几餐。这段生活经历,让我早早就能体会人生真实的一面,了解到生命本身就是艰苦的奋斗过程。
小时候我们房里有两张竹床,小的一张外婆睡,大的一张我跟孝严挤,从小这么推来推去,挤来挤去,到高中都没分开过。如今想起那些事,仍觉得值得回忆。
外婆与舅舅对我们两个小孩,爱当然是极爱,却丝毫不溺爱,无论求学、做人都管得十分严格。每天我们必须自己整理内外的环境,穿衣、吃饭,与长辈亲友的应对进退细节都有一定的规矩。
家中对我管教如此之严,但是我小时候并不真正懂得念书的意义及乐趣,一直到了初中也还是一样。班上同学以农家子弟居多,大自然里长大的孩子顽皮透了,跟着他们,往往早上十点左右就把便当吃完了,中午花样更多,拿着空便当盒,到田里抓泥鳅抓虾子,生火煮来吃。夏天便跑到河里去游泳,整个生活充满了田野的乐趣。
由于家中要求得十分严格,调皮好玩之余,我的功课倒是尚能应付。初中那段日子,舅舅要求我们兄弟俩每天要将上过的国文和英文课文,利用下课时间抄一遍带回来。不这样做,就拿不到零用钱。舅舅以为,不管你懂不懂、爱不爱念书,抄过一遍至少可以记住一些,同时还可练一手漂亮的字。我小学初中都不曾主动地勤奋学习,而自小被严格要求埋下的种子,直到高中之后才萌芽。我如同开窍一般,突然懂得了念书的方法,并且体味到其中的乐趣。
念大学时,孝严与我在东吴,家中经济依然拮据。私立学校昂贵的学费和生活费让我们相当困扰。譬如在小店包饭,我们总无法把每个月的钱一次缴清,小饭馆的老板人不错,见你钱没缴齐,他也不催你。饭仍照吃,菜仍照打,只不过他有个妙方法,小店里备有小黑板,名字都在上头,“正”字为记,欠一天画一杠,缴了钱合算一下又擦掉几杠。我跟孝严每个月都榜上有名,甚至欠到十几天。得等舅舅从新竹寄钱上来才能一点点地还清。
从小外公就教我们吟诗诵词,而舅舅也注重培养我们在古文方面的兴趣。长此以往,兴趣被酝酿得十分深厚,进入东吴大学中文系之后,我读起书来如鱼得水。不过因为大一那年,家中发生了一起法律纠纷,竟使得我改变了一生的发展方向。
纠纷起因于舅舅向人借了钱,真正的债权人并未提出诉讼,而另一个人上法院要求查封我们住的房子。舅舅十分苦恼,总觉得整件事不对劲,欠了钱是没错,对方有权提出诉讼也没错,但是绝不该由此人来告。至于应该怎么办,他又没主张,买了一本《六法全书》看了半天,最后房子仍然逃不过被查封的命运。
这件事给我很大的刺激,我想,如果当时我读的是法律专业,就不至于全家一筹莫展,起码诉状会写,基本概念了解,应享受的权利就不会平白丧失,也许查封之事尚有挽回的余地。因此心里便暗暗决定要转法律系。
第一年,想转法律系的人太多了,却只有一个名额,我考了第二,没转成。到了二年级想转,没有名额。到了三年级我仍然想转,但是当时一位老师告诉我,中文系既已念了两年,再转法律系的话会耽误许多时间,不如先把中文系念完,文字基础深厚了,再来念法律系,效果会更好。
这番话我确实听进去了,于是便扎实地把中文系读完,当完兵,再回东吴从法律系二年级开始读起。东吴法律得修五年,因此我的大学前前后后念了八年,获得了两个学士学位。
由于确实尝到书味,故读书总比别人细心。在法律系,每次考试前,同学总会要求我在课堂上帮他们把所有的课程复习一遍,所以对于法学的脉络,我有了较清楚的认识。
离开东吴,我赴美念书,先是在得州南美以美大学念政治学硕士,随即又到路易斯安那州的杜兰大学念法学硕士及博士,直到民国六十七年才回到岛内,算算这年我正好是34岁,跟早先立下35岁前全心念书的计划颇为吻合。
在美国的六个年头,为了赚取学费,每个暑假,我都得打工。第一个暑假蒙同舍的一个念经济的老美介绍,我天天搭他的车子到盖房子的工地去挖地基。美国式的屋子结构其实很简单,我们负责把地基挖好,钢架竖好,灌水泥,其他部分就是别人的事。挖过一处又一处,顶着得州有名的毒辣的太阳,汗水倾泻不止。第一天下了工回去,十个指头都磨破流出血来,只好包起来,第二天再去,懂得戴手套了,再做几天。连手套都磨破了。整个夏天,我都与大批笨重粗糙的钢筋水泥周旋。记得一个小时可以赚3美金,待遇算是很好,所以辛苦也就在所不计了。
外婆是我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一股推助之力。逃难颠沛,在台东扎新根的苦日子始终没难倒她,她总教我们环境苦不重要,一个人有没有骨气、有没有志向才是关键所在。对我们的身世,她向来只字不提,孩提时我们会问,但是她只灌输我们一个观念:父亲是个正直、勇敢、能干的人,一个很好很好的人。这样的良苦用心,使我们能一路平凡成长,不管做人做事都知道要全心全意,全力以赴。
高三那年,外婆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但她仍习惯早起,将茶杯上的覆布掀开,用湿抹布擦净桌椅,迎接新的一天来临。有一天我醒来,一看什么动静都没有。急奔去看,外婆已在睡梦中过去了。
外婆虽然过去了,但她教导我们的点点滴滴,一种不特别但很坚定的中国人的态度却深深浸透我生命的底层,使我们在面对家世揭晓、众说纷纭的情境之下,仍然能坦诚坚定地走过来,秉着我们心中的爱与诚,开创我们自己的路。
(郑许文荐自《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