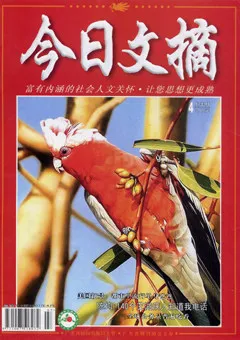陈均:140个艾滋病人知道我电话
陈均身高不足1.5米,穿特小号白大褂,伸直手臂刚好够着戒毒所的门铃,但在四川省L市市中区登记在册的艾滋病感染者心目中,她是一个必须仰视的女人。
她手里有一部小灵通,银色外壳,24小时开通。每次拨通,“你好,这里是市中区疾控中心艾滋病热线。”这个区域里现有的140个艾滋病人差不多都记得住这个号码,一旦出事,陈均常常先于他们的家人,第一个出现在他们身边。
“马路上叫妈妈‘陈医生’的,都不是好人”
陈均今年47岁,毕业于重庆药剂学校,学的是化验。在疾控中心干到第15个年头,她才发现了自己原来还有好大的气力没有使出来。那是2002年初,中英艾滋病项目选中L市作为艾滋病防治和行为干预的试点,作为疾病控制中心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她一下子找到了可以全心投入的事业,没错,不仅仅是工作。
她打交道的主要是:吸毒者、性交易者、艾滋病感染者,他们的家属和警察,最近增加了男同性恋者。夜班出租车司机小赵常在凌晨送她回家:“啊,你不知道她有多忙,一个月30天,有25天她在加班,千万不要做这份工。”
大多时候,她的包里有几盒安全套,可以发给小姐或嫖客;或者一包香烟,散给那些一个个被她和同事们劝进美沙酮替代(海洛因)项目的吸毒者。她的红皮笔记本上有不少好笑的名字,譬如四妹、胖妹、长脚、光头,她知道他们每个人的故事。
以前,她也在公交车上、菜场里丢过钱包,她只知道她居住的这座小城里有扒手,但不知这些扒手背后的生活是如此惊心动魄——为了凑足每天的毒资,这些人忙忙碌碌,坑蒙拐骗,无所不为;吸毒的女性99%都有过卖淫史,一旦犯瘾,任何龌龊的肉体交易都可以达成。
为了接近这群人,她缴了不少学费。她的小灵通差点被诈骗走;发放的医药款转眼调包成了假钞,不得不再发一份;组织感染者参加联谊活动,鼓励他们上台唱歌,有人上台咕哝一句,只是冲着洗发水之类的奖品。
这些人的亲人朋友已经不要他们了,他们借不到一分钱。当他们有病有事有麻烦的时候,都会想起陈医生。许多个求助的深夜,这个小个子女人挟着一阵风就来了。
“她把我们当成跟她一样的人。”一个艾滋病感染者掏心掏肺地说。现在,已经没有人动她的东西了,“人心都是肉长的”。甚至有人丢了钱包、手机、电脑硬盘,可以通过她的吸毒朋友打听到是谁干的,只要没出手,都能找回来。
小城不大,走到哪里都能碰到熟人,于是路上常有精瘦的男子大老远招呼她:“陈医生。”陈均13岁的女儿丫丫却认定:“哼,马路上叫妈妈‘陈医生'的,都不是好人!”
陈医生的丈夫,一个老实人,常常咬牙切齿却不忍发作,只在妻子晚归时到厨房热饭去。一家人定下规矩,坚决不等这个不守时的人共进晚餐。
她干得乐颠颠的,为什么呢?“跟他们四年交道打下来,我真是觉得个个都是聪明娃儿,只是一步走错步步错,可惜了。”
图什么呢?“要求不高的,如果他们说声谢谢,或者他们有一点点好起来,我就满足了。”
到处推广安全套
2006年10月1日晚上8点,陈均在包里塞了11盒安全套,坐公交车去了当地有名的××广场——“站桩鸡”(指从事低价格性交易的女性)聚集揽客的地点。
陈均坐到一个老头儿身旁。老头今年69岁,做杂工,他没有家人,东坡广场是他常来的地方。接过陈均给的安全套,他看起来一头雾水,他一辈子没用过这个。
男人们渐渐围拢来,陈均开始示范:“轻轻撕开外包装,吹一下,挤掉空气……”男人们不好意思起来,冒出一串呵呵笑。陈均接着讲艾滋病的性传播途径,一个坐在自行车上、单脚点地的男子说:“我看见报纸上说,性传播(艾滋病)的几率是万分之零点几呢。”陈均说:“如果你撞上了,就是百分之百。”
她鼓励他们去疾控中心接受免费的艾滋病检测,一个虎头虎脑的男人问:“那查出来,是不是要抓起来?”众人哄笑。又有人问:“查出来,如果是艾滋病,会马上死吗?国家管治吗?”于是,窗口期、潜伏期、发病期、鸡尾酒疗法、四免一关怀,陈均摆开龙门阵。人越来越多,20多号男人围着她,可她一点不害怕,她镇得住场子。
工作总归要做的
2006年10月2日,陈均穿过菜场,去看望一对感染者阿杰和小瑗。
小瑗原先是幼儿园老师,因为长得漂亮,被人拖下水,以卖养吸。她从一个男人身边转到另一个男人身边,只要对方能供她吸毒。跟了阿杰之后,两人联手上街骗外地人的钱。
小瑗见到陈均显得很高兴,陈杰则一如既往抱怨着他的低保太少。
他和小瑗的免疫力都在200以上,没到吃药的阶段。但他常常会问:“免费吃药?是不是拿我们做试验?”陈均不得不从头解释,包括国家抗艾经费的十几亿元并不全给了L市,也不是做个除法,平摊到每个感染者头上。“有时候,他们真的是无知啊。”
从阿杰家出来,就看见一个穿橙色T恤的男人抱着一个黑皮包像兔子一样跑过去了。两个刚下了晚班的超市女职员呆在路边:“抢包了!”后面又过来一个男人,一声“陈医生”,便晃过去了。陈医生没有应他,也没有表情。这是两个在喝美沙酮的吸毒者,一个抢劫,一个断后。
“有时候也沮丧的,这些人,很难改好了。但是,工作总归要去做的。”
2006年10月3日,陈均坐进吸毒者常去的茶馆,绰号师傅的老朋友迎面就劝陈均:“陈医生,没用的,我说你犯不着那么辛苦,又没有加班工资。”
“唉,我也搞不懂,他们究竟要什么,我们做些啥子才能真正帮到他们。”
“要啥子?不劳而获,你能给吗?”师傅接着说:“这些人,别说外人讨厌,我都讨厌他们。”
陈医生笑笑,继续做她的事,虽然也知道好多事情不是她一个人能够改变的,但她从不轻言放弃。
(冯水凭荐自《南方人物周刊》)